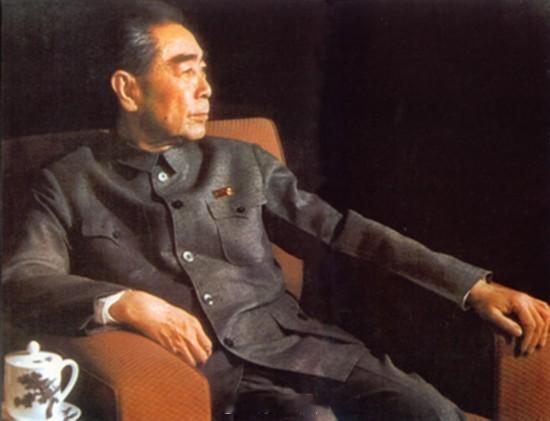杨银禄:“倒周”风波
外交部有一份临时通报情况的刊物《新情况》。1973年《新情况》153期惹出了一场风波。
那年6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6月16日,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副处长张再写了一篇分析文章《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新情况》153期上。文章指出,美苏这次会谈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7月3日,周总理从王海容处得知毛主席批评了这篇文章,当即致信外交部负责人,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4日,毛主席约张春桥、王洪文等人谈话,再次点名批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当年11月底到12月初,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周总理所犯错误。“四人帮”借机对周总理发难,无限上纲上线。
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这是他短短两年时间里第6次访华。周总理多次与基辛格举行会谈。
基辛格访华的第三天,毛主席会见了他。会谈时基辛格说:“我已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指苏联)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
毛主席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按主席的理解,基辛格这番话的用意是:如果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而不是美国深感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这也使毛主席感到不快。求助于人与让人求助,是不一样的。毛主席一贯对敌人强势,他要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11月14日凌晨,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基辛格举行了第四次正式会谈,商定了“会谈公报”的措辞。结束会谈前,基辛格试探性地问道:“如果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加以摧毁的行动,中国需要美国做些什么?”周总理说:“我们还要考虑,我们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至此,会谈结束。14日《中美公报》发表,15日上午基辛格将离华回国。就在他要离开中国前几小时,突然提出要拜见周总理。得到消息。周总理马上打电话请示毛主席,是否可以进行这次会谈?反馈的答复是:“主席才睡,服了几次安眠药才睡着的,现在说什么也不能叫醒主席。”周总理深知毛主席的身体状况,无奈,决定和叶剑英一起会见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再次提出前述那个问题。周总理按照原定的会谈口径回答:“此事需要进一步考虑,等以后再说”,并强调一切需要请示毛主席再作决定。
上午,周总理到毛主席住处,汇报会见的情况,毛主席听了汇报后,也没有提出什么不妥。可是第二天周总理就得到消息,外交部有人在毛主席处说他对外谈话说错了话,接着江青一伙进一步上纲上线,说周总理自作主张接待基辛格,这不符合外交原则,再说接待计划中也没有基辛格回拜周总理这项活动,而且总理对基辛格说了“谢谢”之类“投降性的软骨头话”。
毛主席本来就对基辛格“求助”提议不快,再听说周总理私见基辛格,更加不快,于是大发雷霆: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样,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他严厉地说:“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于是11月17日,周总理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应召到毛主席处开会,会上,毛主席对这次中美会谈提出批评意见,他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批评周总理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以及叶剑英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的“右倾软弱”。
当天晚上,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主席对于这次中美会谈的批评意见,并介绍了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
会上,江青自以为“倒周”时机已到,攻击周总理是“右倾投降主义”。姚文元攻击周总理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总理忍无可忍,当场予以驳斥。
后来,听了江青等人的“谗言”,领袖进一步指示,由王洪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周总理、叶剑英的“右倾错误”。会议从11月21日至12月初,持续开了十几天,多次对周总理进行批评,周总理多次检讨都“过不了关”。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见客,不开会,不化疗,不按时吃饭,一向注意仪表的他,拒绝刮胡子,日夜趴在桌子上写了撕,撕了写,写了又撕。因为老低头写字,他的眼睛肿了,脸肿了。坐多了,腿和脚也肿了。
高振普在他的《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一书中说:“为保密,会议场内的服务员只指定两人,其他人打下手,在场外等候。其中一位服务员进去送水,听到他们在指名批评周总理,她惊呆了,把几杯水倒翻在地,哭着跑了出来。以后再也没让这位服务员进去,连打下手也没她的份了。”“会议的特殊性,把我们提醒总理休息、及时送饭、及时送药的三项服务任务缩短为一项,只剩下及时送药了。有一次,我把药交给服务员,让她送给总理吃。她还给我空瓶时,避开我的目光,低着头跑进服务间。我觉得不对,紧步跟了过去,看她用手绢擦眼泪,她转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对我说:‘他们还在批评总理。接着愤愤地说:‘他妈的,我不干了。”“我按捺不住难过的心情,强忍住要滚出的眼泪,压低嗓音,对她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叫别人看见了。看实在止不住哭声,我就把她让进了隔壁的福建厅,‘你就在这里哭一会儿吧,有事我来叫你。”
江青一伙批评周总理,是想捞一把政治资本。
主席直接踩“急刹车”
到了周总理十分艰难的时候,毛主席发现江青一伙要“倒周”的真正意图。因为江青一伙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让他感到不安了。他们要把周总理打进王明、张国焘、林彪等人的另册。这不是毛主席的初衷和本意。他对周总理的方针是“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周总理如果再不回到总理的岗位上来,全党、全国政治、经济、日常工作就会乱套。
毛主席12月9日会见来访的外宾以后,对周总理说:“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不亦乐乎啊。”
毛主席在当天就找会议主持人王洪文谈话:“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很显然,毛主席对批评周总理的问题,踩了急刹车,下了死命令——此事到此为止。
请看《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中的几段话:“会议不停地开,会场内的气氛变得更紧张了,有时一次会进行七八个小时。我们等在外边更是坐立不安。”
“持续了几天的会,今天照例是晚8时开始,出乎意料的是,会议只进行了三个多小时就散了。这次总理不是第一个出来。先出来的是那些部长们,他们哭丧的面孔不见了,脸上露出了笑容,看到我就主动打招呼,问一声:‘你好吗?这一声‘好,问得我心里顿时暖乎乎的,我猜想这会大概快结了……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更加直率地对我说:‘你又可以吃宴会了。她以此向我透露总理又可以见外宾了。我一直提到嗓子眼的心落下来了。”
对于这么长时间的批评会、这么大的委屈,周总理后来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怨谁。为了顾全大局,他再一次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注:杨银禄,江青第二任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