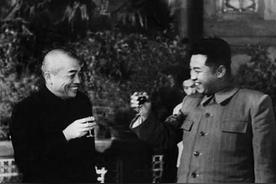1953年,志愿军师长王扶之负伤回国,偶遇一赶车老丈,于是便乘车回家,两人相谈甚欢,可谁料分别之前,老农询问道:“我儿王硕,12岁就参了军,你能帮我打听一下吗?”王扶之听完浑身一颤,喊道:“爹,我就是王硕呀!” “同志,扛着行李不好走吧,要不坐牛车上我捎你一段路。” 王扶之也是个放牛娃,虽然升到一师之长了,但是见到牛车比见到部队的皮卡还亲近。 他没有推脱,爽快的感谢了老乡的热心,一个跃步登上了牛车。 本来部队考虑到王扶之受伤,因此专门派了汽车送他回家,可是乡下的土路泥泞又崎岖,四个轮子的汽车走得十分颠簸。 王扶之觉得这样走下去不仅耽误时间,而且汽车也容易故障,于是主动下车,拿着行李自己往家走,正好遇上了干完农活的老人。 老人见王扶之虽然穿着军装,但是没有架子觉得亲近,而王扶之感谢老人的帮忙,两人很快热络地交谈起来。 “你们年轻人能跑能跳的,也不怕磕磕碰碰,我这把老骨头可不敢这么跳上车,没准儿就要摔。” 王扶之见老人虽然满面风霜,但是经年累月做农活训练出来的身体十分结实,于是夸赞老人不输年轻人,没准儿比自己还厉害呢。 “我没参军前就每天放牛,这牛车可不好赶,老黄牛的脾气可倔了,可是在您老人家手下服服帖帖的。” 老人哈哈一笑,听出了王扶之没有说假话,这番言论倒是让老人想起了自己多年未见的儿子王硕,王硕小时候也老是跟牛较劲。 王扶之穿着军装,虽然老人认不出衣服上的编号和标志,不过在他心里,共产党的军队跟人民都亲近,便大着胆子向王扶之打听。 “同志你这肩膀上星星这么多,是不是在部队里当大官啊。” 王扶之连连摆手,对他来说不管是师长还是士兵,都是守护国家和人民的兵,虽有等级和职责的不同,但是对人民都是一样的。 老人一听王扶之级别不低,首先想到的不是王扶之军衔有多大,而是他手下一定有很多兵,认识自己儿子的可能性大大增强。 老人还没说完,王扶之已经泪流满面,他印象中的父亲还是跟结实的中年汉子,一别十八年,父亲已经成为了白发苍苍的老人。 “爹,我是王硕啊,我回来看您了。”王扶之此时哪里还有师长的威风,像个孩子一样跌进老人的怀中。 父子俩相拥而泣,老人把王扶之拉起来仔细端详,当初那个瘦骨伶仃的放牛娃,怎么就长成比自己还高大的战士了。 十八年分别,老人在家乡经历动乱,王扶之在沙场闯过战火,二人都不复当初的模样,两人居然都没有认出对方。 说起儿时的事情,记忆中的影子与对面的人相互重叠,即使身形容貌、声音气质都已改变,但是二人对亲人的思念丝毫没有减少。 老人迫切的想知道王扶之这么多年都去了哪里,自己的儿子在外南征北战,有没有吃饱穿暖,是否受伤。 而王扶之又怎么能让年迈的父亲再担惊受怕?他不能说自己转战三大战区九死一生,在敌人刀霜风剑严相逼中受尽苦难。 他不能说自己骑着自行车闯入日寇据点,面对敌人密不透风的扫荡冒死传递战报。 他不能说自己曾在枪林弹雨中攻坚的,每一次战功背后是数次擦肩而过的子弹。 王扶之更不能说,自己刚刚在朝鲜战场上死里逃生,美军空投的一颗炸弹,炸的天崩地裂,把王扶之埋在了山石和碎木之间。 王扶之全身上下都是伤痕,在空气稀薄的坑道下,王扶之的右腿之间失去知觉。作为师长,王扶之把保障战士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数次将唯一的水源留给战友。 他不能告诉父亲,自己被埋在坑道中时,连遗书都无法写,十八年未见的父亲,差点儿就成为了终生的遗憾。 王扶之只是说:“爹,咱们志愿军打了胜仗,以后国家就安全了!” 参考资料:朝战最命大将军:遭活埋38小时生还2016-02-2411:16凤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