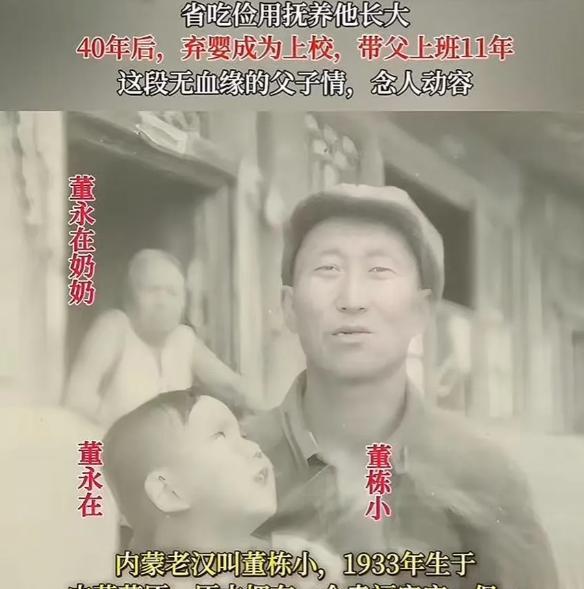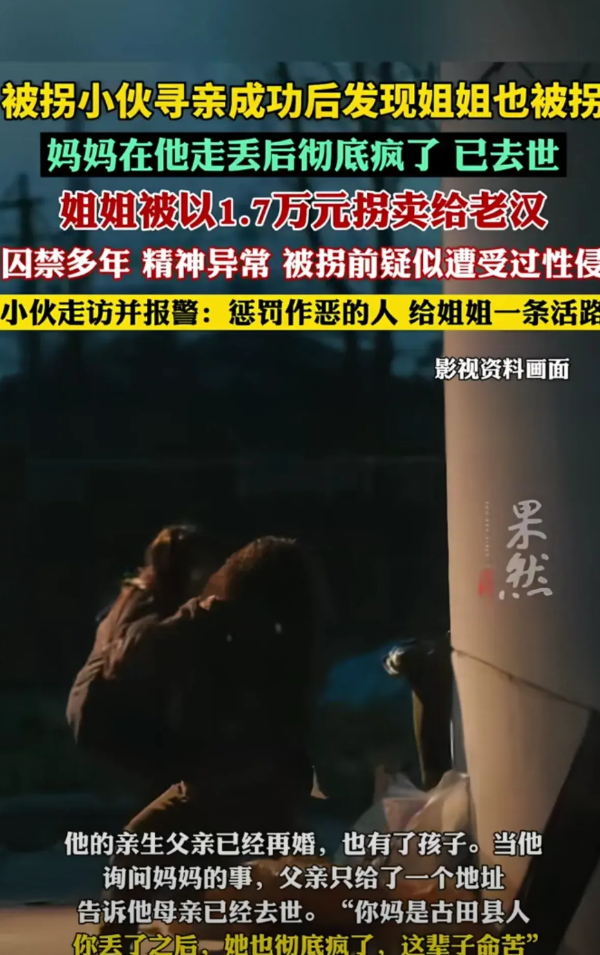五旬哭灵人李美珍:痛哭发自肺腑,今每场挣3000元,给儿子买了房 在中国,丧葬仪式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虽然一些古老的习俗逐渐消失,但有些传统依然得以传承。 哭丧不仅是亲人哀悼死者的一种形式,也是一种纪念长辈生平事迹的方式。 出殡时的哭丧仪式最为庄重,通常会由亲属尤其是男性进行。 然而,在一些农村地区,哭丧的环节变得越来越商业化。 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的职业哭灵女,她们代替家属哭丧,在棺材前哭泣、唱歌,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定的报酬。 哭灵女的职业早在北宋时期就有类似的职业队伍。 这些哭灵人通过唱挽歌、念丧词等方式为死者送行。 在某些地方,丧葬仪式中的哭丧队伍往往伴随有鼓乐演奏。 今天的哭灵女通常由专业演员担任,许多人认为,这种方式改变了传统丧葬习俗的本质。 亲人自然流露的悲痛被替代为表演。 然而,对于家属而言,长时间的哭泣和精神压力可能带来健康隐患,因此请专业人员代替哭丧,也是一种妥协。 李美珍的故事令人注目。 李美珍家里十分贫困,她在八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 她从小不仅要帮助父母照顾弟妹,还要忍受连年灾荒。 她成绩优异,一直希望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然而家中贫困让她在初中毕业后不得不辍学。 18岁时,李美珍在亲戚的安排下与村中的一名男子结婚。 尽管这段婚姻并非出于自愿,但只能默默接受。 婚后,李美珍随丈夫前往广东打工。 丈夫的暴躁脾气让她深受折磨。 李美珍仍然尽力操持家务,并生下了两个儿子,然而她的付出换来的却是更多的责骂。 李美珍曾多次试图反抗,但每次都被丈夫和婆婆压制,有一次,她在绝望中差点用砖头结束自己生命。 终于,在28岁那年,李美珍决定摆脱这段恶性循环的婚姻。 回到娘家后,她与丈夫分居,带着两个儿子开始了新的生活。 起初,她仅能靠做一些零工维持生计。 在一次邻村的表演中,她看到了一个年轻女孩在丧事上痛哭流涕,真情流露。 李美珍被女孩的情感所感染,知道了“哭灵人”这个职业。 通过与女孩的交谈,她了解到哭灵人需要具备良好的情感共鸣能力与演绎技巧。 她开始主动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哭灵人。 在女孩的推荐下,李美珍参加了一次丧事。 在丧事的现场,李美珍将自己的痛苦和逝者的悲伤融为一体,痛哭流涕。 她也因此获得了70元的报酬。 哭灵人的工作虽然看似简单,但实际上要求极高。 她必须深入了解逝者的生活和经历,编写适合的哭词,并把握哭泣的节奏和情感的强度。 每一次的哭灵,她都要倾尽全力。 李美珍逐渐成为了长乐一位颇具声望的哭灵人。 如今,她凭借自己的努力,买房、改造老房子,并且能够独立养育两个儿子。 她的哭灵从最初的几十元逐步攀升至3000元一场。 她不再为过去的困境感到惋惜,而是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 如今,李美珍年过五十,她的事业依旧稳步发展,偶尔在空闲时间分享自己的经验。 还有很多人在这一职业找到归宿。 武会霞是河南人,小时候目睹过许多周围人去世的场景。 她回忆,自己家境贫困,母亲瘫痪在床,而自己和丈夫所种的土地根本不足以养活这么多口人。 有一次,她参加了村里一位老人的葬礼,看到主家请来了一些专门的哭丧人。 她发现原来哭丧不仅是一种传统习俗,还能带来可观的收入。 这种收入对她来说,显得尤其诱人。 而且,她发现自己眼泪容易掉。 然而,做职业哭丧人常常被看作不光彩的事。 武会霞的丈夫最初并不赞同她从事这一行。 而亲戚朋友们听说后,也纷纷表示反对。 但武会霞认为自己更应该注重生活的实际需要,她最终找到了一个专门的哭丧团队。 刚开始时,武会霞并没有掌握足够的技巧。 记得第一次接活时,她由于紧张,根本无法投入情感。 尽管有同行在旁帮助,但她仍感到非常尴尬。 武会霞开始向其他经验丰富的同行请教。 在工作中,她渐渐掌握了如何临危不乱,如何哭得更有感染力。 她表示,哭丧时一旦哭丧人叫错了死者的名字或称呼,那么这一场丧礼可能就会被认为不合适。 逐渐地,武会霞和丈夫合作成立了自己的哭丧团队。 她们夫妻俩一年大约会接七十多场丧礼,每一场收入在六七百元之间,年收入大致可以达到五六万元。 除了基本的生活条件,她们还置办了车子和房子,甚至开始接到一些老乡的介绍活。 武会霞认为,虽然如今这份工作给她带来了生计和尊重,但它可能会逐渐消失。 参考文献:[1]郑怀佐.闵惠芬二胡“声腔化”演奏技法探究——以闵惠芬《宝玉哭灵》中的“喊风调”及其润腔处理为例[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8(3):139-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