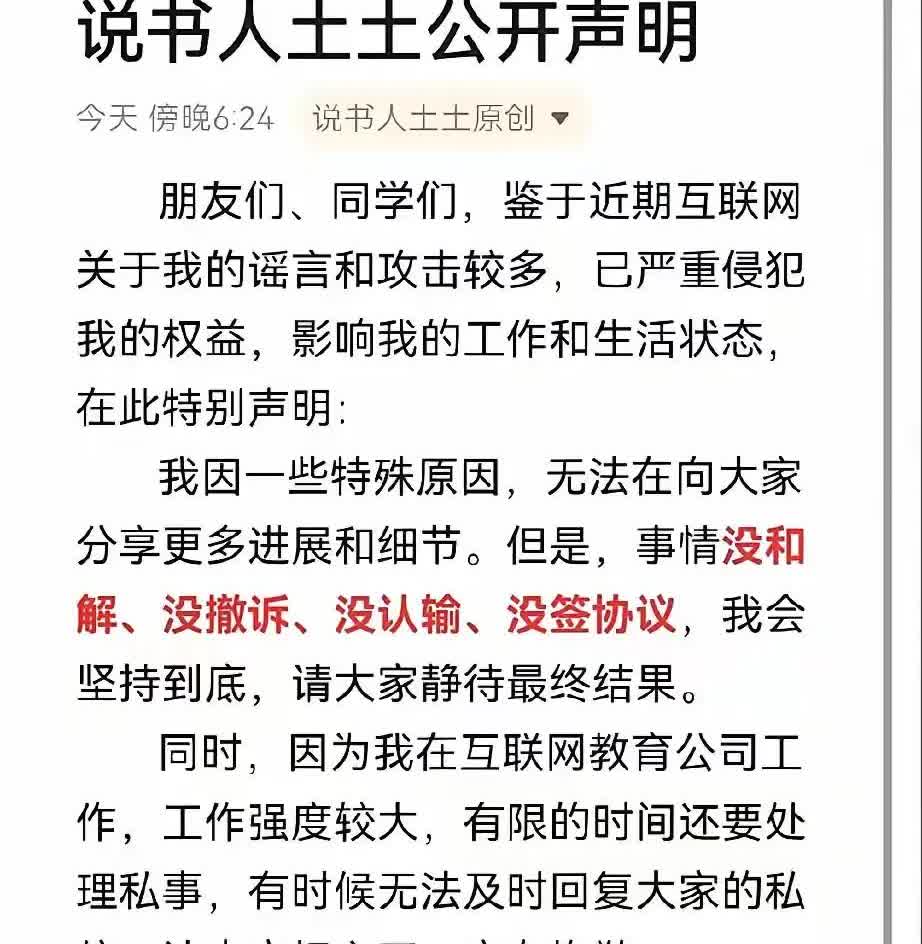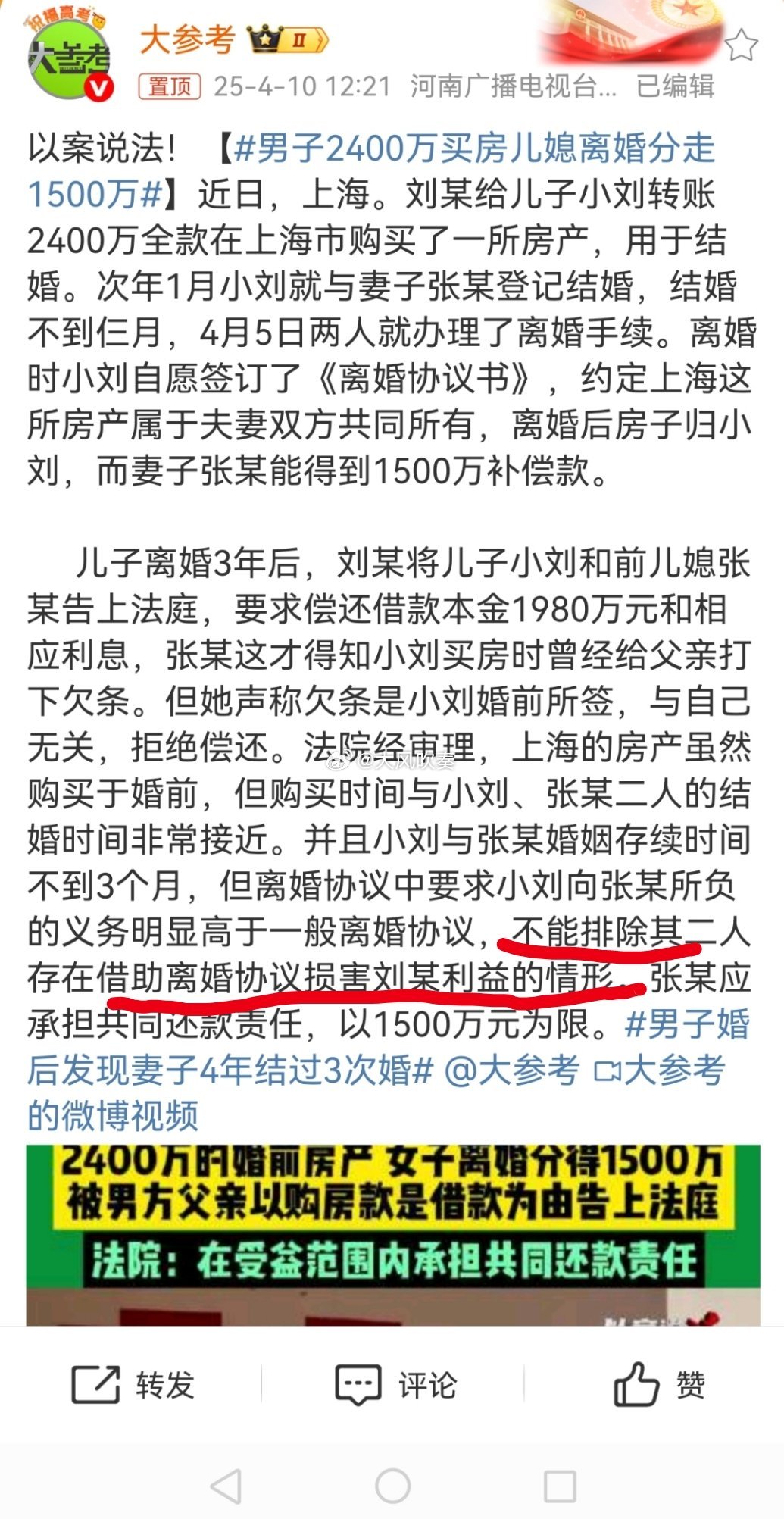她穿着绸缎短裙,挽着风尘男子,在北平最热闹的东单舞厅门口被一群人围住,有人喊她“民国第一荡妇”,有人骂她“勾引公子哥的狐狸精”。 她没说话,只朝天啐了一口,转身进了舞厅,这一幕成了当时报刊竞相报道的“奇闻”。 可没人关心她的真名叫余美颜,更没人知道,她不过是想活得像个“人”。 余美颜出生在1902年,广东佛山人,家里是做丝绸和洋货生意的,父亲是传统商人,母亲倒是个识字女子。 她长得漂亮,皮肤白、眼睛大,还有点混血的感觉,学校男生追她,她写情诗回过去,被老师抓到,还写进学籍档案。 父亲知道后大怒,把她从学校拉出来,关进后院两个月,不许她见人,说:“你再这样,将来没人要你。”她只回了三个字:“不稀罕。” 1918年春,她十六岁,家里忽然逼她嫁给一个三十多岁的广西盐商,说是能帮家里渡过经济难关。 她死活不从,晚上拿剪刀剪断头发,跑了,她跑去广州,没钱没地住,在码头被巡捕抓走,说她是“女流浪汉”,关进了广州女子习艺所。 那地方看上去像慈善机构,实际上就是半个女监,她被关了半年,每天缝军服、织毛袜。 有人想带她出去做女佣,她直接说:“宁愿在里面累死,也不伺候人。” 她从里面放出来时,整个人像变了一样。原本是个胆大的女学生,现在变得更刚。 她不回家,自己在广州租了个小房子,用别人的身份证办了舞女执照。 那个年代,跳舞是“新女性”的标志,也是堕落的代名词,她不管这些,只说了一句:“老娘跳的是自由。” 有人说她三年内换了上百个男人,有的说她“跟过三千人”,其实这些大多是传闻。 她确实交过不少男朋友,其中有个叫马建民的,是当时南海县县长的儿子。 马是个留洋回来的,鼓吹自由恋爱,他俩一见钟情,常常在报纸副刊上发公开情书,还在《南方妇女》写专栏,标题就叫《摩登情书》。 她写的内容非常露骨:“情欲像炸开的水银球,越压越散,越散越浓。” 她并没有就此沉寂,她去了上海,用稿费出版了她唯一的一本书《摩登情书》合集,那年她二十岁。 书里收了她写给马建民的情诗,还有她与几个男人的书信往来。 她写性爱、写分手、写身体的感觉,每一封信都像是在说:“我爱过,也伤过,但我活得明白。” 书卖得不错,上海文坛却炸了锅,说她“用下半身写作”。 最狠的一条评论来自《时报》:“女人若无廉耻,何谈自由?”她回信:“你们骂我,是因为你们怕我。” 有段时间她真的火了,她白天写稿、晚上去舞厅,有时穿着男装出门,抽烟、喝洋酒、玩扑克牌。 她说:“我玩的是命。”但事实是,她的生活越来越难,她写稿的收入微薄,靠男人接济维生。 她住在虹口一个小公寓里,楼下是菜市场,楼上是戏子。 有人说她靠卖身养活自己,她笑,说:“这世道,谁不卖身?卖劳力的不算?” 她的感情世界也越发混乱,她短暂结过三次婚,一个是印刷厂老板,一个是文人,还有一个是个骗子,骗她钱跑了。 她曾在日记里写:“婚姻是个漂亮的笼子,进去容易,出来像剥皮。”她最失败的一段感情,是她去苏州出家时发生的。 她在1926年剃度出家,说是想“洗心革面”,其实是失恋后太痛,她在庙里住了三个多月,每天念经写诗。 有个年轻和尚喜欢上她,写了好多信,还偷偷给她送吃的。 事情被庙里发现,她被赶了出来,她在庙门口对记者说:“佛门清净,但世人不净。” 她重新回到上海,身体已经很差,常常咳嗽,那时的她,早已不被文人圈待见。 没人敢公开跟她来往,报社也不再给她版面,她投了几篇稿子,都被退回,说是“不合时代”。 她去找熟人借钱,没人肯借,有一次她去旧书摊,看到自己的《摩登情书》被人当废纸卖,一本两毛。 1928年,她坐船准备回广州,船还没开出长江口,她就跳了海。 船员说看到她站在甲板上抽烟,身上穿着男士西装,脚下是她的行李箱。 她留下的遗书很短:“黑暗社会偷生,不如一死了之。”遗体没找回来,后来有人说她其实没死,只是逃去南洋了。但没有证据。 多年以后,学者翻出她的《摩登情书》,有人说那是中国最早的女性主义写作。 可大多数人记住的,还是她“风流”“浪荡”“放纵”的标签。 她一生都在反抗,家庭、婚姻、道德、体制,但没一样反抗得成功,她曾用身体对抗父权,却被身体反噬。 她想用爱情改变命运,结果被爱情摧毁,她试图通过文字发声,却被噤声。 她不是圣人,也不是“烈女”,她只是想活成一个不听话的女人。 她失败了,但她留下的那句“情欲像炸开的水银球”,一直留在一些人的心里。 那是一种挣扎过、爱过、痛过的证明,是一段民国女性最真实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