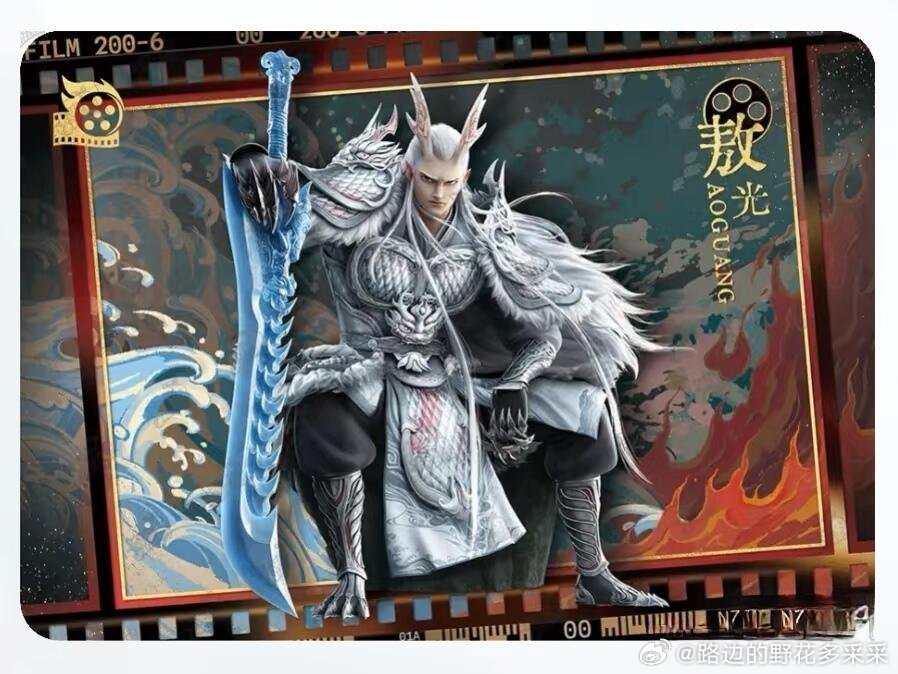1952年,在印尼教书的刘峙,给台湾的好友顾祝同写去求助信。顾祝同去找老蒋说:“让一个上将滞留于爪哇,传出去也不好。”
1949年9月,在广州的国军上将刘峙,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加之自己因之前的徐州兵败,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不敢去台湾,便带着姨太太黄佩芬及几个子女,跑去香港当了寓公。
刘峙当过省主席、集团军总司令、战区长官、绥署主任、“剿总”总司令等要职,敛取了不少钱财,因此在香港的日子,一度过得逍遥自在。
一天,刘峙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闭目养神,门铃突然急促响起。佣人打开门,一群神色不善的人闯了进来。
来的人有十几个,都是刘峙的旧部,带头的军官说:“刘长官,兄弟们在香港过得艰难,你可得拉我们一把。”
刘峙脸色一沉,不悦地说:“我如今也是落魄之人,哪还有闲钱救济你们。”
一个军官气冲冲的说:“还叫长官是抬举你,如今兄弟们都快吃不上饭了,你要是不帮忙,可就别怪我们手黑,不客气了。”
黄佩芬在一旁吓得脸色发白,紧紧躲在刘峙身后。昔日的“福将”刘峙,这时也只是一个“富家翁”而已,他深知这些人惹不起,无奈之下,只能忍痛拿出一笔钱财打发他们。
可这些人贪得无厌,一次又一次上门敲诈,刘峙见再这样下去,除了钱财不断缩水外,家人的安全也是个问题,于是决定离开香港。
去哪里呢?老蒋尚在气头,台湾肯定是不行,刘峙在友人的推荐下,决定去印尼。
于是,刘峙一家乘坐轮船,踏上了远赴南洋的旅程,一路辗转,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暂时住了下来。
由于沿途遭遇劫匪勒索、印尼的军警卡哨强行收走携带的港币,到雅加达后投资做生意失败的诸多原因叠加,让刘峙的万贯家财所剩无几。
无奈之下,刘峙只得带着家人搬去了物价较低的茂物,可茂物消费再低,终究还是要花钱的。为了维持生计,上过大学的黄佩芬,在当地一家华侨学校谋得了教师的工作。
靠着黄佩芬一人的薪水,和剩下不多的积蓄,刘峙一家勉强在茂物安顿了下来。
几个月后,黄佩芬一脸焦急地回到家,对刘峙说:“我在香港的亲友去世了,我得去一趟,可这一走,学校的工作怕是保不住了。”
刘峙也犯了难,说:“这可如何是好,你这一走,家里的收入又没了,而且要是把这个工作丢掉,那以后怎么办?”
黄佩芬说:“我明天再去找一下校长,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第二天中午,黄佩芬回家后,兴冲冲的对刘峙说:“我跟校长说你也很有学问,让你先替我教着,等我回来,校长答应先让你试试。”
刘峙硬着头皮来到学校,校长问:“刘先生,你确定能教好小学的课程?”
刘峙说:“我早年读过私塾,国文还是有基础的,地理方面,我走南闯北多年,教孩子们绰绰有余。”
就这样,刘峙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他好歹是国军上将,阅历丰富,早年还在黄埔军校当过战术教官,教育一帮小学生,还不是手到擒来。
在试课过程中,刘峙仅仅上了两次课,就深受学生喜爱。校长随后带着一众老师前来听课,老师们也被刘峙的博学所折服。于是,校长决定聘任刘峙为正式教师,安排他教授六年级的国文和地理课。
过了一段时间,校长又让刘峙兼授五年级的尺牍写作,不久后又给他增加了作文、历史。由于带了五门课,刘峙的薪水,比黄佩芬高不少。
黄佩芬探亲归来后,校长说:“你丈夫讲得很好,今后你就改教音乐和美术。”
至此,刘峙一家在印尼算是扎下了根。
到了1952年,由于茂物的治安急剧恶化,针对华人、华侨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为了家人的安全,刘峙不得不另谋去处。
刘峙给顾祝同写了求助信,顾祝同将情况反映给老蒋,以言语暗示,说刘峙若长期留在印尼,万一乱说话,将老蒋的某些“秘闻”、“黑料”抖落出来就不好了。
老蒋一听有理,便给刘峙发去邀请电,让他到台湾来养老。1953年初,刘峙带着家人到了台湾,老蒋倒也没有食言,让他挂名“上将战略顾问”,领取薪水。
国民党逃台后,面对“官多兵少”的现状,老蒋下令按照“铨叙军衔”发放薪水。昔日那些中将、少将,许多铨叙军衔只是上校,在失去军职后,薪水大大降低。
而刘峙,早在1935年就铨叙“陆军二级上将”,因此薪水还是不低的,足够一家人的花销,境况比在印尼要好上不少。
无事可干的刘峙,整日忙着写回忆录。不知为何,老蒋拒绝让刘峙的回忆录正式出版,于是刘峙自行油印了一百来册,分送给在台的好友及黄埔学生。
对刘峙的回忆录内容不以为然的大有人在,比如孙元良就愤愤的说:“我这个老师,把徐州兵败的责任全推给杜光亭了,简直是荒唐至极。”
黄杰、王叔铭、袁守谦等黄埔一期生,在收到刘峙的回忆录后,几个人拿出一笔钱作为“回礼”,让刘峙带着黄佩芬去美国旅游散心。刘峙的美国之行,耗时大半年,回来后,他将精力用在了完善回忆录上。
1965年,一直陪伴刘峙的黄佩芬因病去世,这对刘峙打击很大,此后变得沉默寡言。六年后,刘峙因糖尿病并发症而死,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