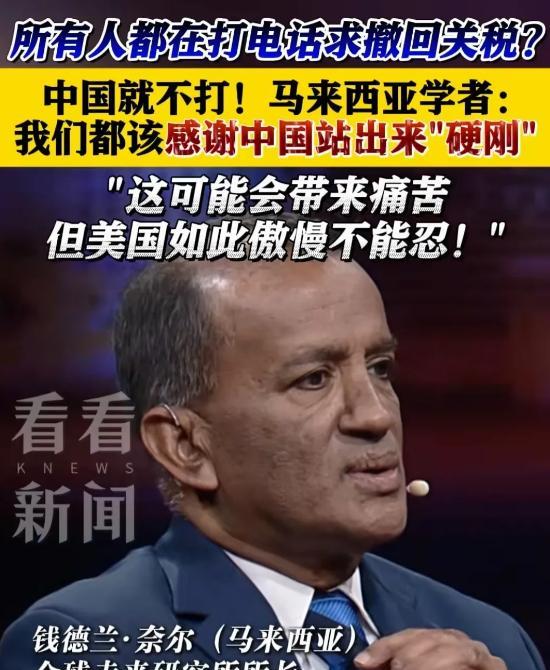作为美国后院,美国为啥不将南美打造成制造业基地?因为布热津斯基早就说了:拉美的角色是防止后院起火,而不是成为另一个德国!
南美又被称为拉美,南美只是地理概念,指赤道以南的美洲大陆部分,包括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家。拉美则是文化划分,语言殖民,蚀骨于无形。
15-19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等拉丁语族国家殖民南美,强制推行自己的语言,让其成为南美主流语言,与英语为主的北美形成对比。1836年,法国学者舍瓦利耶提出“拉丁美洲”概念。
目的是通过强调语言共性,为法国在墨西哥等地的殖民扩张寻找合法性,对抗盎撒文化的影响。同时抹掉安第斯文明、玛雅文明等原住民文化对南美的贡献,从文化、思维和精神等层面彻底控制原住民。
“欲亡其族,先绝其言。”剥夺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摧毁他们的文明基因库和民族记忆体。失去语言等于失去历史、思想和身份,这就是语言殖民的可怕之处。它会让受害者产生强烈的精神皈依,最终沦为精神买办,为殖民者辩护。
比如,英国人虽然已离开70多年,但英语的舌头依然卡在印度人的喉咙里,导致印度人至今仍以在伦敦买房为人生巅峰。
拉美独立运动之后,当地精英阶层用“拉丁”一词强化与欧洲文化的联系,试图构建一种区别于原住民和非洲裔的“文明身份”,但鱼不会因为学会鲨鱼的语言,就变成鲨鱼。
这就是拉美最大的悲哀,其骨子里有着深深的殖民依赖。就跟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似的,受害者不仅不仇恨迫害者,反而对其产生依赖、认同,甚至爱慕。所以,拉美几乎所有的悲哀都是命中注定的。
19世纪末,美国崛起,因为干不过英法德等新列强,只能暴揍老列强西班牙。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美国就把西班牙所控制的中美洲给抢了,进而大规模推行香蕉种植。
1904年,美国作家亨利在洪都拉斯创作小说《白菜与国王》,首次用“香蕉共和国”形容被水果公司操控的中美洲国家。其实,这就是典型的美式殖民,貌似好人好事,其实包藏祸心。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严禁“耕地非粮化”,就是耕地必须种粮食,不能种植“经济作物”。美国反而煽动其他国家大规模种植香蕉、菠萝和橘子等经济作物。为此,美国不惜长期压低主粮价格,提高经济作物价格,就是想通过控制主粮控制其他国家。
网上有个问题:如果全球都停止出口粮食,我们能否自给自足?高赞回答是:“够!因为我们每年能产10亿吨钢铁”,满脑子海盗殖民。
袁老为啥终生研究杂交稻和盐碱稻,为的就是防患于未然。它的口感或许不佳,但真到没饭吃的时候,谁还会在乎口感?其实,这就是为国铸剑,是否开刃取决于是否需要,正如钱老所说:手中无剑和有剑不用是两回事!
美国从一开始就没想让南美国家搞工业,而是将其定位为“原材料供应地”,而非工业伙伴,跟欧洲列强对非洲的定位如出一辙。所以,为了像摘香蕉一样攫取南美矿产、石油、大豆,美国一直把工业文明的种子锁在保险箱里。
1900-1930年,美国对南美投资中,矿业和农业占比高达78%,制造业仅为5%。1960-1980年,美国对南美军事援助达130亿美元,经济援助仅47亿美元……此外,为了防止身边出现工业竞争对手,美国对南美工业化采取了系统性压制。
1929年,洪都拉斯香蕉出口占全国收入87%,全国仅有3家肥皂厂和1家火柴厂。
1946年,庇隆在阿根廷推动工业化,美国不仅拒绝提供贷款,还操纵IMF施压,致使其工业化失败。
1960年代,巴西试图建立本国汽车工业,美国就通过“争取进步联盟”附加条款,强制巴西开放市场,导致巴西车企被通用、福特并购,最终沦为代工厂和组装车间。
1970年代,巴西航空工业依靠政府补贴崛起,波音就通过专利诉讼和并购施压,最终被迫使其将商用飞机业务出售给波音。巴西人说:“巴西航空工业卖给波音的那天,上帝在里约海滩上哭了,因为他老人家也没见过这么贵的卖身契!”
1994年,北美自贸协定生效时,墨西哥以为接住了“工业圣杯”,其实是饮下慢性毒药。此后,美国资本疯狂涌向墨西哥,大搞“分尸式制造”,让墨西哥陷入“工业植物人”状态。
2003年,巴西总统卢拉推出“工业强国计划”。但世行的贷款合同里却藏着毒丸条款:强制开放电信市场,导致巴西本土设备商破产率80%;强制削减关税,导致国外工业品如潮水般冲垮巴西工厂……
如今,在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贫民窟里,孩子们的梦想是成为足球明星或毒枭,没人想当工程师。巴西最受欢迎的职业调查中,制造业工程师排名第47位。阿根廷书店里,《如何移民美国》的销量是《工业设计手册》的20倍……
所以,美国不打造南美制造业基地的本质,是维护其全球价值链的等级制,因为它不需要一个工业化的南美,只需要一个为其提供廉价资源和消费市场的“永恒外围”。正如墨西哥谚语所说:种下甘蔗的地方,永远都长不出钢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