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4岁的贾平凹迎娶护士郭梅。洞房前神色慌张,支支吾吾提了个请求,郭梅听完泪流不止,抹着眼泪点头答应。贾平凹当场落泪,感慨:“现在死也值得了。” 1994年,《废都》炸出个大雷,封、禁、骂、讽,接连砸在贾平凹头上。 有人说文丑心也不正,有人指着他骂“文化流氓”,屋外风声正紧,屋内也不太平。 婚姻早已摇摇欲坠,韩俊芳陪着贾平凹走过艰难起步,却没能穿过沉默的高峰期,写作一头扎进“世界里”,身边人像影子一样被掏空。 饭不吃、话不说,纸上字句比人重要。 孩子慢慢长大,叫“爸”越来越陌生,屋檐下的“夫妻”越来越客气。 流言没停过,最多的,是那个茶馆老板娘的故事。 西安南郊,写作圈里传得神乎其神。一次笔会后,两人并肩回屋的照片成了“铁证”,哪怕事后说是同路借宿,信的人寥寥。 感情冷得像空屋,最后韩俊芳提了离,离得利落,孩子归她,姓还叫贾浅浅。 贾平凹拎包搬出家门,住进作协宿舍,人清了,名臭了,心也乱了。 没几天,住进了医,是内科病还是精神崩溃,说法不一,但人真的是瘦了,整天盯着窗户,医院里没人认出他来,除了一个年轻的护士,叫郭梅。 她不说多话,端水、擦身、换药,利索。 别的护士轮班,她却天天值,别人都当是调排班,其实贾平凹心里早明白。 一次中午醒来,听见她坐在窗边低声念《废都》的段子,说“写得是真好”,他当时没说话,眼眶热得像烧。 就这样,从“认得”到“懂得”,隔了三个月,病好那天,两人都没说再见,但没过多久,贾平凹开始频繁回医院“复查”。不是肠胃,是心事。 1996年12月12日,两人登记结婚。 新婚那晚,本该高高兴兴,结果气氛却沉着,一顿饭吃得闷,酒也喝不下几口。 贾平凹坐沙发上点烟,烟抽一半,突然冒出一句:“每周我要去看浅浅。” 不是请求,是惶恐,神色慌张,话卡在嗓子眼,像怕被拒绝又怕被问原因。 郭梅听着,眼圈红了,没生气,没哭闹,她只是点头,说:“去吧。” 这句话落地,贾平凹蹲在屋角哽住了。 这事就定了,从那以后,每周一次探望,风雨无阻。 郭梅从没拦过,反而有时候替他带礼物,或者自己先去打听女儿的近况,浅浅考级、换学校、生病,她都比贾平凹知道得早。 有一回贾平凹在外地采风,她直接替他去了女儿学校家长会。老师还以为是亲妈。 两人过得平稳,生活起了变化。 郭梅不管钱,不管稿子,不打听交际圈,也从不翻他的书桌。 贾平凹认识不少女作家、画家,来来往往都看得见,郭梅从没问,只说一句:“别让我难看。”他记住了。 1998年出《秦腔》,2002年出《怀念狼》,之后《古炉》《带灯》陆续上架。 那几年,他的笔仿佛捡回了光。 郭梅身边人都问:“你不怕他再红了变心?”她笑着摇头,“这人只要把心打开一次,就不会轻易关上。” 争议当然还是有,有人写文章说她“17岁护士”嫁给“名作家”,被骂“图名图利”。 一查,贾平凹1996年44岁,郭梅那年27,两人差了17岁不假,但不是“她17”。 错误数据一传十、十传百,媒体也懒得纠正。 郭梅不回应,一次采访说她“不关心外界怎么看”,只盼家里平静,她不高调,也不脆弱。 浅浅长大,称郭梅“是照进家庭的那束光”,从没喊过“后妈”。 2017年,郭梅因病离世。 葬礼简单,没有名人场面,贾平凹坚持“只请亲友”。 他一个人站在墓前,许久不走,后来写文章提到“有人用安静方式撑起全家”,未署名,但圈内都知道在写谁。 外头评价多,有人说这是“现代版雷峰塔”,她是那座塔下的观音,把贾平凹的“孽缘”全都渡了。 也有人说这是“理性版爱情”,无风花雪月,全是柴米油盐,靠理解、靠包容、靠一天天磨合出来的信任。 哪种说法都对,哪种都不全。 但有一点最实在:贾平凹从没忘记那个护士走进病房那天,光线斜着打在她脸上,他第一次想:活着,还能重新来。 参考资料: 郭于华.《贾平凹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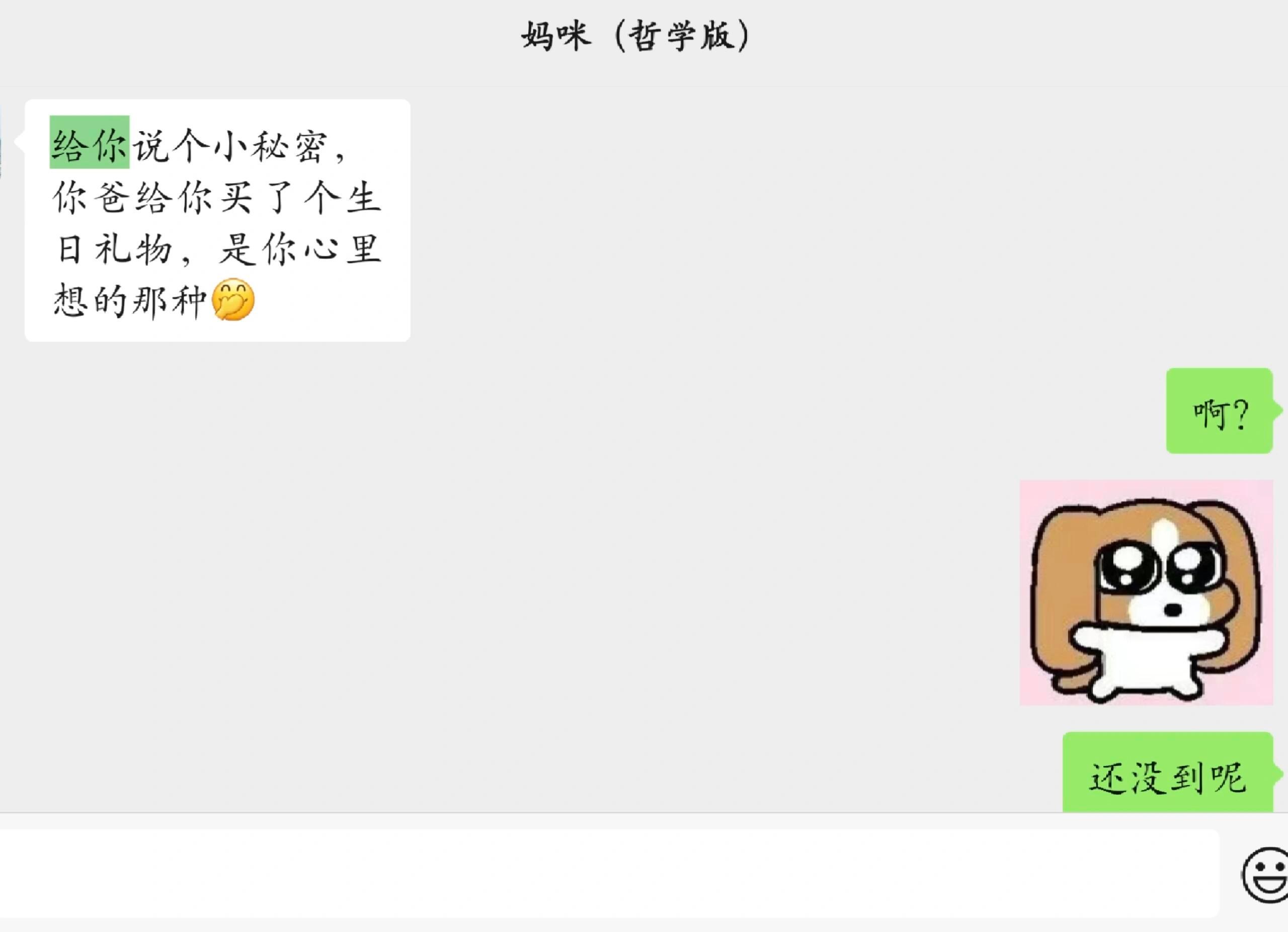
![你有多久没跳起来过?[doge]](http://image.uczzd.cn/11602674978975459808.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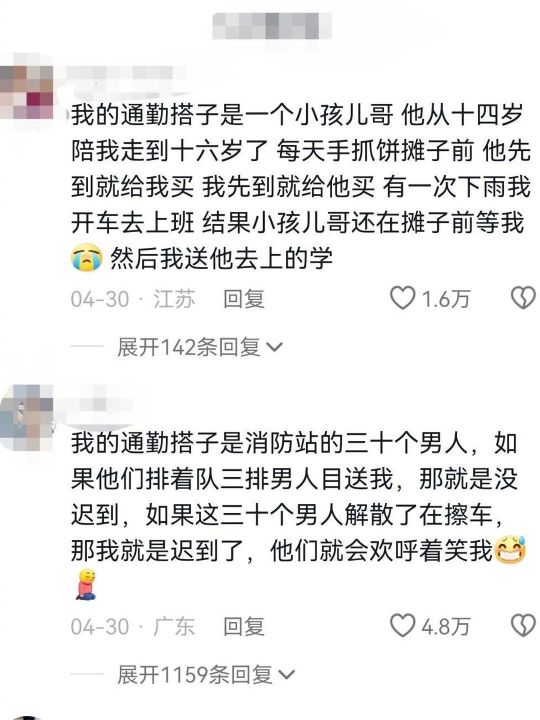

![又是梗图[doge]](http://image.uczzd.cn/5470036484712391298.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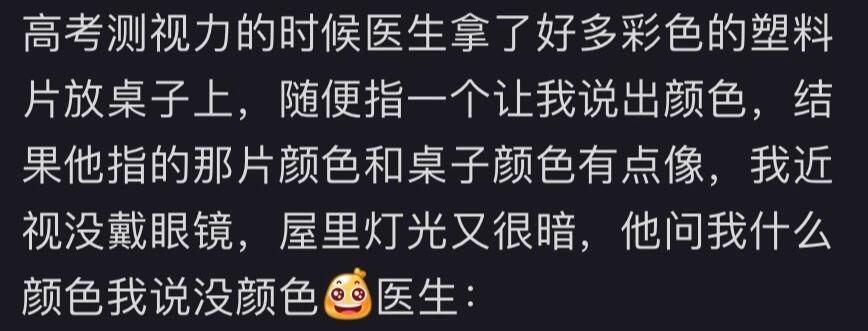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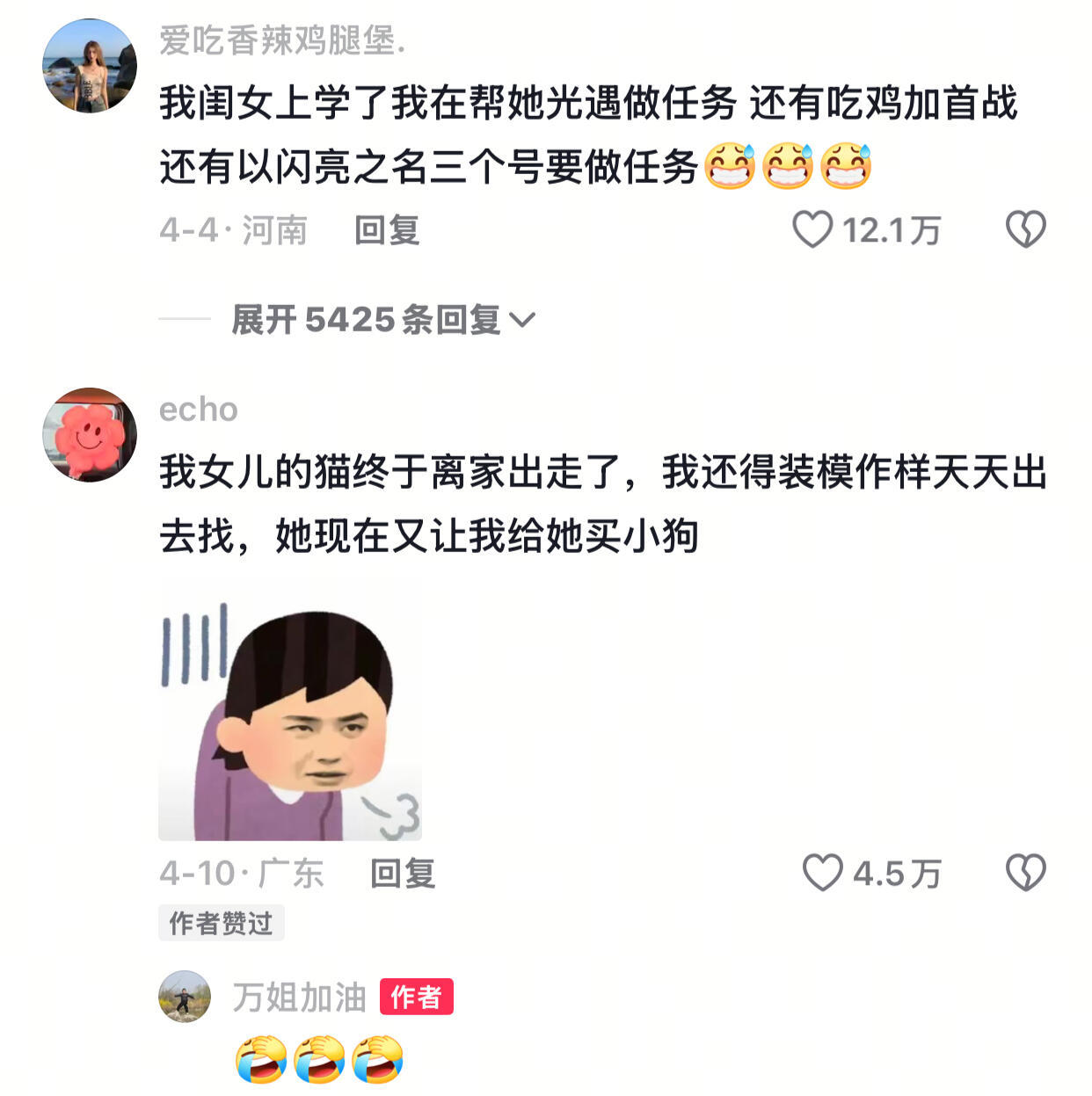

王家哥哥
在雪白的大地上。我尿了一条线,而你却尿了一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