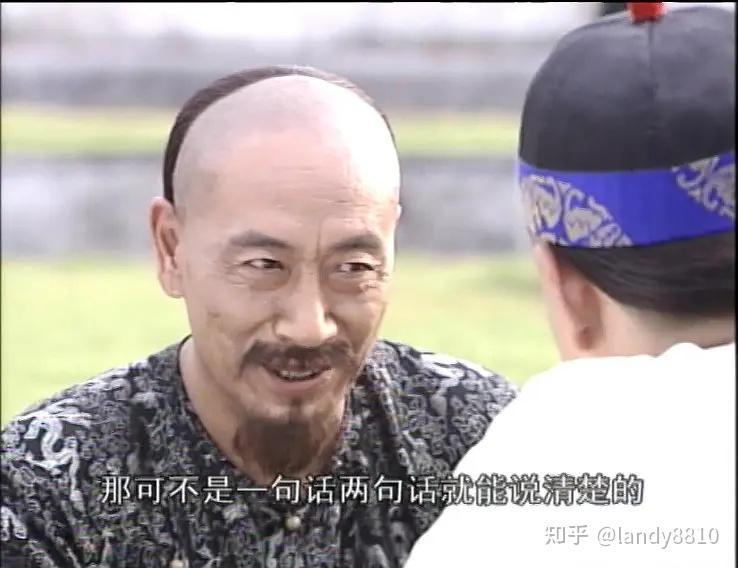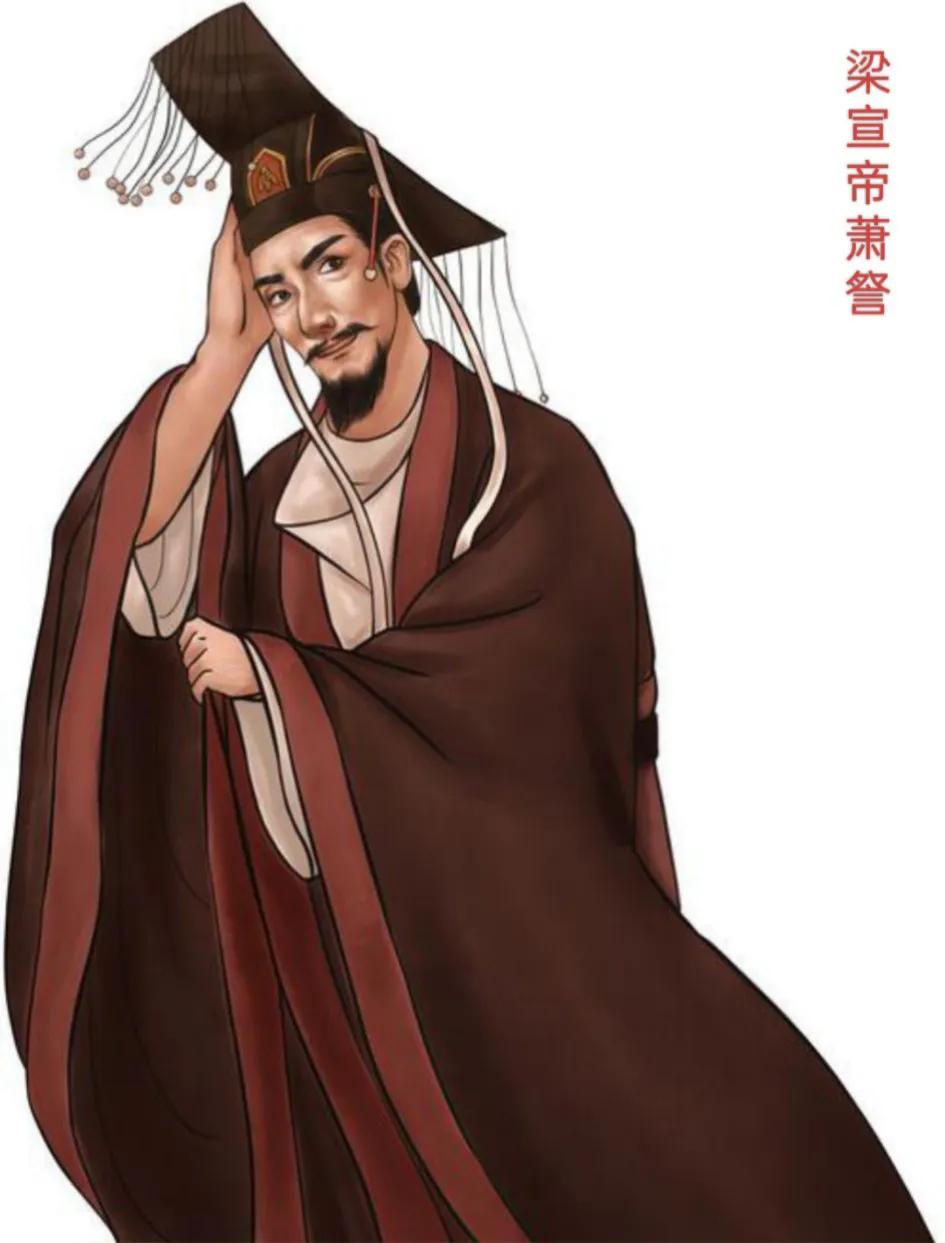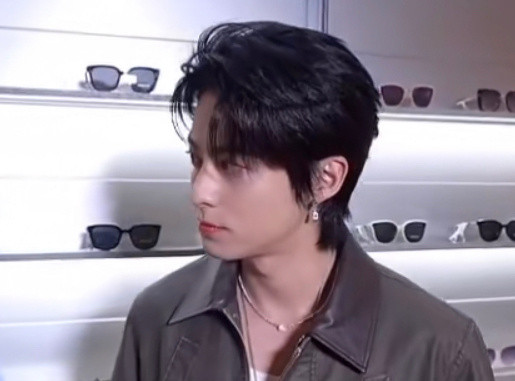1975年初春,82岁的毛泽东突然放下手中的《资治通鉴》,转头问身边工作人员:"功德林里,还有国民党战犯吗?"这句看似寻常的问话,掀开了新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页特赦篇章。 这座始建于金代的古刹,历经元明香火,到了光绪年间改作粥厂救济饥民。北洋政府时期,梁启超在此创办中国最早的现代监狱,青砖墙上至今还留着"京师第二监狱"的斑驳字样。 1949年后,这里成了专门关押国民党高级战犯的场所,杜聿明、黄维这些曾在淮海战役兵戎相见的将领,都在高墙内度过了人生最漫长的二十六年。 管理所档案显示,到1975年春天,这里还关着293名平均年龄68岁的战犯。他们中年纪最大的已经七十六,最小的也过了耳顺之年。 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们,如今每天的生活是读报、种菜、写思想汇报。黄维在回忆录里写道,他花了十五年时间研究永动机,管理所给他配了三个助手,虽然最后证明是徒劳,但这份宽容让他第一次对共产党产生了敬意。 毛泽东听取汇报后沉默了足足三分钟,工作人员记得,主席的手指在轮椅扶手上轻轻敲击,突然说了句:"他们老了,做不了恶了,都放了吧。" 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实则酝酿了二十六年。早在1959年首批特赦时,周恩来就提出过"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方针,但当时国际形势复杂,特赦工作始终保持着审慎节奏。 3月17日的人民大会堂里,特赦大会的布置颇费心思。桌上摆着红烧肉和黄河鲤鱼,每人面前放着崭新的中山装。 当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念完特赦令,现场响起压抑了二十多年的啜泣声。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接过特赦证书时,发现自己的手指在证书上抠出了汗印。更让人感慨的是,每人都领到了200元安置费——这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 这些获释战犯的去向成了大问题,有关部门原计划安排他们去工厂当技术员,但考虑到年龄问题,最终决定让愿意留下的担任文史专员。 杜聿明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整理淮海战役史料,这个曾经的华东剿总司令,现在要亲笔写下自己如何被解放军俘虏的经过。 最倔强的文强,也就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世孙,在接到编写《戴笠与军统》的任务时,苦笑着对工作人员说:"你们这是要让我自己揭自家老底啊。" 台湾方面的反应却让人心寒,当大陆通过红十字会给蒋经国去电,表示愿意送返想回台湾的战犯时,得到的回复是冰冷的拒绝。 原国民党68军政工处长张铁石,本已买好去香港的船票,得知消息后竟在旅馆自缢身亡。这件事深深刺激了其他战犯,原军统少将段克文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成了政治棋盘上的弃子,终于看清了谁才是真正的家人。" 1980年,黄维作为政协委员到井冈山考察,站在黄洋界炮台前突然老泪纵横:"当年要是早听共产党的话,何至于让百姓多受二十年苦。"曾经最顽固的战犯成了最积极的统战宣传员。 而功德林旧址在1986年被拆除时,施工队从墙缝里挖出上百封未寄出的家书,这些泛黄的信件后来被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成为那段特殊历史最鲜活的见证。 当年发放的200元安置费,有三分之一被战犯们捐给了希望工程。1995年杜聿明女儿从美国回来探亲,看到父亲每月领的300元工资,忍不住问:"您不觉得少吗?"这位曾经的东北保安司令大笑:"够买五十斤猪肉呢!共产党待我不薄。"这话被记者记下来登在《人民日报》上,成了改革开放初期最动人的统战故事。 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1975年毛泽东决策释放国民党战犯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