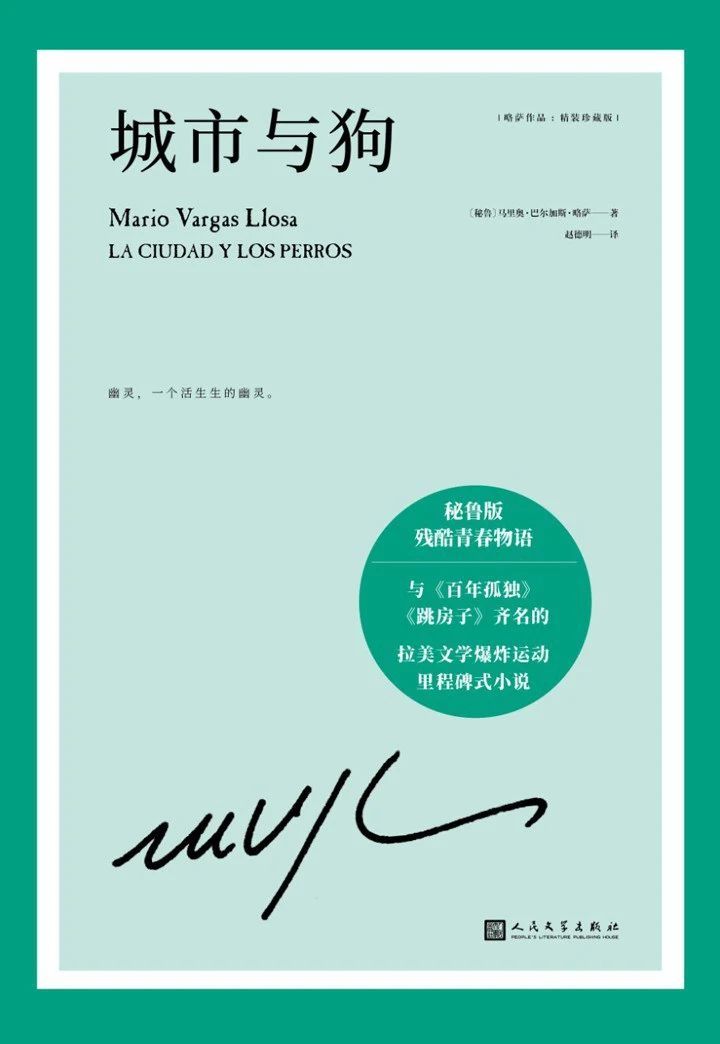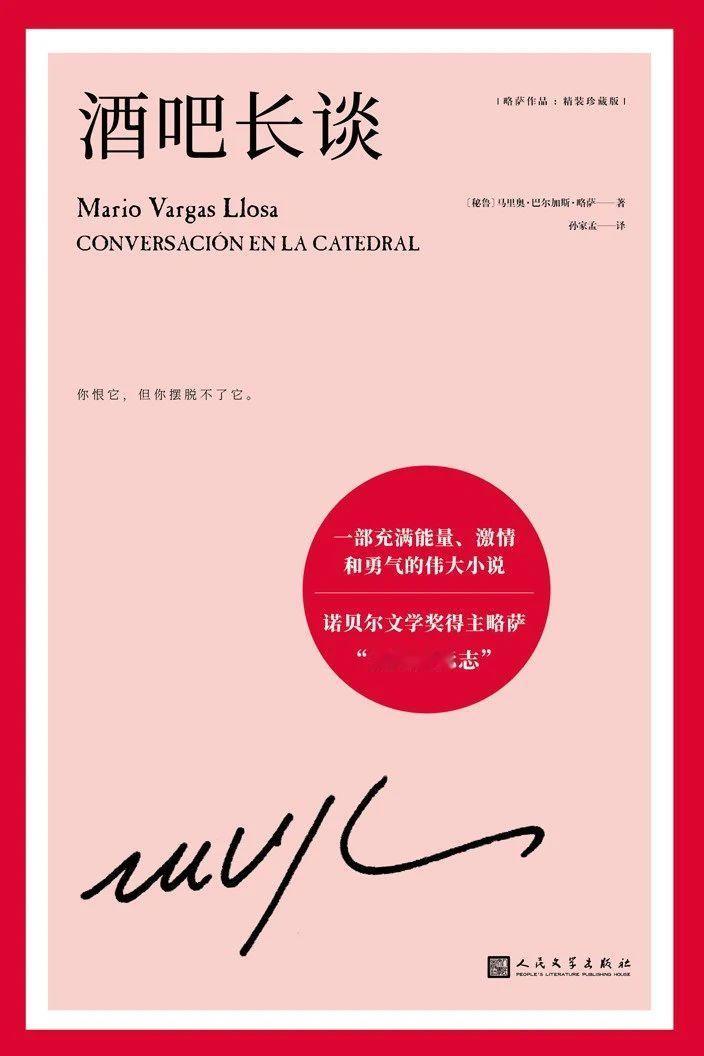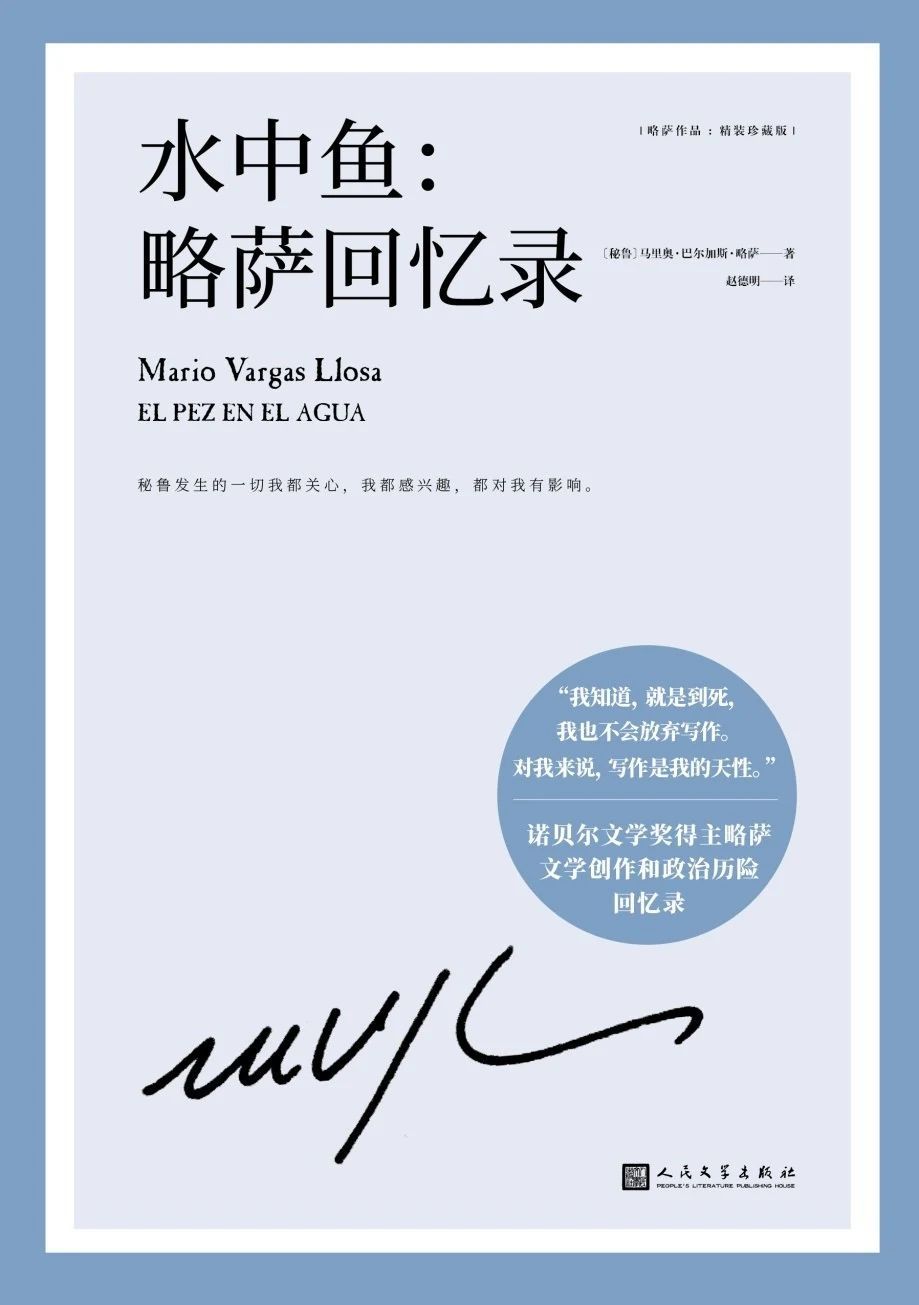深焦阅读纪念略萨 告别“弑神者”略萨,拉美文学最后的爆炸。
当地时间4月13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于秘鲁首都利马逝世,享年89岁。至此,“拉美文学爆炸”四主将均已离世,一个时代宣告终结。
然而实际上,所谓“拉美文学爆炸”在七十年代便已草草收场——终结它的还是略萨(在1971年的“帕迪利亚事件”中,略萨公开宣布反对卡斯特罗政府“以言治罪”,他本人被视为“左翼的叛徒”,“爆炸一代”拉美作家阵营也就此分裂)。是巧合也是宿命,尽管在早年的文论作品中,略萨将马尔克斯比作“弑神者”,但其实他自己才更符合这一称谓:“对于弑神者而言,写作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他们无法抑制极端的盲目反叛的冲动”。当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理想主义终将堕落为神话的戏码无可避免地反复上演,略萨也注定要反对所有恶龙与神话。
在“爆炸一代”的另一员大将何塞·多诺索看来,略萨是他们当中最可敬的人物,“当他对某种思想意识失望时就说出来,并且抛弃这种思想意识。哪怕你送给他黄金和宝马他都不肯隐瞒”。略萨只在乎他的小说与“末日之战”,因而并不会遗憾自己已然成为历史——已为陈迹正是对无休止的反抗者最好的奖赏。
“我妈妈拎着我从省政府的旁门来到大街上,我们向埃奇古伦防波堤走去。那是1946年底或者1947年初,因为我已经在萨雷霞诺考完各门功课,我已经念完小学五年级,那时皮乌拉正是夏天,阳光灼人,热得令人窒息。”
略萨的回忆录《水中鱼》开始于母亲带他去看父亲的那个下午,显然并非对马尔克斯经典开头的无谓戏仿,而是事实如此——随着与父权的正面遭遇,略萨的人生才真正开始。1936年略萨出生,然而在那之前4个月,他的父亲便不辞而别,“1935年11月的一个早晨,他装出一个多情的丈夫那样告别了怀有五个月身孕的妻子。”理由很充分,“我父亲的问题……比起他那坏脾气或者醋意更为本质、更为决定性的是他那种感觉。他总觉得我母亲来自一个姓氏响亮的家庭,而他的家则因为政治原因而贫穷、败落了”。
只是这种具有明显父权色彩的自矜与妒忌,最终还是让位给这种体制同样要求的精明——地位高于一切。1945年略萨的舅舅何塞·路易斯当选秘鲁总统,他的外祖父随即被任命为皮乌拉的最高行政长官,正是这一契机,促成了父亲在十年后的回归,“有一天,他开车去上班,在收音机里听到了任命佩德罗·略萨·布斯塔曼特为皮乌拉地方行政长官的消息”。信奉父权的个体往往既理想又现实:当他痛陈不甘乃至愤然出走,仅仅是因为现实开出的条件不够诱人。
对于父权——或者更具体地,对于封闭体制——的洞察,成为略萨第一部杰作《城市与狗》的主题。这部出版于1962年的作品主要取材于他1950年到1952年就读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自然是他的父亲认为他需要接受如此“历练”——的亲身经历。略萨最初将这部小说命名为“骗子们”,因为太过直白才做了修改——“狗”是高年级士官生给低年级士官生起的绰号。在略萨看来,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士官生们把学校看成某种修行场所,你必须经过很多阶段的磨砺……才能从狗变成人”。“同袍”之间没有真诚,只有利用,以至于书中一个人物只能与狗发生“亲密关系”——可以想见这样的人物即使熬出了头,又会怎样开始作为“人”的新生活。
阅读更多内容,可搜索“深焦DeepFocus”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