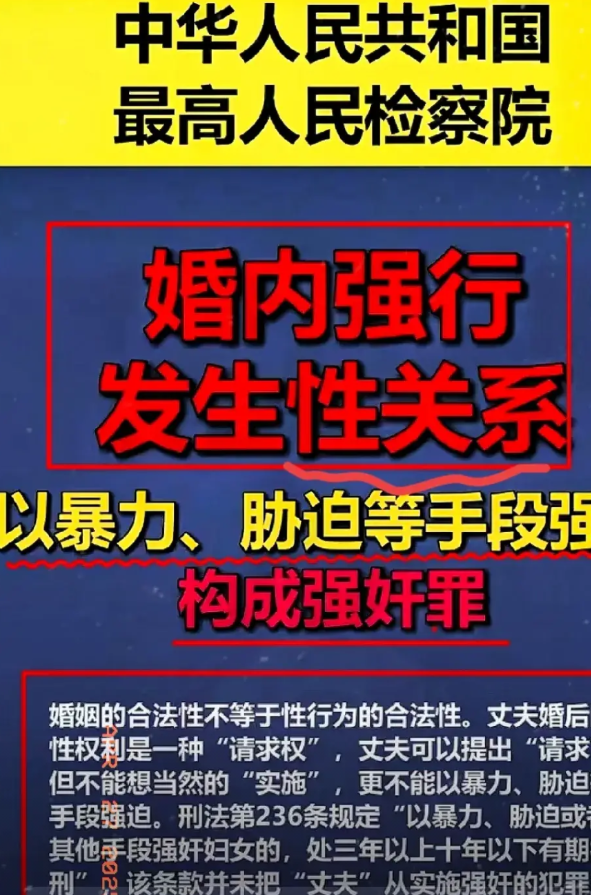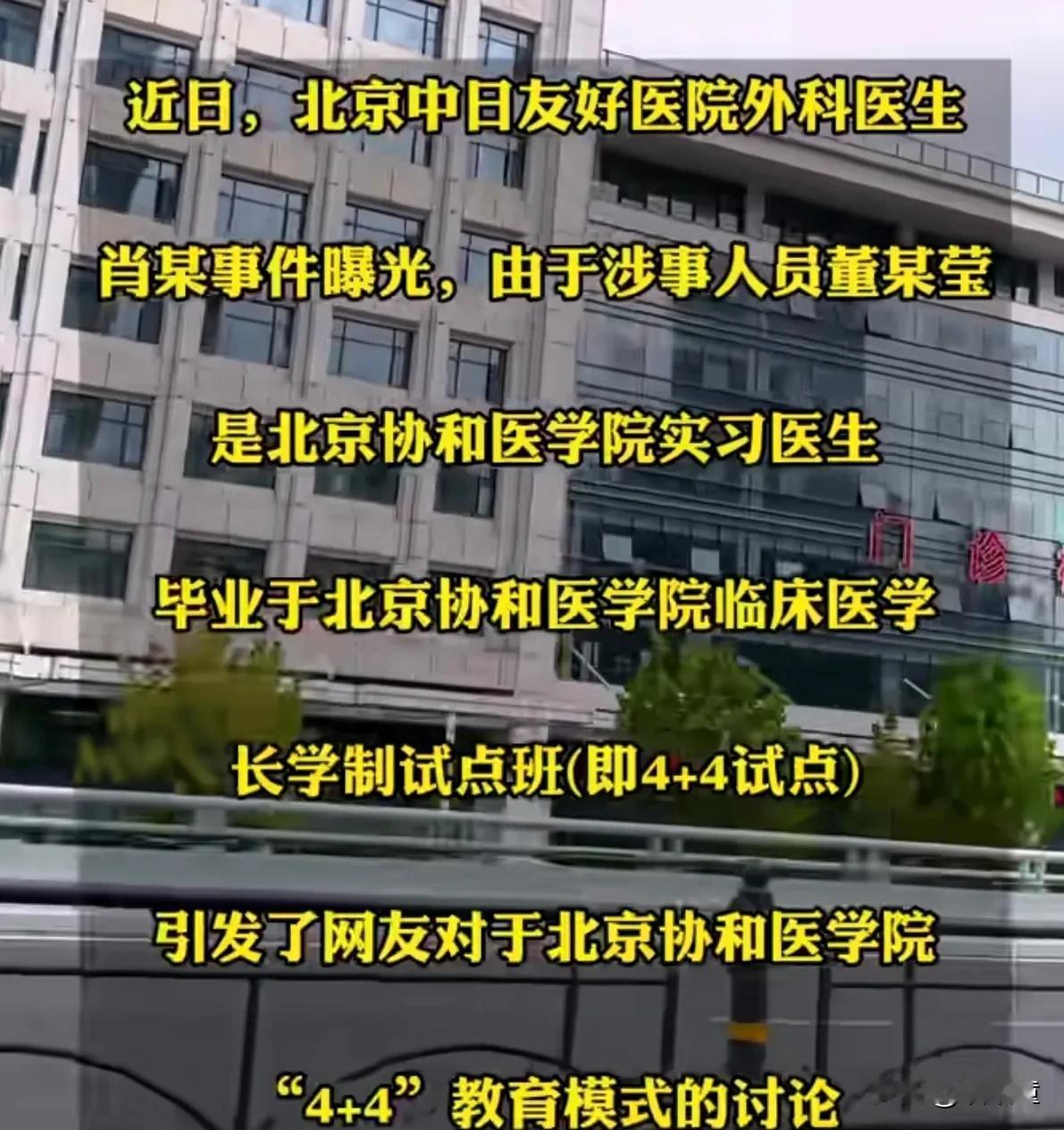1981年春天,武汉东湖宾馆里,一场看似寻常的老友相聚,背后却藏着生死边缘的隐隐较量。 83岁的叶剑英元帅,身体已经不如从前,笑着对80岁的何长工开了个并不算轻松的玩笑:“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还有两个月呢!” 何长工听了,立马回了句:“那这两个月可得仔细着点。”一句话,两人笑了,笑里藏着太多无奈和硬撑。 叶剑英来武汉,是为考察地方经济,这一年,他的身体已经被帕金森病折磨了三年多,走路僵硬,说话缓慢,肺部也总是感染。 医生一遍遍劝他休息,可他哪里肯,硬是带着医疗组出门考察,何长工这边听说叶帅到了武汉,马上赶到东湖宾馆,想见一面,两人上次见面,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见面那天,叶剑英穿着简单的灰色中山装,脸色略显苍白,走路也要人扶着。 他一边抬手招呼,一边笑着开了头:“你啊,比我小两岁,还敢说不中用了?”何长工赶紧笑着回敬:“谁还能跟你比啊,老头子还能下江南!” 说笑归说笑,何长工心里明白,叶帅的身体是真不行了,他那句“七十三、八十四”的话,不是没来由的。 这句老话在民间广为流传,说的是人在七十三岁和八十四岁这两道坎儿,最容易出事,叶剑英83岁零10个月,说得轻松,心里怕是也有点数。 这顿饭吃得不算轻松,席间叶帅几次咳嗽,医生轻声提醒他少说话,可他摆摆手,照旧谈天说地。 他讲起刚去山东烟台考察的事,笑着说:“那边的苹果好得很,吃一口,咬得嘎嘣响。”可说到一半,又咳了起来,身子一抖一抖的。 何长工见状,心里一紧,嘴上却打趣:“行啊,还能吃苹果,咱这身子骨比年轻人强。” 叶帅笑着眯了眯眼:“还能撑两个月,阎王爷再催,我也不着急。”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都笑了,可医生的脸色,笑不出来。 叶剑英的医疗小组早在两年前就提出过,希望他减少出差、减少外出活动,尤其要注意防止肺炎。 1979年,他被确诊帕金森病后,病情一年比一年重,特别是到1981年,已经发展到走路需要人搀扶,说话声音发颤,吃饭都得用特制的餐具。 免疫力下降后,肺炎成了常客,一感染就是高烧不退。 但叶帅性格倔,他总说,国家的事不能耽误,他亲自主持宪法修订工作,不顾医生反对坚持参加会议,还多次亲赴地方调研。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生死有命,咱干革命的人,怕过死?” 医生们只能尽量安排保障,比如出门配专车,随行带全套应急药品,每到一地,提前安排好医院。 可就算这样,意外还是时常发生,像这次东湖会面前几天,他在武汉小雨中巡视工地,回来后就低烧了,幸好抢救及时,没有引发更严重的问题。 何长工见到他时,正是叶帅状态最不稳的时候,两人聊了很久,从抗战谈到建国,从战场讲到经济。 他们谈起昔日战友,有的已经离世,有的卧病在床。,叶帅笑着说:“咱们算是剩下来的,得撑到最后。” 说到这,何长工沉默了一会儿,端起杯子碰了碰:“干一杯,不求长寿,只求不窝囊。” 屋里气氛突然沉了下来,只有外头东湖的水声细细的,叶帅轻轻点了点头,眯着眼慢慢喝了口茶,像是喝下了千斤重的岁月。 谁都知道,这次见面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医生不止一次在内部会上表示,叶剑英的病情到了不得不重视的阶段。 尤其是肺部,反复感染,一次比一次严重,一位随行医生后来回忆,说武汉那次,他们已经备好急救设备,只差开动了。 即便如此,叶帅坚持照原定计划完成了武汉之行,还抽时间见了地方干部,提出经济要“实事求是,别搞花架子”,语气坚定,听不出丝毫病态。 见完何长工后,叶帅坚持要到黄鹤楼转一转,工作人员劝了半天,他笑着摆手:“哪天走不动了,想看也看不到。” 一行人慢慢走到黄鹤楼下,他抬头望着楼顶,沉默了很久,像是把半生浮沉都装进了这一眼。 到了七月,叶帅肺部感染加重,不得不入院治疗。医生判断病情极为危险,但他坚持完成了山东烟台的视察,才肯回京。 回北京后,他几乎就没再外出了,此后几年,病情每况愈下,1984年肺炎加重,高烧不退,呼吸困难。 1986年更是三次发生心脏室颤,每次抢救都堪称与死神拔河。 1986年10月22日凌晨,叶剑英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89岁。 去世前的最后几个月,他仍然坚持看文件、关心国家大事。邓小平在悼词中评价他是“活到老,战斗到老的典范”。 那年东湖的一场对话,成了叶剑英和何长工最后的见面。 何长工后来回忆起那次谈话,说:“叶帅啊,笑着讲阎王,背后多硬气。”两位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用最轻松的话,说了最沉重的事。 一场见面,不止是老友重逢,更像是两个革命老兵对生命的最后告别。 他们用笑声掩盖病痛,用酒杯碰响岁月,用一段段旧事,抵挡住眼前不可避免的衰老与离别。 他们不是怕死的人,可谁又真能无所谓地看着时间一寸寸把自己带走? 东湖那天的风很轻,叶剑英抬头望着远处湖面,眼里有光,像年轻时在战场上看到过的晨曦一样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