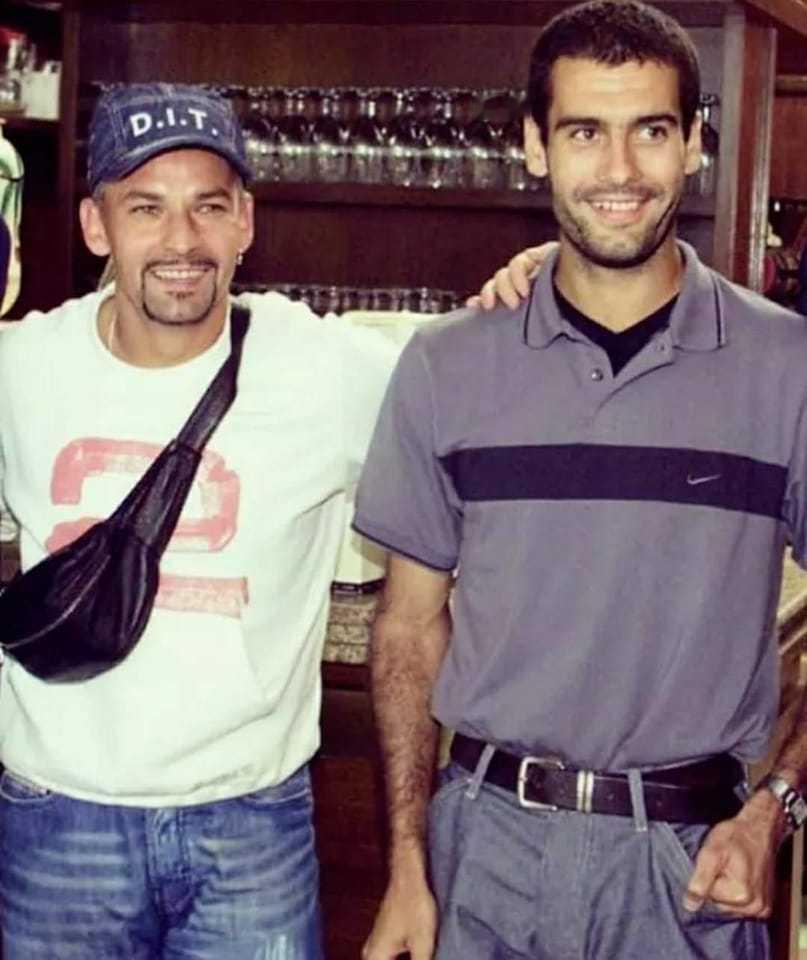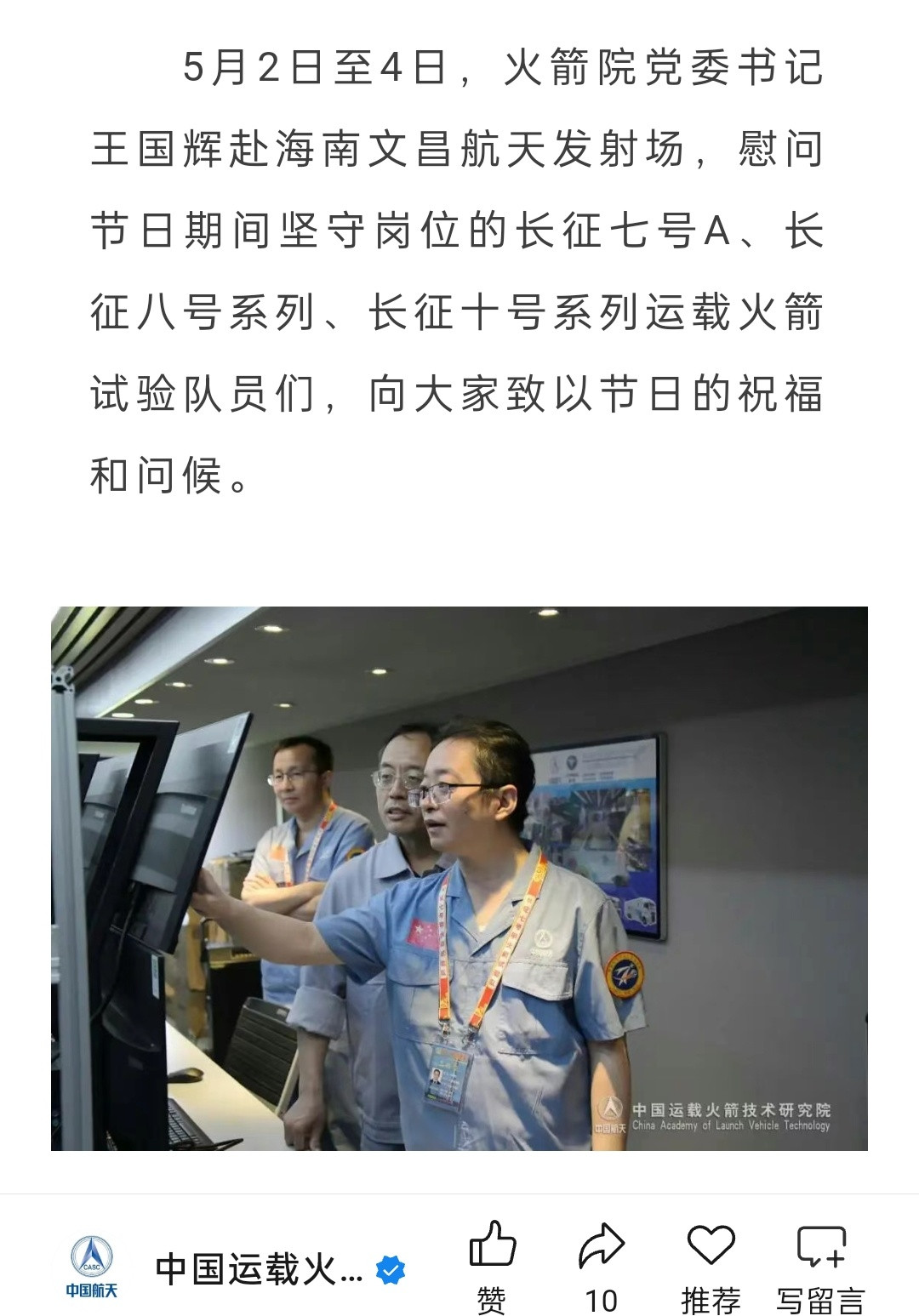1908年,外交天才顾维钧被迫回国与张润娥完婚,而他却在母亲房中躲了两晚,没想到第3天晚上张润娥找他同寝,顾维钧不肯碰她,她却说:“房间够大,床也很宽敞,你一个人睡足矣,从此沙发是我的。” 话音落下,房间里只余烛火摇曳的轻响。顾维钧望着眼前这个裹着红嫁衣的女子,烛光映得她眼底的倔强忽明忽暗。他满心愧疚,却又不知从何说起——留洋多年,他早已习惯了自由恋爱的思想,这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就像一副沉重的枷锁,压得他喘不过气。 张润娥转身走向沙发,嫁衣的裙摆扫过青砖地,发出细微的摩擦声。她动作利落地铺开薄毯,仿佛在整理一件稀松平常的家务事。“我知道你瞧不上我,”她背对着顾维钧,声音里听不出喜怒,“但既进了顾家的门,我也不会让你为难。”这句话像根细针扎进顾维钧心里,他张了张嘴,最终只吐出一声叹息。 此后的日子,两人在同一屋檐下过着近乎“分居”的生活。张润娥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每日晨起为公婆奉茶,傍晚操持饭菜,见着顾维钧也只是淡淡点头。邻里间开始嚼舌根,说顾少奶奶性子冷,新婚夫妻却像陌生人。只有张润娥自己清楚,她不过是把满心委屈都咽进了肚子里。 顾维钧常常借口公务早出晚归,有时甚至一连几日不回家。张润娥坐在空荡荡的新房里,对着镜子摘下珠钗,想起出嫁前母亲拉着她的手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对着镜中人苦笑,原来自己的一生,早在媒婆的三寸不烂之舌间就定了局。 直到有一天,顾维钧接到紧急调令,要远赴重洋处理外交事务。临行前,他站在玄关处,望着正在为他收拾行李的张润娥,突然有些说不出的滋味。“此去不知何时归,”他犹豫片刻,“家中父母,还望你……”“放心,”张润娥头也不抬,“我既嫁进来,便会尽好儿媳的本分。” 顾维钧走后,张润娥依旧过着平静的日子。她会在天气好的时候,陪着公婆在后院晒太阳;会在深夜里,就着油灯为顾维钧缝补衣裳,尽管知道他或许永远不会穿。
几年后,顾维钧寄回一封书信,言辞恳切地表达了离婚的意愿。张润娥握着信纸,指尖微微发颤,最终只是默默将信叠好,收进木匣——这个结局,她早有预感。 离婚那日,张润娥换回素色布衣,对着镜中的自己细细描眉。走出顾家大门时,她抬头望着湛蓝的天空,忽然觉得身上的担子轻了许多。
这场有名无实的婚姻,让她尝尽了苦楚,却也换来了后半生的自由。而顾维钧,带着愧疚与解脱奔赴新的人生,却永远忘不了那个在婚姻里默默退场的女子,用自尊与倔强,书写了属于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