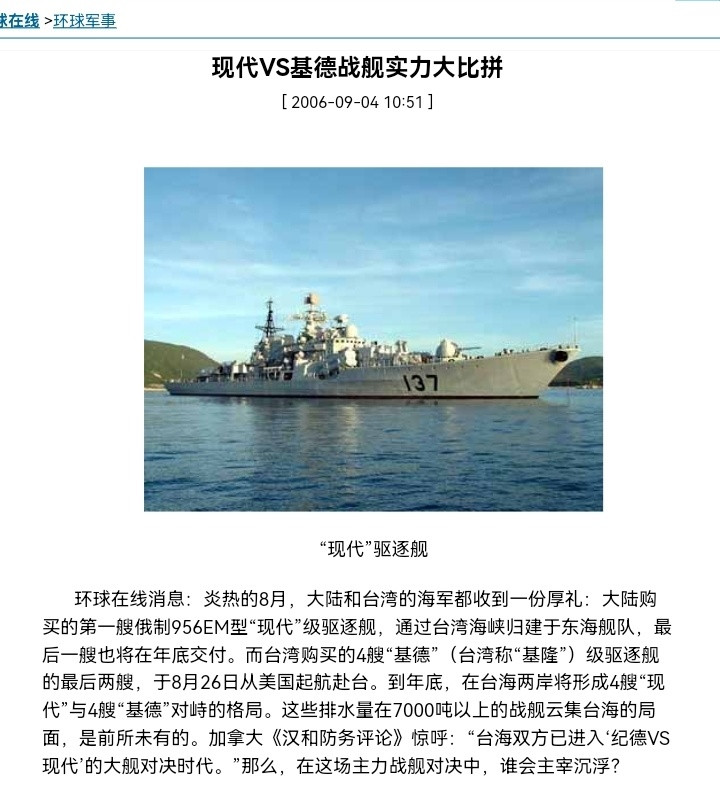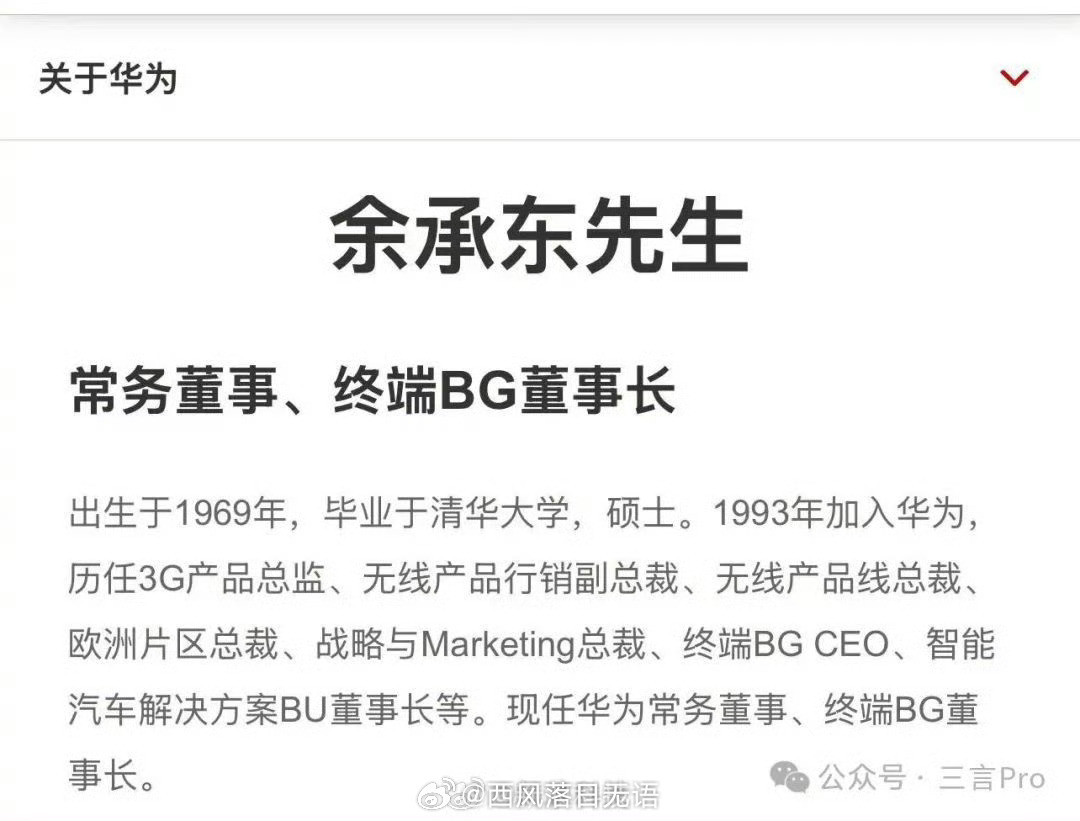填坑蹲战壕,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俄罗斯对伤亡承受能力很高吗?其实,都是爹生妈养的大活人,谁都怕死,关键在于死得值不值,账怎么算。 宗教国家的算法通常比较复杂,我们的算法相对简单粗暴。有位92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就掰着手指头算过:“我打死你一个,我死了,我就够本。我打死你两个,我就赚一个,我打的多,我就赚得多!” 这种战场算账逻辑主要源于抗日战争,因为武器代差问题,中日军队战损比很大。国军与日军战损比平均在5:1-10:1之间,中条山会战甚至打出了15:1战损比。 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战损比平均在1:1-1:3之间,百团大战甚至打到0.85:1。因为我们以游击战为主,伤亡率较低,但也因此催生出了“以命换命”的悲壮计算。 上甘岭战役,志愿军伤亡1.15万人,杀伤联合国军2.5万人,战损比约1:2.17。此战堪称钢铁与血肉对决方程式,联合国军倾泻190万发炮弹,相当于每秒6发,每平方米落弹76发。 但志愿军的坑道工事使得炮击杀伤效率仅0.7人/100发,远低于平原战3.2人/100发。美军原计划伤亡200人结束战斗,但最终数字超预期45倍,且从精神和心理层面彻底干趴了美军,以至于美军直到现在都有心理阴影。 单纯算经济账,美军此战耗费相当于2023年18亿美元,志愿军投入约0.3亿美元。美军每消灭1名志愿军耗资12万美元,志愿军每杀伤1名美军耗资2400美元。 俄罗斯老铁对战争伤亡的承受力,本质上是地缘文化、历史悲情、宗教救赎和经济理性所焊接起来的社会心理机制。这套系统可能在短期内有效,甚至可以展现出极强韧性,但是否长久则是个疑问。 最底层逻辑肯定是地理决定论,地处寒带,年均气温-5.5℃,西伯利亚冬季可达-50℃,严酷环境迫使俄国人发展出了极强的耐寒能力与心理韧性。冬季长达6-8个月,这就意味着一年要窝在炕上近200天,要是没韧性,早特么抑郁了。 每年农业周期仅3-4个月,迫使他们必须注重效率与储备,尤其重视行动优先,懒得瞎哔哔。比如俄乌冲突,事后证明这货压根就没做长期规划,而是先打起来再说,一副边打边看的造型,否则很快又是冬天了。 其实,地处北极圈地区,寒冷如刀,暴风雪可瞬间吞噬生命,导致俄罗斯人将死亡视为自然循环的一部分,不咋惜命。涅涅茨人至今仍保留着“将死者遗体留在雪原”的习俗,以此来敬畏自然力量。 另外,冷酷的气候让腌菜和伏特加成了他们应对食物短缺的生存智慧。俄罗斯年耗伏特加70亿甁,连血管里都流淌着伏特加。正如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的灵魂在伏特加的迷雾中寻找上帝,却永远迷失在自己的深渊里。 俄国诗人莱蒙托夫曾说:“在这广漠的国土上,痛苦更甚,欢乐更虚无。”当人陷入极寒所造就的虚无中时,为了刷存在感,“生存理性”就会压倒“生命理性”,而伏特加就是就是最好的生理燃料。 只要喝不死,就往死里喝。2023年,俄女性平均寿命77.8岁,俄男性仅为67.5岁,排名全球136,还不如印度男人呢! 然而,恰恰就是自然环境所造就的生命无常,让东正教成为了俄罗斯人的灵魂救赎,跟精神伏特加似的。东正教将严寒苦难包装成“赎罪之路”,导致65%的信徒认同:“死亡是通往永生的门槛!” 在东正教传统中,自愿承受苦难的“圣愚”被视为接近上帝的存在。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主角保尔柯察金,就是一位铁人式的狠人,在自己坚持的事业上走得一身伤痛,却无丝毫退意。 他甚至义正言辞的拒绝了美丽的冬妮娅,我小学六年级看这本书时,就觉得这哥们脑子有大坑。有看过这本书,且喜欢冬妮娅的老铁,可以在评论区来一波爷青回,祭奠下萌动的青春。 在俄乌战场上,瓦格纳士兵都是佩戴十字架赴战。在顿巴斯前线,士兵们也经常将浸信会教堂的圣母像绑在装甲车上,高喊“上帝与我们同在”冲锋。 经典操作就是:胸前挂着十字架,手里攥着圣经,包里塞满伏特加。阵亡遗书常见金句是:“上帝正在清点我的杀敌人数”。清点完之后,灵魂就可以得到升华,进入天堂。 正如东正教圣徒西蒙·沃林所说:“死亡不是终结,而是永恒生命的开始”。目前,58%的俄国大兵坚信,为国献身可以插队进天堂,相当于附赠“天堂VIP通道”。 抛开精神账,揭开英雄主义的外套,里面还藏着一本经济账。82%的阵亡士兵来自月薪2300元的贫困地区,当上合同兵就是月薪7000元起步。战死沙场,家属还能得到100万元人民币抚恤金,还有终身免税、免费医疗和子女高考加分等特权。 其实,俄罗斯人对死亡的忍受度,本质上是一场持续千年的精神淬炼,寒冷既锻造他们的钢铁意志,也孕育了他们宿命般的悲怆美学。 但当个体生存理性突破集体叙事框架时,这种“视死如归”的文化特质到底还能持续多久?无疑是对俄罗斯人最尖锐的灵魂拷问!拷问伏特加的纯度还能燃烧灵魂吗?拷问喀秋莎的爱情还能抚慰心灵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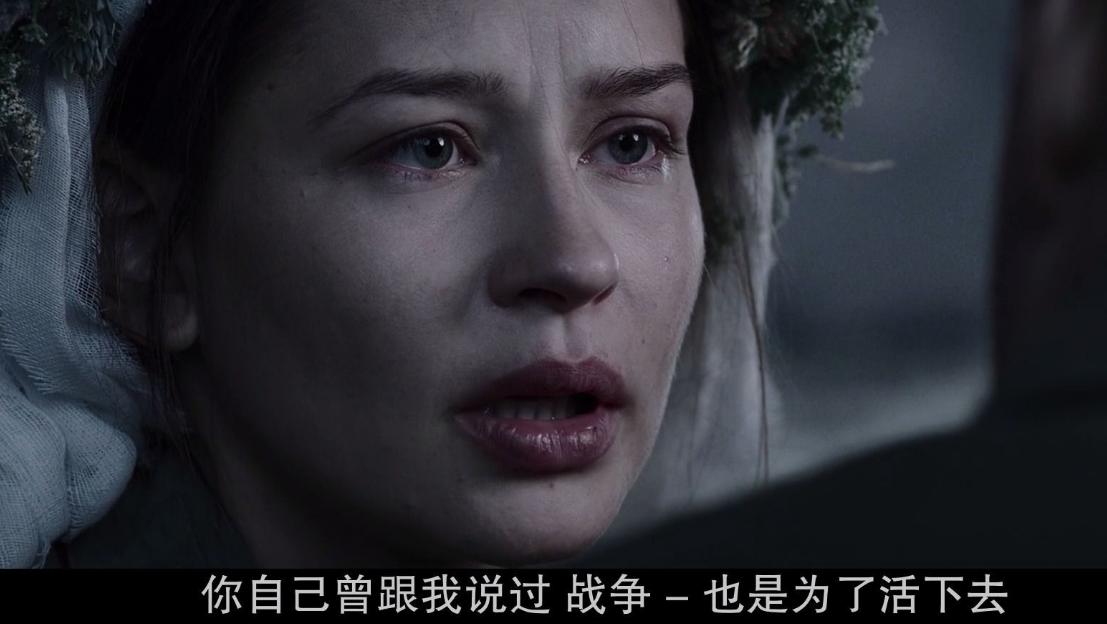







![歼50、歼36的假想图一个比一个好看[666]](http://image.uczzd.cn/1133514602724281644.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