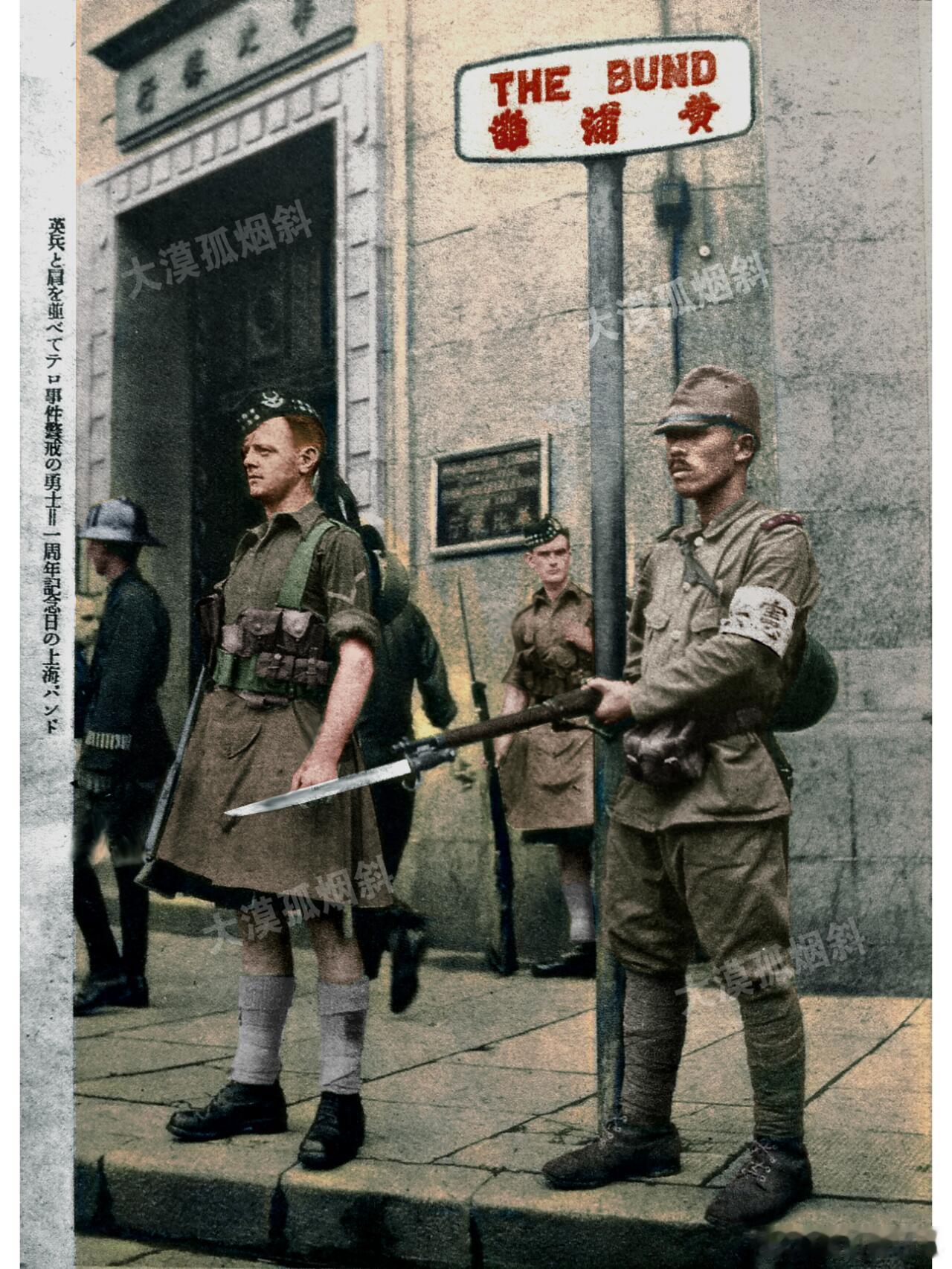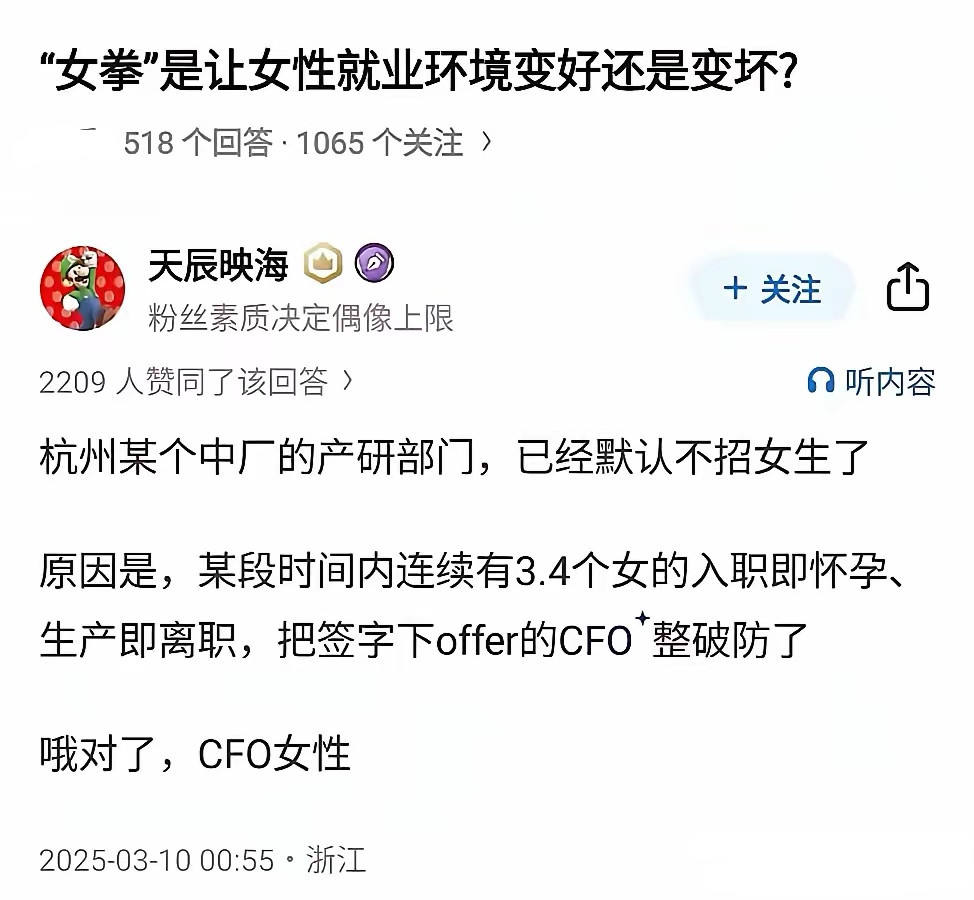1970年,上海女知青林小兰在分娩时遭遇难产,命悬一线之际,一位邻家老妇人挺身而出救了她。十年光阴流转,当林小兰一家即将踏上返城归途时,那位白发苍苍的老邻居突然拉住她的衣袖,声音颤抖着说道:"你们这一走,往后我这孤老婆子可怎么活啊......" 【消息源自:《上海知青口述档案:1970年代农村生活实录》2023-08-15 上海市档案馆】 煤油灯的火苗在林小兰手里抖得厉害。这张盖着红印章的返城通知书,她丈夫已经盯着看了半小时,纸面上全是汗渍晕开的圆圈。"要不...把娘带上?"丈夫突然开口,声音像被灶膛里的柴火烤过似的发干。屋外传来李老太哄孩子睡觉的哼唱,调子还是十年前从林小兰那儿学来的上海童谣。 十年前那个雪夜也是这样猝不及防。林小兰捧着滚圆的肚子在土炕上打滚时,李老太正把最后半瓶煤油倒进自制的小桔灯。六十岁的瘦小身影撞开风雪那刻,棉裤管已经冻成冰柱子,左腿那道被山石划破的口子结了紫黑色的痂。"接生婆说再晚半个时辰,你们上海姑娘的细骨头就要被娃娃撑裂喽。"后来李老太总爱用这句话吓唬不肯好好吃饭的孩子,却从不提自己瘸着腿摸黑走了十八里山路的事。 晒谷场边的趴趴屋里,李老太正用豁口的搪瓷缸给孩子喂鸡蛋羹。这是她拿三斤晒干的野菌跟邻村换的,瓷缸上"为人民服务"的红字早被刮得斑驳。"奶奶吃。"四岁的孩子突然把勺子往她嘴边送,李老太喉头动了动,只假装抿了口:"乖孙吃,奶奶在灶上留了糊糊。"这话飘进窗外的林小兰耳朵里,她想起上个月看见老太太蹲在茅房后头,就着井水啃她们吃剩的窝头渣。 公社书记来送通知那天特意强调:"政策允许带亲生子女返城。"他把"亲生"两个字咬得像嚼炒黄豆般清脆。李老太当时正在纳鞋底,针尖在发髻上蹭了又蹭,粗线穿过千层布的声音又密又急。等干部走远,老太太突然笑出声:"上海好啊,娃娃能坐电车上学哩。"可夜里林小兰起夜时,看见月光下那个佝偻的身影正用围裙拼命按着眼睛。 搬家前夜,李老太把十年攒的布票粮票全缝进孩子的棉袄夹层。"这些在上海用不上..."林小兰刚开口,老太太就变戏法似的摸出包东西——用红绸裹着的是一撮胎发、两颗乳牙,还有张按着孩子脚印的烟盒纸。"让娃带着,就当奶奶跟去了。"她说话时眼睛亮得反常,像是把后半辈子所有的光都攒到了这一刻。 火车站月台上,李老太的包袱突然散了。除了两件补丁摞补丁的衣裳,滚出来的是晒干的槐花、腌好的野莓酱,还有包得严严实实的荠菜种子。"上海水土金贵,种这个不挑地。"她弯腰去捡时,灰白的发丝扫过林小兰的手背,像十年前那盏小桔灯里跳动的火苗。列车员吹哨那刻,丈夫突然把户口本拍在检票台上:"等等!还有我娘!"三个鲜红的"随迁"印章旁,工作人员添上了第四个。 如今静安区老房子的阳台上,总有个戴绒线帽的老太太用旧脸盆种荠菜。有次居委会干部来登记,看见她正教重孙子念:"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年轻干部疑惑道:"您不是上海人吧?"李老太眯起眼睛笑,缺了门牙的嘴漏风:"咋不是?我闺女返城那年,可是把老骨头都背回来了。"楼下传来林小兰买菜归来的脚步声,塑料兜里活鱼扑腾的响动,惊飞了花盆边偷食的麻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