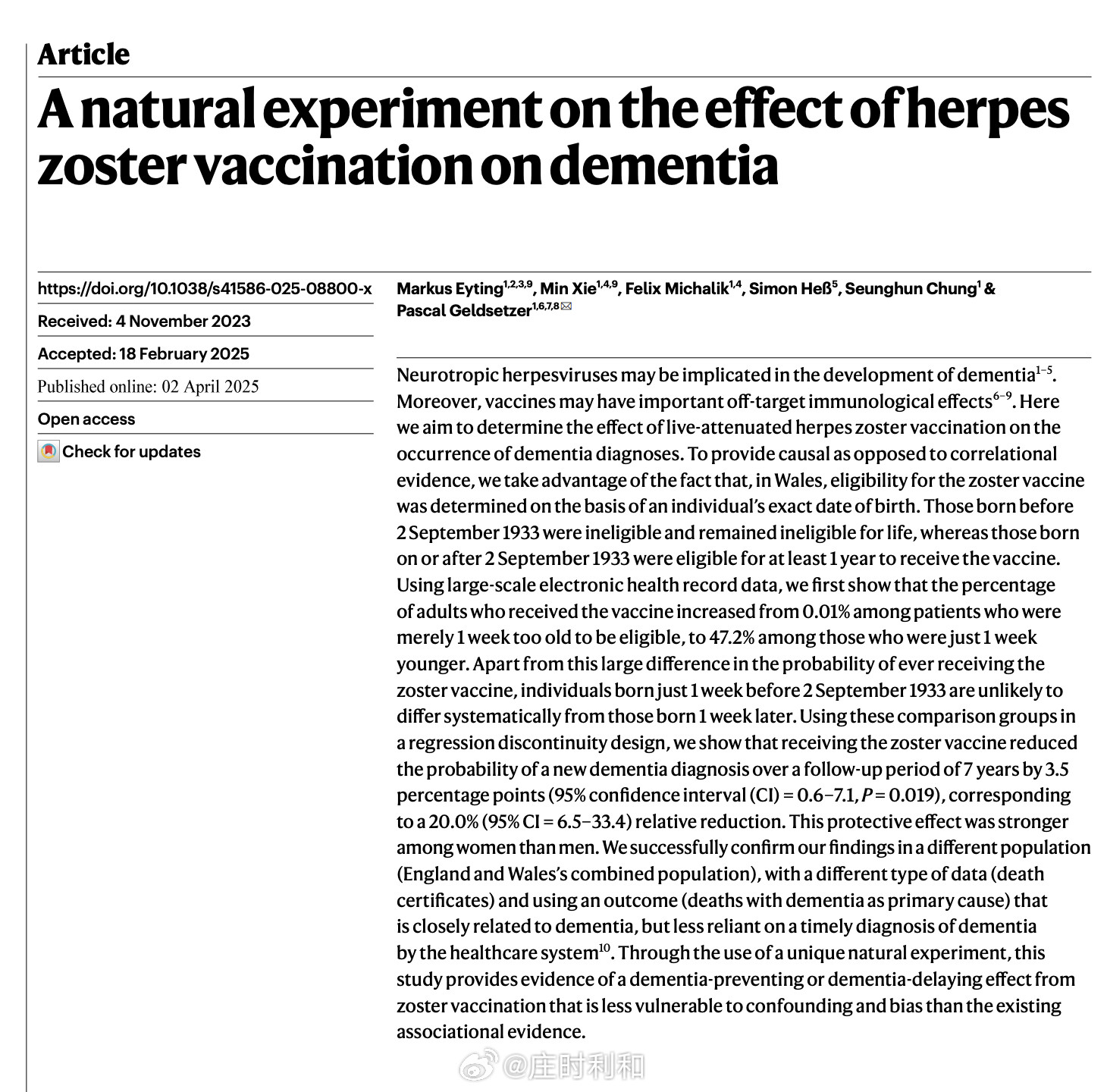1970年4月11日,强大的土星五号火箭从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搭载着阿波罗13号任务,将宇航员吉姆·洛弗尔(Jim Lovell)、弗雷德·海斯(Fred Haise)和杰克·斯威格特(Jack Swigert)送上本应成为人类第三次登月的旅程。不幸的是,这次原计划探索月球弗拉·毛罗(Fra Mauro)地区的任务,并未如愿进行。原本被许多人视作“例行公事”的一次任务,却很快让全球数百万观众守在电视机前,目睹和祈祷这一航天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能有圆满结局。
1969年7月阿波罗11号的巨大成功,以及随后阿波罗12号的顺利完成,使公众产生了一种错觉:登月仿佛已成为一种常规操作。与此同时,越战的持续也逐渐吸引了人们对阿波罗计划的关注。随着预算不断削减,阿波罗后续多项任务被取消,包括阿波罗18、19和20号。一些迷信者还注意到,即将进行的这次任务就带着“不吉利”的13号编号。而这些担忧似乎也并非毫无根据,一次麻疹感染的风险最终导致原定的指令舱驾驶员肯·马丁利(Ken Mattingly)被杰克·斯威格特临时替换。
任务开始就不甚顺利:在发射阶段,土星五号第二级的一台J-2发动机意外提前关闭。剩余四台发动机多燃烧了34秒,第三级也额外燃烧了9秒,才将飞船送入正确轨道。此后,任务仿佛重回“常规节奏”,以至于地面休斯敦的胶囊通信员乔·克温(Joe Kerwin)宣称:“飞船状态良好,我们这边都要无聊得打哈欠了。”但就在几分钟后,氧气罐2号发生爆炸,彻底终结了这种“无聊”。
机舱内的警报灯显示三组燃料电池中的两组失效,宇航员立刻向地面报告出现重大问题。洛弗尔从指令舱“奥德赛”号观察到飞船“正在向太空排放某些东西”,而那排放物正是任务生命线——氧气。进一步调查发现,2号氧气罐爆炸同时也损坏了1号罐,导致燃料电池无法继续工作,从而严重威胁电力与水源的供应。登月计划至此彻底取消,宇航员与地面控制人员开始昼夜不停地寻找解决方案,力保宇航员平安归来。
首要应对方案是进入所谓的“救生艇模式”——登月舱“水瓶座”(Aquarius)成为挽救整艘飞船与宇航员生命的关键。其完整的氧气罐与下降发动机为宇航员提供了生存和返航的保障。然而,除了严重的水源和电力短缺,宇航员还遭遇了危险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问题。虽然指令舱中有充足的氢氧化锂罐(用于清除舱内二氧化碳),但这些“方形罐子”却无法与水瓶座中的“圆形接口”配合。休斯敦的工程师们不得不真正实现了“方钉塞圆孔”的神操作。
阿波罗13号采取了自由返航轨道,用太阳作为导航对准星,逐渐接近地球。然而,还有一个巨大挑战尚待解决:如何重新激活长时间断电的指令舱。在常规情况下,这样的重新启动程序需要三个月才能编写完成,而这次休斯敦只剩下三天时间。一个重大问题是,舱内仪器上的冷凝水是否会在通电后引发短路。多年后,海斯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整个指令舱看起来像“被人用水管喷过”,他们只能“拿毛巾把一切都擦干”。幸运的是,通电时并未发生电弧。这也归功于阿波罗1号火灾事故后的飞船重新设计,电线增加了绝缘保护。
4月17日,宇航员们与“水瓶座”告别,并顺利在萨摩亚附近的太平洋洋面溅落。直到他们登上“硫磺岛”号回收舰,NASA和全世界的人们才终于松了一口气。阿波罗13号这一“成功的失败”所带来的经验教训被迅速吸收,并持续影响着NASA后续的任务安全与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