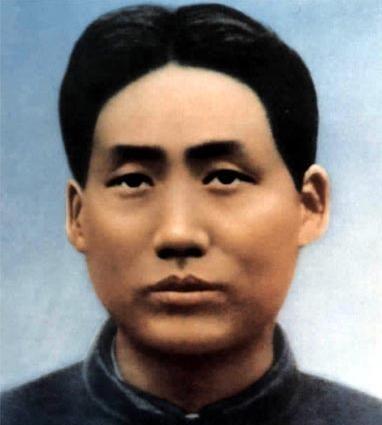1940年,皮定均看上了女干部张烽,就让县长去说媒,张烽听说了县长的来意后,拒绝道:“他条件很好,但我不想嫁给他!” 涉县刚打完一仗。鬼子被奇袭了,三百多号人,一个不剩,带队的是皮定均,这人从前线一路打上来,名字挂在墙上都能镇场子。 战后进城,县里人都在议论,说这回来了个硬茬子,不光能打,脾气也倔。 张烽听了没吭声,只心里冷笑一句:能打咋的?上战场死得快。 当时在县妇救会当主任,天天接收烈士家属,送物资、办丧事、安抚遗孀,身边的女人,一个接一个当了寡妇。她发誓:“军人不嫁。” 不是怕吃苦,怕的是送别,亲眼见过,战斗一开始,男人刚走,女人还没反应过来,骨灰盒就送回来了。 整个涉县,有几个女人真能守一辈子?更多的是熬死自己。 那天,郑晶华上门,跟她试探:“你听说过皮定均吧?现在在咱们县里。” 张烽头也不抬:“听过,不想认识。” 郑晶华有点尴尬:“他……挺看好你。” 张烽直接回了句:“让他别想了。” 革命是唯一,家庭是负担。 第一轮说媒,凉了,两年后,又有人来了,这回是谢富治的老婆刘湘屏,带着饭菜来串门,寒暄一阵,绕进正题:“定均还记挂你。” 张烽盯着她:“我说过,不谈恋爱。” 干革命,就得干个彻底,掺了感情,就是乱阵脚。 皮定均那边没死心,开始写信,信一封一封来,写得像检讨,又像日记,张烽不看,直接撕了,有时候连信封都不拆,原样退回去。 别人说她太硬,她不在乎,女人不硬,战场上怎么活? 真正拐点,是徐子荣来了,这人是五分区政委,皮定均的顶头上司,也是张烽敬的人,那天饭桌上,徐子荣笑着说:“皮定均不是什么花架子,他是真心实意。” 张烽夹菜,没接话,徐子荣叹气:“你怕什么我知道。但他这人,不光是战场硬。你要真不合适,我这做上司的,绝不撮合。 但我知道你怕的是什么,你不是怕婚姻,是怕失去。” 那顿饭吃得沉默,当天夜里张烽躺在床上,一句话在脑子里绕:“你怕的不是人,是命。” 后来收到一封信,开头有个错别字,把“烽”写成“峰”,她皱了眉头,往下读,越读越安静。 信不长,内容却细,他记得她爱喝苦丁茶、左耳有颗小痣、冬天手冷不爱戴手套。 她突然想问:战场上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怎么会注意这些? 没立刻回信,但也没再撕,过了段时间,两人一次共同行军,天突降暴雨,前线没吃的,皮定均把自己的干粮留给张烽,自己喝水顶着走了一天。 她问:“你不怕饿死?” 他回头一句:“你不在了,我打仗也没心气。” 那次,张烽没说话,只低头把干粮吃了。 三年,说不爱是假,扛住的,是不敢。 终于,1943年6月,张烽点头了。 结婚那天没婚纱,没鞭炮,就一顿“肉煮萝卜”,两菜一汤。 吃饭那会儿,外头还传来枪响。有人在讲:“你们这婚礼,枪声当礼炮了。” 结完婚转身上前线,婚姻不等于安稳,该打仗还得打,孩子出生那年,1946,中原突围时张烽怀孕还在前线,敌人特务追击,条件太差,途中早产,孩子保不住。 那夜,躺在山林里,她痛到说不出话,孩子没气了,连埋的力气都没有。 消息传到皮定均那儿,连夜赶来时,只剩一个小包袱。他一言不发,在风里站了很久。 那次之后,张烽才算彻底明白,战争不是“怕不怕”的事,是一场谁也躲不开的宿命。 婚后也不常见面,分分合合,跑在各自的阵地上。孩子寄养在老家,张烽说:“你守战场,我守后方。” 直到1976年,消息突然传来:皮定均空难去世。 电话那头的声音像刀子划过耳朵。 那一刻,没有眼泪,只有一声:“走得太快。” 张烽独自活了几十年,没再嫁,也没改姓。晚年病重,亲自写下遗愿:“骨灰一半埋涉县,一半葬武汉。” 有人问为什么分开。她说:“他打下的地方,我都要陪着。” 张烽一直说,她嫁给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份信念。 哪怕开始再拒绝,到最后,终究还是没躲过心。 她不是谁的附属,也不需要谁来成就。她是张烽,是那个曾说“军人不嫁”的女人,最后亲手守住一个军人的一生。 参考资料: 《太行妇女志》,中共涉县县委党史资料办公室编,1994年版,第213-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