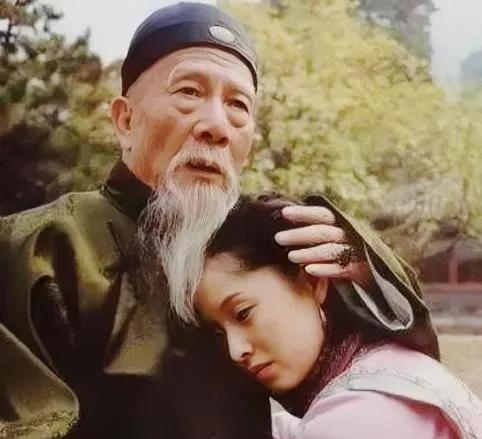张勋晚年闲居在天津的松寿里,独留花白辫子不放,有人劝其要识时务,他手捏辫梢,学着杨小楼的京剧念白说道:“吾回天无力,尚可独善其身。脑袋在,辫子不掉!真吾大清股肱之臣。” 麻烦大家点一下右上角“关注”,可以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见解,感谢分享与支持哟! 他为何这么钟情于大清朝呢,这个人的极端程度你想象不到。 就他说这话,周围人听了,怕不是吓得掉头就跑。 光绪二十一年,当那封盖着朱红御印的调令送到张勋手中时。 他正蹲在天津城外的野地里啃冷窝头。 20年前那个被继母卖给戏班子的瘦弱少年,此刻紧紧地攥着这封圣旨。 这是能让他重返奉天的东西,因用力太狠,手指关节处已经泛白。 野风卷着沙砾,拍打在他满是刀疤的脸上,却吹不散他眼里的狂喜。 他想哭——39岁的张勋终于等到了这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大清给他的恩典,让他常在营帐里对亲兵嘶吼自己的忠诚。 他的每道皱纹里都刻着偏执,离不开他幼年时被继母虐待的经历。 用火钳烙在后背的疤痕,此刻化作偏执的信念。 当其他将领在营房里讨论维新变法时,他总把佩刀拍在桌上: 没了圣上,咱这些泥腿子算个屁! 这种近乎病态的忠诚,让他在袁世凯的帐下如鱼得水。 那些被新式学堂熏陶的同僚,都笑他迂腐。 却不知这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武夫,正把每道军功都看的无比重要。 当成了他向皇恩报恩的投名状,包括1901年深秋的銮驾返京路上的事。 当慈禧的凤辇碾过保定城外的黄土路时,这个总兵大人正趴在泥地里。 他居然用腰带——死死勒住痔疮发作的臀部。 冷汗顺着他青筋暴起的脖颈往下淌,染红了靛蓝的官袍后襟。 可他像头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困兽,死死盯着那抹明黄流苏,任凭血水浸透裤管。 张大人这是不要命了么,李莲英掀开车帘时,正撞见这幕骇人场景。 李公公也做不到如此“忠诚”,月光下,张勋扭曲的面容。 看上去比戏台上的包公还要狰狞,后襟的暗红血渍,像朵诡异的曼陀罗。 老太监的拂尘在掌心攥出裂帛声,他忽然想起三十年前。 自己还是小太监时,在御花园偷听御前会议时,也是这般战战兢兢。 这个新晋太监总管从未见过如此虔诚的武人,他望着张勋渗血的袍角。 恍惚间竟想起自己初入宫情景,那时他跪在冰凉的青石板上。 看着先帝的画像,连呼吸都带着颤音。 如今这个满身血污的武将,竟让他生出种诡异的亲近。 或许都是被命运肆弄过的人,才会对恩典有这般病态的执着。 张大人这血,倒比咱当年给老佛爷上香还诚。 小德张抹着眼泪,用沾血的手帕给张勋包扎伤口。 这个总兵不知道,自己跪着的对象,从慈禧变成了张勋。 而这份虔诚,正在悄然改变着紫禁城里的权力格局。 当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是否也注意过这个在銮车旁站岗到天亮的武将。 此刻的李莲英,终于读懂了这个让慈禧流泪的疯子——原来愚忠,也可以这般惊心动魄。 他摸着怀表,想起自己初入宫时,不过是个给端茶倒水的末等小太监。 而眼前这个总兵,却用这种近乎偏执的忠诚表示决心。 这个被继母卖掉、在戏班子里挨打,却死死攥着"大清"二字的戏服少年。 用三十年光阴换来的千人之上,不允许被推翻。 所以,他的长辫子成了最后偏执的证据。 1917年7月的第一天,他再次上书,带头要求复辟。 皇帝都惊呆了,可能心想:真该你来当这个皇帝啊。 晚年的时候,满大街都是剪了辫子的新青年。 他倒好,每天天不亮就对着铜镜梳他那根花白辫子。 仿佛辫梢上系着大清的龙脉,有人隔着墙头喊他"辫帅"。 他倒得意,说这是对老佛爷的念想。 活像戏台上的忠臣,可大伙背地里都笑他迂。 如今百年过去,我们再瞧这话,倒品出几分悲凉。 这老古董怕是把辫子当成了命根子,剪了辫子,连带着把二十岁被继母卖进戏班时。 那个没饭吃还要给师父倒夜壶的苦命娃,都给剪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