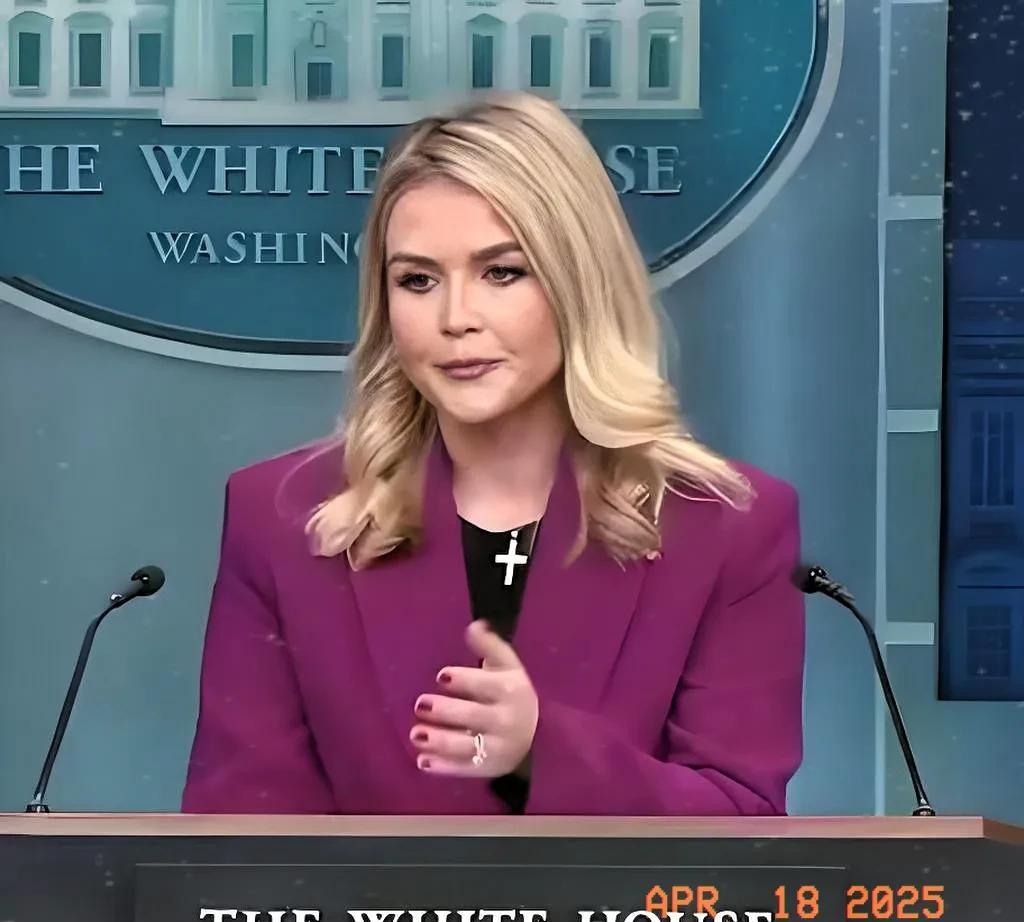“没有国家的强大,你永远只是二等公民,甚至是狗。” 一个中国人在国外被人指着鼻子骂“滚回你的国家”,周围人却视若无睹,他只能默默咽下这口气。为什么?因为在那个瞬间,他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的影子。 国家弱,他在外面就是个没人瞧得起的“外人”;国家强,他才能昂首挺胸地反击。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赤裸裸的现实:没有国家的强大,你永远只是二等公民,甚至是狗。 1934年,曾宪梓出生在广东梅县一个清贫的客家家庭,祖上世代务农。 小时候家里连鞋都买不起,他总是赤脚上学。梅县山区闭塞,物资短缺,但他从小成绩优异。靠着奖学金和乡亲们的接济,他读完了中学,并凭借优异成绩考入广州中山大学。 那时的中山大学实行奖学金制,对贫困学生提供补助,他因此得以完成学业。1961年,他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因学术交流机会被派往香港,但由于历史原因滞留当地。 初到香港,他一无所有,语言不通、身份未定,只能打零工维生。 1968年,社会动荡加剧,他辗转做过苦力、仓管、销售,甚至摆过地摊卖布料。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挑货至旺角,重雨,湿衣,夜归,得钱四元。”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整三年,直到他开始认真思考创业。 香港当时是加工贸易中心,西服盛行,但曾宪梓敏锐地发现——尽管满街男装,却几乎没有专门做领带的厂商。 他反复调查后,确认这是个被忽视的空白市场。他找到了在港经商的叔叔,开口借6000港币作为启动资金。叔叔起初犹豫,但最终还是答应了。 1971年,他在深水埗租下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老房子,将其改造成小型领带生产车间。起初他希望招几个工人,但因为没有订单,没人愿意来。 他便和妻子便自己动手,亲自裁布、熨烫、缝合、包装。一开始他们做的是低档领带,单价低廉,一天到晚拼命干也挣不了几个钱。 那段时间,他曾多次在账本上写下“负增长”三个字。夫妻二人曾连续一周吃白粥加咸菜。他心里开始明白,做廉价货赚不到出路,于是决定孤注一掷,转向高端市场。 为提升工艺,他在中环一家日本百货买回多条进口高档领带拆解研究。他记录布料纹理、缝合结构、压边技巧,还把欧洲流行的款式剪裁学了个遍。 首批样品做成后,他并不急于销售,而是联系香港几家高端成衣品牌,免费提供样品试销。 不久后,有三家男装店与他达成合作,产品一推出便引发关注。那时香港正值外贸兴盛,商务男装市场快速扩张,他的领带因款式新颖、做工考究,迅速在市场上站住脚跟。 1970年,他注册“金利来”(Goldlion)品牌,寓意为“黄金狮子,尊贵吉祥”。品牌成立第二年,营收已破百万港币。那一年,他重新装修了厂房,并开始批量出口东南亚市场。 他刚刚申请公司执照、准备大展拳脚时,香港经济却突遭打击。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进入汇率浮动时代,香港作为外向型经济体受到连锁影响,市场信心动荡,物价、股市、楼市均陷入低迷。大批商品因库存积压而降价求售,消费市场竞争激烈。 面对同行纷纷降价求生的局面,曾宪梓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逆市提价。 他认为,如果继续走低价路线,只能与无数小作坊拼成本、拼人力,无法建立品牌价值。他将领带价格提高至市场平均价的两倍,并在广告中高调宣称:“不是每个人都配戴金利来。” 此举引发争议,却奇迹般地激起了上流社会的追捧。当时的香港正值消费阶层上升期,富人群体在寻求“可见的尊贵符号”,金利来正好填补了这一心理空缺。短短一年,销售额翻了三倍,公司走上了快车道。 1974年,他扩大工厂规模,正式推出“金利来男士系列”,涵盖皮带、皮鞋、皮具、衬衫等多个品类,形成男士商务形象一体化方案。广告语“男人的世界”在港九各大公交车、地铁、电视台频频出现,深入人心。 到1980年代末,“金利来”在香港几乎无人不识,门店遍布各大商场。曾宪梓也多次荣登《亚洲周刊》《南华早报》的封面人物,被称为“香港服饰之王”。此时,他的身家已达百亿港元,成为粤籍华商的代表人物之一。 真正让他声名远播全国的,是他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行动。1978年底,他是最早一批响应“到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家之一。 他先后在广州、深圳、梅州等地设厂建校。1983年,他斥资修缮母校梅县中学,并设立“曾宪梓奖学金”;1986年,他在广东开办“金利来工艺学校”,帮助农村青年技能培训。 至2010年,他通过各种渠道累计捐资达11亿人民币,涵盖教育、医疗、扶贫、文化遗产保护等项目。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国家给了我知识,我只是还债。” 即便在年逾八旬后,他仍不肯歇脚。2018年他被选为北京奥运火炬手,他笑言:“我虽然老,但能走,就要为国家跑一程。”那年他还被评为“感动香港年度人物”。 2019年9月20日,曾宪梓在香港病逝,终年85岁。家人按照他的遗愿,未举行奢华葬礼。他在遗嘱中写下:“我的遗产交国家安排使用,不留给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