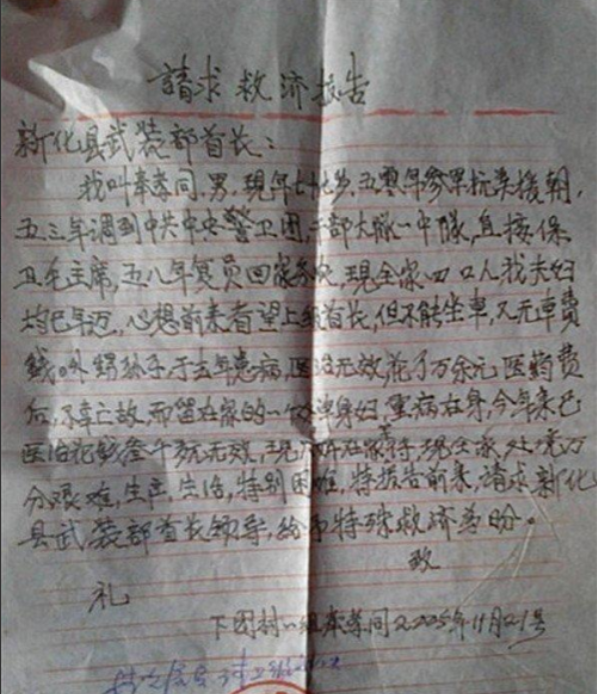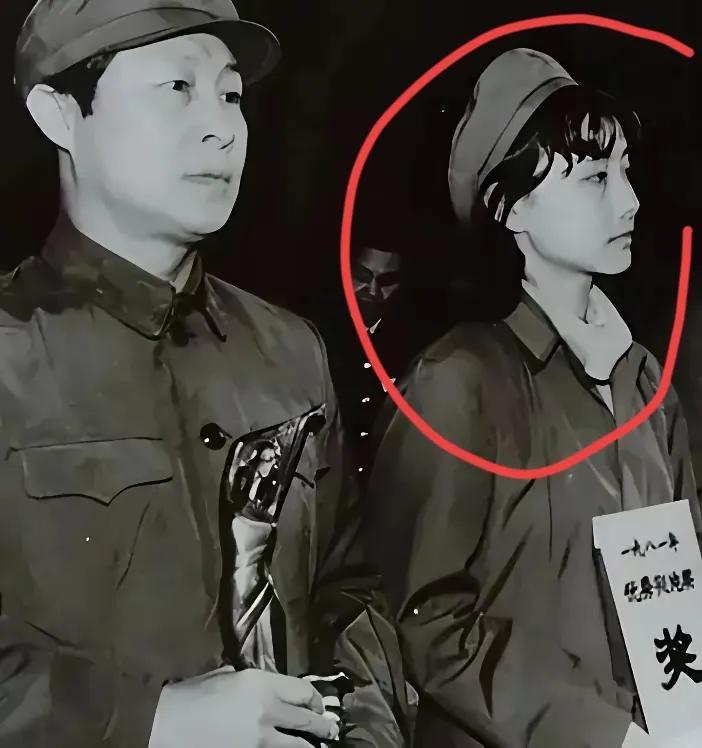1934年,14岁张爱玲听说父亲要再婚,竟在心里发誓:“如果那女人在眼前,我一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后来,张爱玲通过文学作品,让她成了“民国最恶毒的后母”。晚年,她却笑着说:“一切恶名我认,但无愧于心。” 张爱玲和孙用蕃的故事,起源于1934年。那年,张爱玲14岁,父亲张志沂决定续弦,娶了孙用蕃。这个消息对张爱玲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她从小跟母亲关系亲近,父母离异后,她跟父亲生活,但父女感情并不融洽。父亲再婚,等于在她心里又插了一刀。更何况,孙用蕃的到来还带来了金钱和地位的纠葛。张家曾是上海滩的显赫人家,但到张爱玲这一代,家道已经中落。孙用蕃出身也不低,她父亲是晚清重臣孙宝琦,她自己受过西式教育,会讲英文,气场不弱。这样的女人进了张家,难免让敏感的张爱玲觉得自己的地位被威胁。 张爱玲对孙用蕃的敌意不是空穴来风。她曾提到,父亲再婚后,家里的气氛变得更压抑。孙用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她有自己的性格和主张,跟张志沂的生活方式也很西化。这跟张爱玲的审美和价值观格格不入。她从小就对父亲的鸦片瘾和颓废作风不满,孙用蕃的加入在她眼里像是火上浇油。更别提,张爱玲觉得自己被父亲冷落,继母的存在放大了这种疏离感。那句“从阳台上推下去”的誓言,虽然只是少女一时的气话,却透露出她对这段关系的深深抗拒。 后来,张爱玲离开家,靠写作谋生。她把对继母的复杂情绪写进了作品里。比如《私语》里,她提到继母的生活细节,用冷冷的笔调勾勒出一个精明、强势的女人形象。她没直接点名孙用蕃,但谁读了都知道她在写谁。这种“春秋笔法”让孙用蕃在读者眼里成了典型的后母形象——冷漠、刻薄,甚至有点恶毒。尤其是张爱玲写到家里开销拮据时,继母还保持着讲究的派头,这在她笔下成了虚荣的证据。渐渐地,孙用蕃被贴上了“民国最恶毒后母”的标签,这名声一传十十传百,成了文学圈里的谈资。 但这故事没那么简单。孙用蕃真有那么不堪吗?她进张家时,张志沂已经是个瘾君子,家里经济也靠变卖老宅子撑着。孙用蕃嫁过来,不是来享福的,而是接了个烫手山芋。她得管家、应付张志沂的脾气,还要面对张爱玲这个满心敌意的继女。家里没多少钱,她还得维持体面,这在张爱玲眼里是虚伪,但在孙用蕃自己看来,可能只是撑场面的无奈。张爱玲写她强势,可从另一个角度看,孙用蕃也得硬着头皮撑起这个家。她不是没脾气的泥菩萨,偶尔跟张爱玲呛声,也算人之常情。 再说张爱玲这边。她对继母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年轻时,她满腔怨气,把孙用蕃写得一无是处。但人到中年,她开始反思。她在散文里提到过,自己小时候对很多事都带着偏见,长大后才明白,有些怨恨是自己放不下的心结。她没直接说后悔,但语气里多了点平和。比如,她写到父亲和继母的生活时,虽然还是冷嘲热讽,却也透出一种“他们过他们的,我过我的”的释然。这说明,她对孙用蕃的看法多少有了松动。 孙用蕃晚年的态度也挺耐人寻味。她活得比张爱玲长,到了老年,有人问她怎么看“恶毒后母”这顶帽子,她笑笑说:“一切恶名我认,但无愧于心。”这话听着挺硬气。她没为自己辩解太多,也没反过来指责张爱玲。她知道自己被写进了文学史,成了个反面角色,但她选择坦然接受。这态度让人有点意外。一个被骂了几十年的人,能这么淡定,要么是真问心无愧,要么是懒得计较。至少从她的话里,听不出多少怨气。 其实,张爱玲和孙用蕃的恩怨,说到底是家庭矛盾的缩影。张爱玲敏感、多疑,又有文学天赋,她把自己的情绪放大到了纸面上。孙用蕃呢,可能只是个普通女人,嫁了个不省心的男人,摊上了个难搞的继女。她俩的冲突,既有性格原因,也有时代背景。那时候,上海滩的旧式家庭和新式观念撞在一起,谁都过得别扭。张爱玲拿笔当武器,孙用蕃用沉默做盾牌,各有各的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