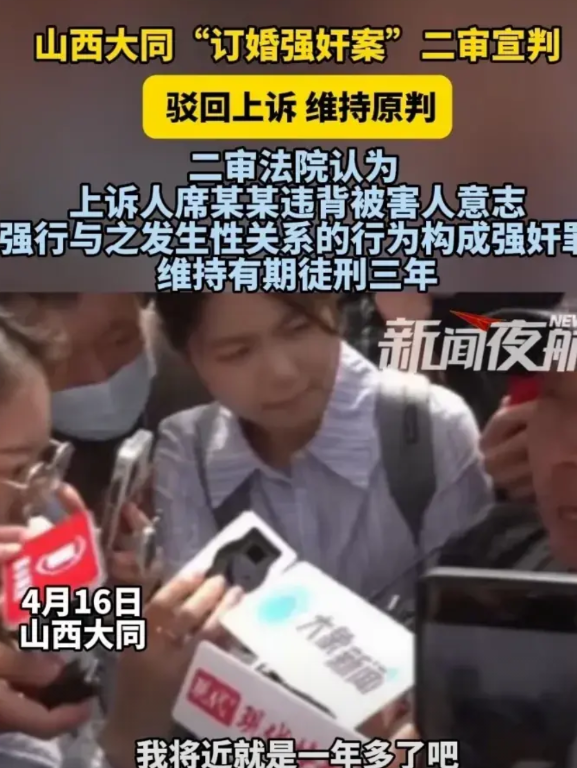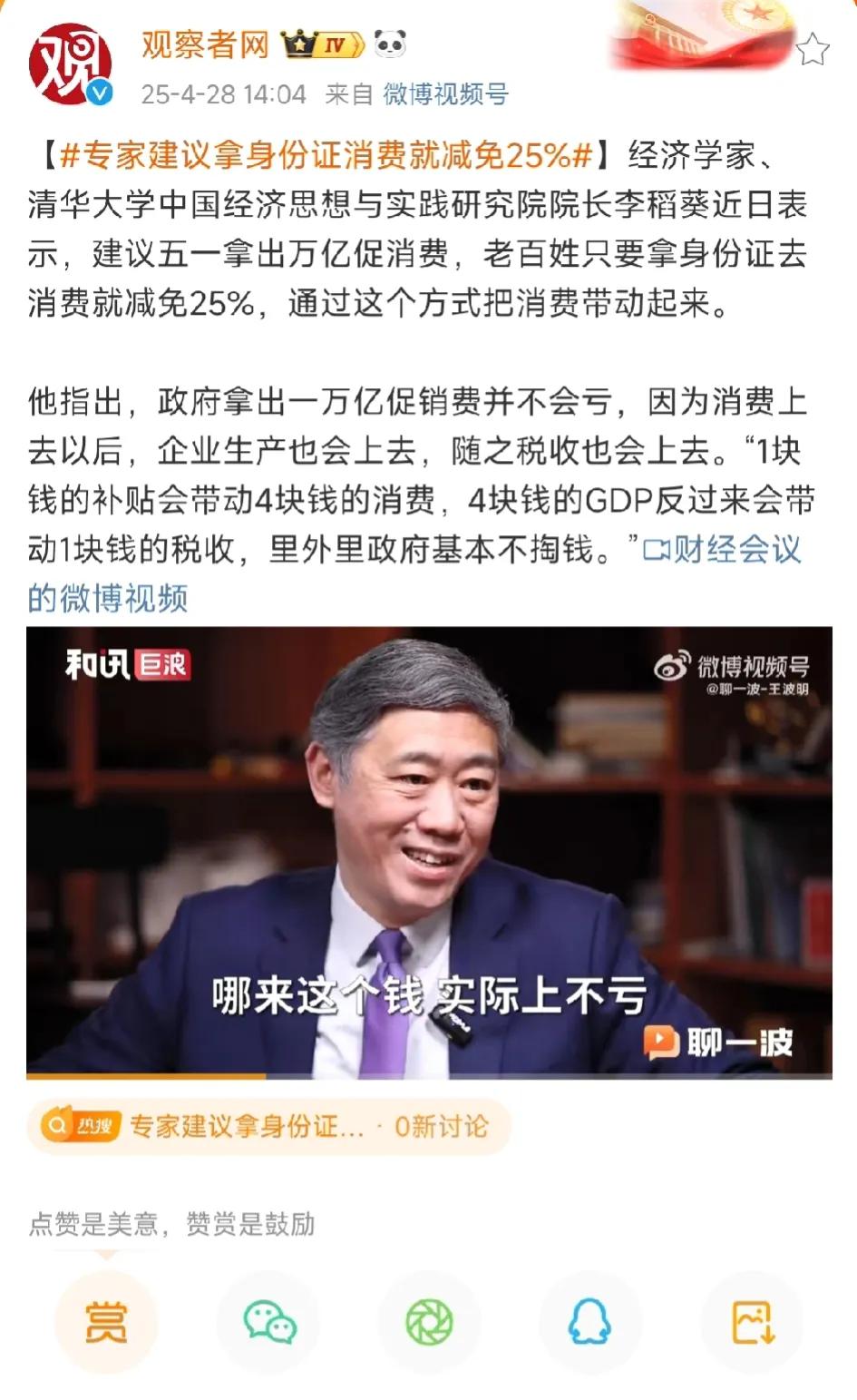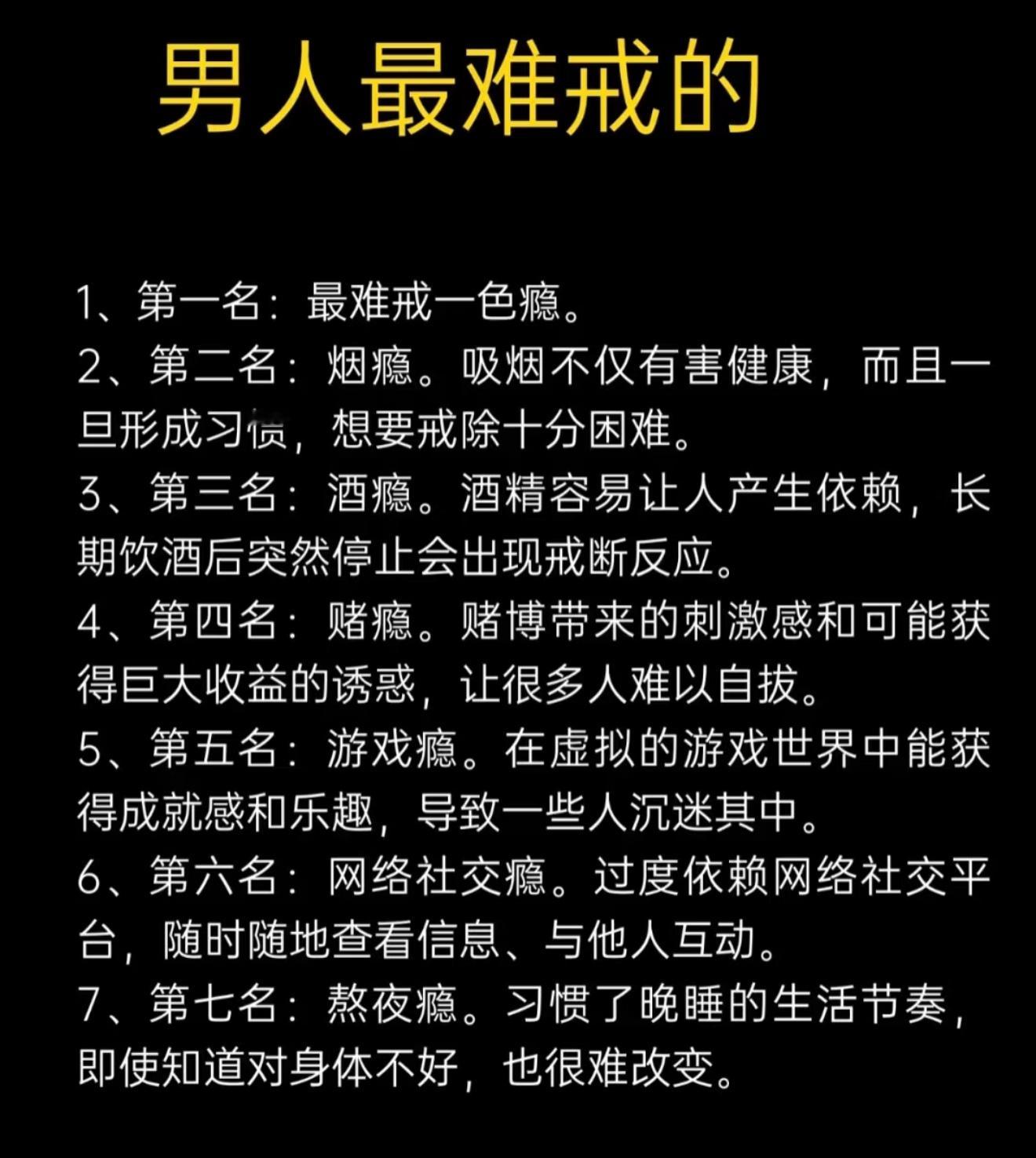1985年,在陕西西安火车站台上,一名即将奔赴老山前线的军人和未婚妻依依惜别。未婚妻抑制不住哭了,还说:你安心打仗吧,家中有我…… 这名军人就是杨越朝,毕业于西安陆军学院,这一次随部队开拔老山前线。 火车鸣笛声刺破了站台的嘈杂,杨越朝攥紧未婚妻刘小丽的手。她的眼泪砸在他手背上,烫得他心里发慌。军装口袋里还揣着昨晚写好的遗书,纸角被汗水浸得发皱。站台上其他新兵也在和家人告别,有个半大小子抱着母亲嚎啕大哭,哭声混着广播里的《血染的风采》,听得人眼眶发热。 杨越朝把刘小丽搂进怀里,闻到她头发上熟悉的桂花油香。这姑娘为了送他,特意换上过年才穿的红色呢子外套,现在袖口全被泪水打湿了。"别哭成花猫。"他故意逗她,手指抹过她眼下,却沾了满手湿凉。火车开始缓缓移动时,刘小丽突然追着车窗跑起来,红呢子外套在风里翻飞像面旗帜。她喊的那句"我等你回来"被汽笛声吞掉大半,但杨越朝看懂了她的口型。 前线比想象中更残酷。猫耳洞里永远有挥不散的霉味,压缩饼干嚼在嘴里像木屑。杨越朝每次写信都要先用膝盖压平皱巴巴的信纸,子弹箱当桌子,钢笔水总被雨水晕开。他不敢写阵地上的真实情况,只说些连队里养的土狗下了崽这样的琐事。有回炮弹炸塌了半个猫耳洞,他抖着满身泥土摸出刘小丽的照片,玻璃相框裂了道缝,正好横在她酒窝的位置。 刘小丽在纺织厂三班倒,下班就去照顾杨越朝瘫痪的父亲。有次老人半夜发病,她咬着牙用板车拖了两里地送到医院。护士看见这个满手老茧的姑娘瘫在走廊长椅上,军用水壶还挂在腰间晃荡。每个月领了工资,她先买两条大前门香烟托人往前线捎,杨越朝在信里提过,排长总抢他的烟抽。 1987年雨季,杨越朝在防御作战中被弹片击中后背。野战医院的帐篷里,他听见护士喊"23床需要输血",才发现喊的是自己。高烧中他梦见西安古城墙下,刘小丽踮脚给他系围巾,羊毛围巾刺得脖子发痒。醒来时看见连队文书攥着封信,信封上熟悉的字迹让他突然开始发抖——上次收到家信还是三个月前。 信里夹着张照片,刘小丽站在纺织厂光荣榜前,胸前大红花的绸带被风轻轻吹起。她在信上说父亲能拄拐走路了,又说巷口那家羊肉泡馍搬到了西大街。最后用铅笔淡淡补了句:"邻居张婶给我介绍对象,我说我家灶台上还温着饭呢。"杨越朝把这句话读了三遍,纱布下的伤口突突地跳。 停战消息传来那天,阵地上有人开了瓶珍藏的汾酒。杨越朝分到小半茶缸,辣得他直咳嗽。月光下他摸出所有家信按日期排好,发现刘小丽寄来的信纸越来越薄,有封甚至写在厂里的生产报表背面。他忽然想起离家前夜,这姑娘偷偷往他行李塞了双千层底布鞋,鞋垫里缝着她剪下的一缕头发。 凯旋的军列驶入西安站时,月台上锣鼓喧天。杨越朝在人群里找那件红呢子外套,直到看见个穿藏蓝工装的身影。刘小丽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举着"欢迎杨越朝回家"的纸牌站在横幅下。他挤过人群抱住她,发现她右手中指戴着顶针——那是给父亲做棉裤时留下的。 庆功宴上喝高了的战友起哄,问他们什么时候办喜事。刘小丽红着脸掏出手帕包,里面整整齐齐码着这些年杨越朝寄回的所有津贴。"都存着呢,"她眼睛亮得像蓄满水的井,"够买台蝴蝶牌缝纫机了。"窗外飘来槐花香,杨越朝想起阵地上那个被炸碎的相框,现在相片里的人正鲜活地坐在他身边。 这些年过去了,西安站台上的拥抱被拍成照片登在报纸上。有人说是爱情战胜了战争,可杨越朝总记得猫耳洞漏雨时,是想着刘小丽补袜子时的侧脸才熬过来的。那些藏在信纸里的牵挂,那些没说出口的承诺,或许比枪炮声更能穿透岁月的迷雾。 你们说,到底是什么让两个普通人能在烽火中守住这份等待?是那一封封被雨水打湿的家信,还是站台上那句没说完的"家中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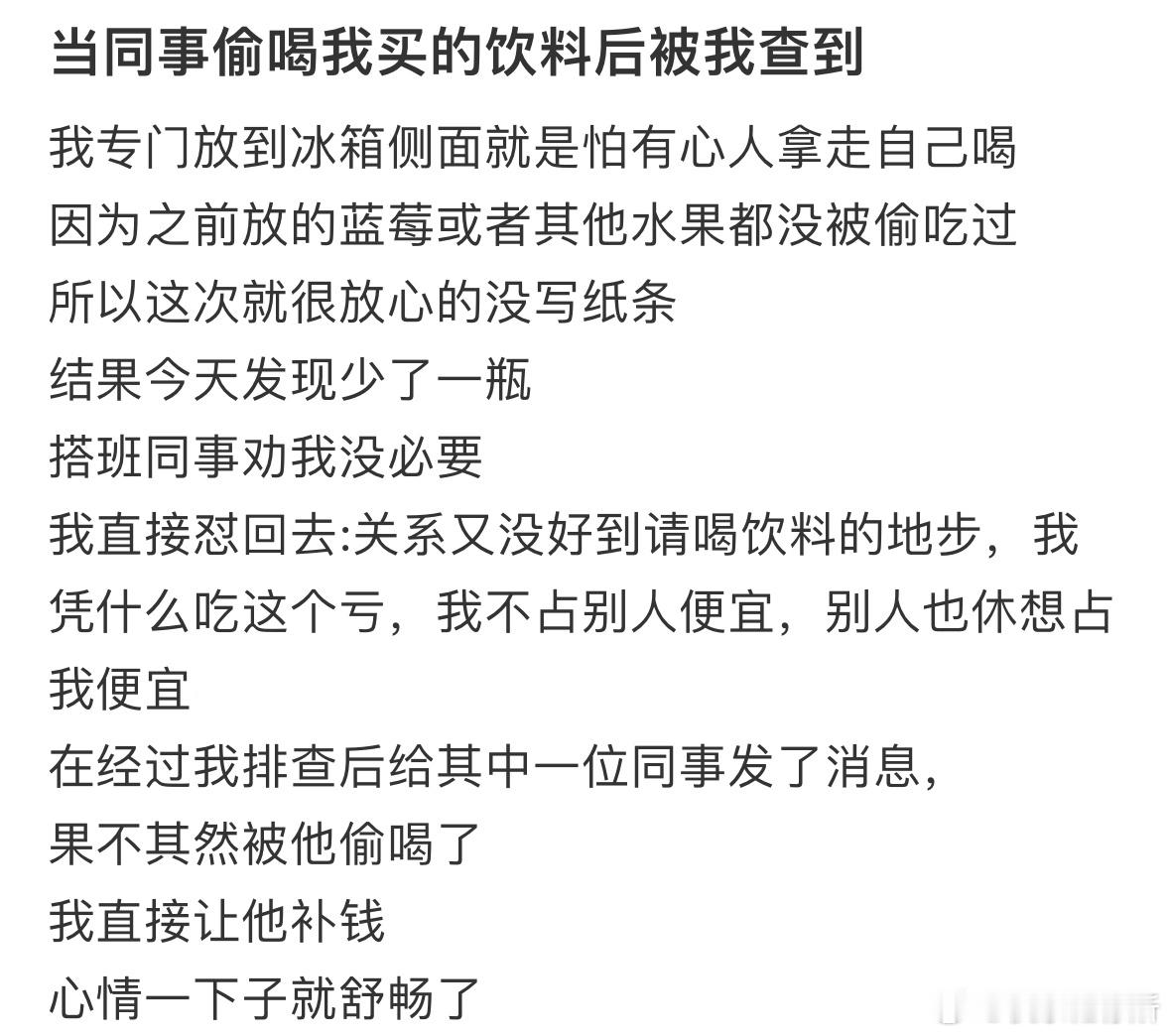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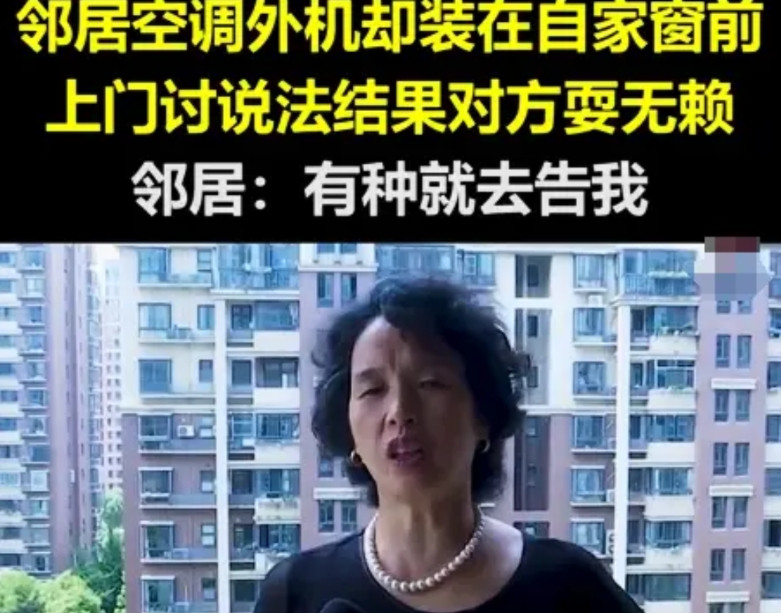
![戳到心窝子了?我安利马丽高叶和雷佳音红毯视频也要举报我[???][???]](http://image.uczzd.cn/16574057575948348902.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