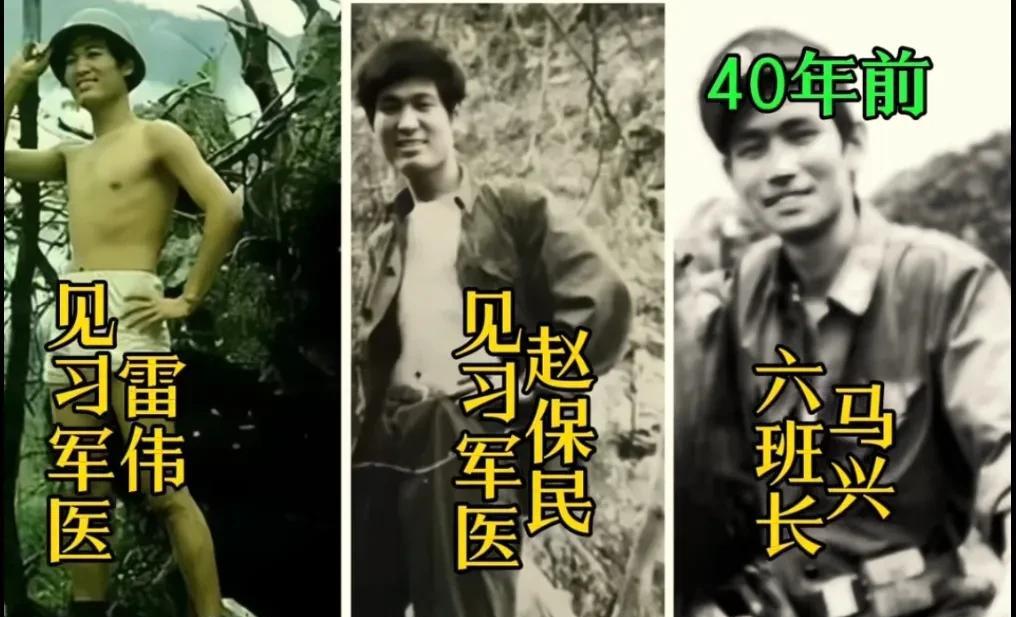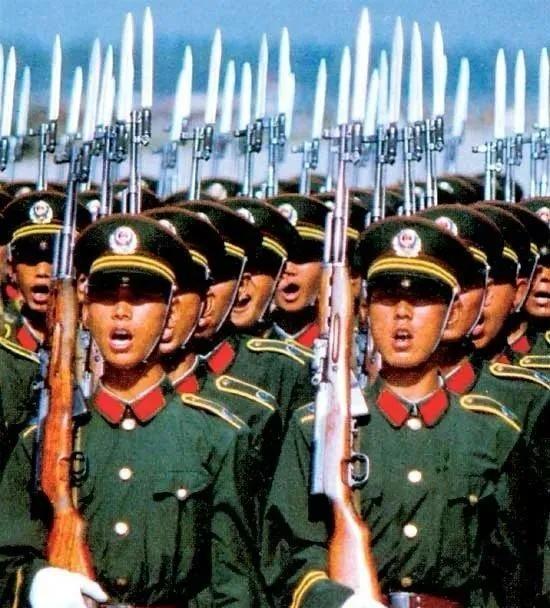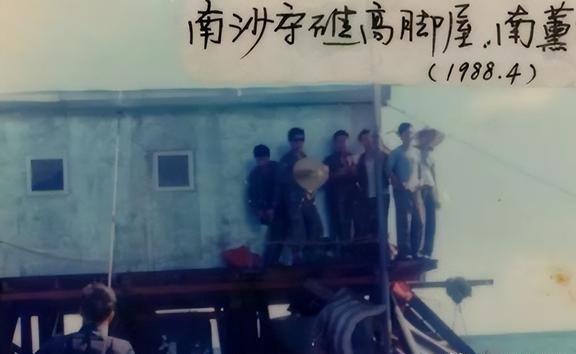1984年,硝烟弥漫的老山前线,战士黄登平正坚守在哨位上。就在他警觉扫视的瞬间,浓雾中若隐若现的人影引起了他的注意。待到破晓时分实地勘察后,这个看似寻常的观察竟让他荣立一等功——而他捕捉战机的敏锐与果决,令所有战友为之叹服。 【消息源自:《南疆卫士——老山战斗英雄谱》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雾锁老山》参战老兵回忆录2004年出版】 浓雾像一锅煮糊的米粥,黏稠得能掐出水来。黄登平把56式冲锋枪的背带在手腕上多绕了两圈——这是班长教的小窍门,防止武器在潮湿的雾气里打滑。1984年4月的老山前线,这样的夜晚他已经守了三十多天。 "小黄,换岗了。"身后传来窸窣声,是同班的李大个。黄登平摇摇头:"再守半小时,这雾不对劲。"他说不清为什么,只觉得雾气里飘着股铁锈味,就像小时候在公社杀年猪时闻到的血腥气。 凌晨三点十七分,一道比雾气更深的阴影从二百米外的山脊线掠过。黄登平立刻蹲下身,枪托抵住了肩窝。"班长!"他压低嗓子喊,"十一点方向,至少十五个黑影。"班长王铁柱猫着腰摸过来时,钢盔上凝着的水珠正顺着他的络腮胡往下滴。 "放两枪试试。"班长说话时,喉结上的伤疤跟着上下滚动——那是三年前被弹片刮的。砰!砰!枪声像石子扔进棉花堆,瞬间被浓雾吞没。战壕那头传来战友的嘀咕:"又是黄皮子(当地人对野猴的称呼)吧?" 黄登平却盯着左侧那条被当地人叫作"鬼见愁"的深沟。上周巡逻时他注意到,沟底的蕨类植物有被军靴踩踏的痕迹。"越南人肯定猫在那儿,"他指着地图上铅笔画的圆圈,"他们想等雾散。"班长突然笑了:"你小子眼睛比雷达还毒。" 天蒙蒙亮时,黄登平带着侦察组摸到了沟沿。越南话的交谈声混在晨雾里,像毒蛇吐信。有个越军士兵甚至就在他们头顶三米处的岩缝里解手,尿液溅在黄登平的伪装网上,带着浓重的鱼露味。 "撤!"黄登平比了个战术手势。他们故意踩断几根树枝,弄出仓皇撤退的动静。回到阵地后,他往脸上抹了把泥:"二排去东侧断崖,机枪组卡住葫芦口,等他们全冒头再打。"班长往他兜里塞了半包"大前门":"活着回来,给你申请探亲假。" 九点零五分,第一双军靴踏出了深沟。领头的越军特种兵端着美制M16,枪管上缠着防反光的布条。黄登平数到第十二个时,听见身后战友的呼吸突然加重——原来还有三个正用绳索从崖壁速降。 "打!"黄登平一枪掀翻了那个正在系绳结的越军。霎时间轻重机枪的咆哮震得雾霭翻腾,有个越军士兵的钢盔被击中时,发出像破锣般的闷响。二十分钟后,硝烟里躺着十五具尸体,最新款的苏制夜视仪还挂在其中一人的脖子上。 打扫战场时,黄登平在敌军指挥官身上搜出张地图。红铅笔圈着的正是他们营指挥所的位置,旁边用越南文标注着"04:00突袭"。班长用打火机烧地图时,火苗映得他眼白发黄:"好小子,你救了全营八百号人的命。" 三个月后,黄登平在表彰会上接过一等功勋章。礼堂里挂着"向英雄学习"的横幅,浆糊还没干透。记者追问他当时怕不怕,这个云南农家出身的战士搓着勋章上的绶带:"怕啥?我家田里的蚂蟥比他们难缠多了。"全场哄笑中,只有班长看见他偷偷把溅到领章上的血渍擦了又擦。 后来有军事专家分析,这支被全歼的越军305特工队,每个成员都在苏联接受过丛林战训练。他们携带的作战日记显示,原计划次日凌晨炸毁我军弹药库。而这一切,都被那个雾夜里不肯换岗的年轻士兵改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