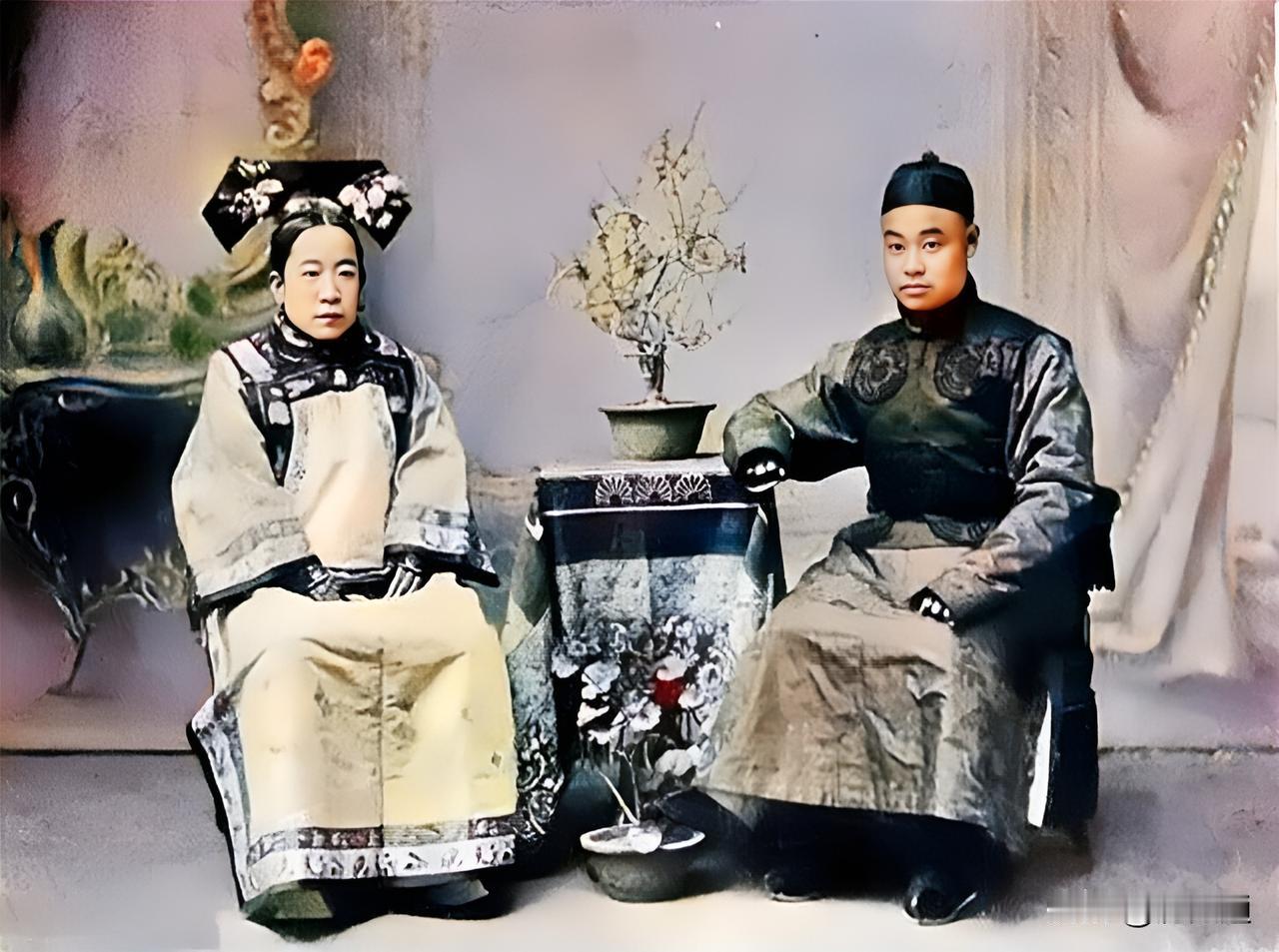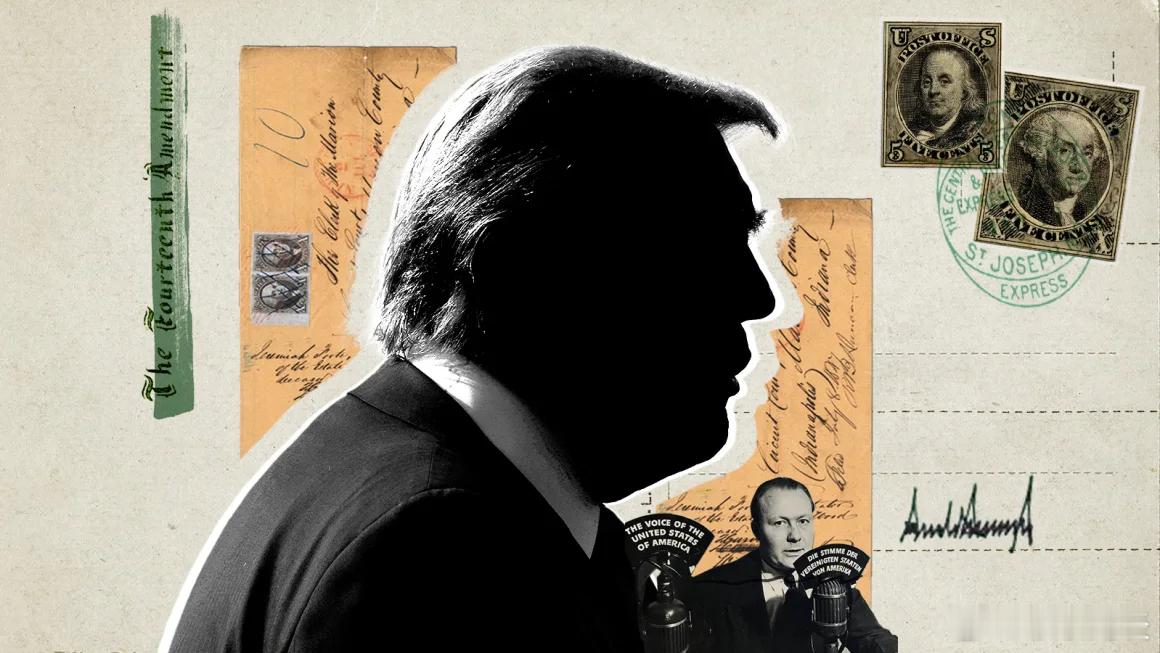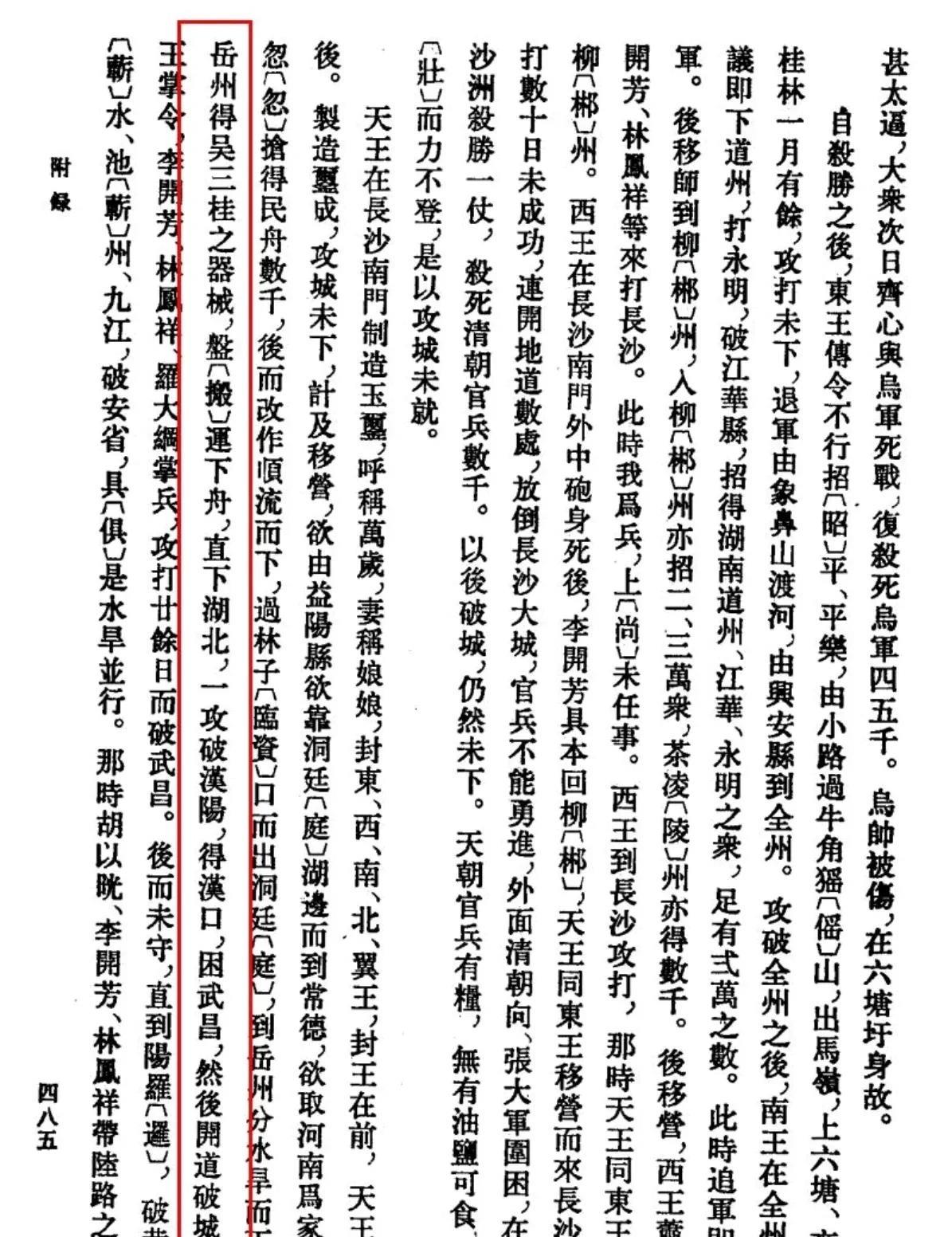1876年,64岁的左宗棠打到新疆敌占区时,忽然冒出一百来个衣着破烂的清朝官兵,异常激动地冲向他。左宗棠定睛一看,不禁痛哭流涕。 西北戈壁上,一支风尘仆仆的军队正往西前进,走在队伍最前头的是已经满头白发的左宗棠,他骑在马背上望着远处光秃秃的山丘,心里盘算着怎么收拾新疆的烂摊子。就在这时,前面探路的士兵突然跑回来报告,说前面巴里坤城门口有动静。 左宗棠拍马赶到时,只见城门口歪歪斜斜站着百十来号人,衣裳破得能看见皮肉,有的穿着露脚趾的皮靴,有的干脆光着脚,手里攥着锈迹斑斑的刀枪,旗杆上的黄龙旗被风沙撕成了布条,却还在风里飘。领头的老兵扑通跪下,沙哑着嗓子喊:“左大帅!是咱们大清的官军啊!”话音未落,身后的士兵们齐刷刷地磕头,膝盖砸在碎石子上啪啪响。 左宗棠赶紧翻身下马,扶起那老兵,借着夕阳一看,对方脸上的皱纹比自己还深,盔甲上的铜钉早没了,肩膀处补丁摞补丁,露出底下黝黑的皮肤。老兵的手像老树皮,攥着左宗棠的胳膊直发抖:“大帅,我们等了整整十三年啊!自打同治三年叛军打进乌鲁木齐,我们被切断退路,困在这巴里坤城里,跟外头断了音讯。”左宗棠这才发现,好些士兵的兵器根本不是制式装备,有的扛着木棍,有的攥着牧民的弯刀,甚至有个年轻士兵背着张用兽皮绷的弓——这哪是官军,分明是靠着一股子气硬撑下来的残兵。 “粮食呢?援兵呢?”左宗棠声音发颤。老兵抹了把脸:“头几年还有朝廷的粮饷,后来断了,我们就挖草根、煮皮带,把战马杀了分着吃,再后来……”他指了指城外的荒地,“开垦了几亩薄田,种点青稞,可叛军时不时来抢,能活下来的,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说话间,一个士兵抱着个陶罐过来,里头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青稞粥,飘着几片枯黄的野菜叶。左宗棠舀了一勺,发现底下沉着几粒发黑的豆子——这竟是他们过年才能吃到的“细粮”。 更让他揪心的是,队伍里有不少士兵缺胳膊少腿,有的用布条缠着溃烂的伤口,有的靠木棍撑着走路。一个断了左手的士兵凑过来,从怀里掏出半本破旧的《圣谕广训》,封皮早没了,纸页上全是补丁:“我们每天都朝着东边磕头,想着朝廷不会忘了咱们,想着总有一天官军会打回来。”左宗棠摸着那本被翻烂的书,突然想起自己抬棺出征时立下的誓言——抬棺不是怕死,是怕自己死了,这些困在边疆的弟兄们就真的没人管了。 当天夜里,左宗棠让随军的郎中给伤员治伤,把自己的粮食先匀给他们。火光中,老兵们说起这些年的坚守:他们曾打退过叛军五次攻城,用城墙砖、滚木当武器;曾在零下三十度的雪地里巡逻,脚冻掉了指甲也没敢合眼;甚至有兄弟临终前,还把最后一块青稞饼塞进战友嘴里。“我们把阵亡的弟兄埋在城西北的沙地里,每人坟前插根木牌,上面刻着‘大清官军’四个字。”老兵望着星空,声音轻得像风,“就盼着哪天有人能给他们收个尸,让魂归故里。” 第二天,左宗棠下令在巴里坤城举行祭典,带着全军给战死的弟兄们磕头。当他看见那些木牌上用刀刻的名字,有的歪歪扭扭,有的甚至只写了个“张”“李”,眼泪又止不住了。这些被朝廷遗忘的人,却用十三年的时光,把“大清”两个字刻进了戈壁滩的骨头里。后来收复新疆的战役中,这些老兵像开了刃的刀,冲锋时比年轻士兵还狠,他们说:“等了这么多年,就为了这一天,让叛军知道,大清的兵,没一个孬种!” 如今再看这段往事,左宗棠的痛哭里,有心疼有愧疚,更有感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边疆的将士们靠着信念硬生生撑起了国家的脊梁。他们或许不被史书大书特书,可每一道伤疤、每一块木牌,都在诉说着什么叫“虽远必守,虽苦必坚”。那些在戈壁滩上坚守的日日夜夜,让我们明白:一个国家的底气,从来不是靠朝堂上的空话,而是无数个无名官兵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