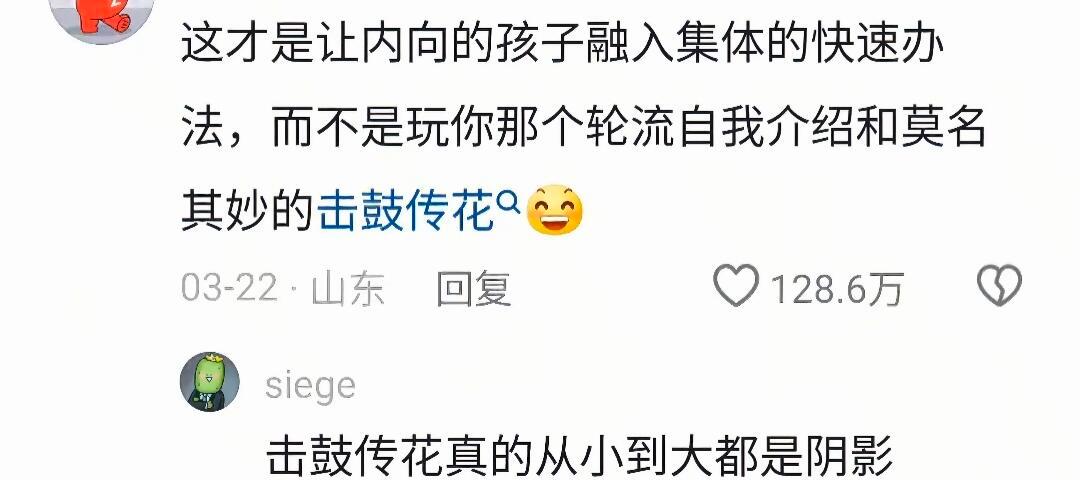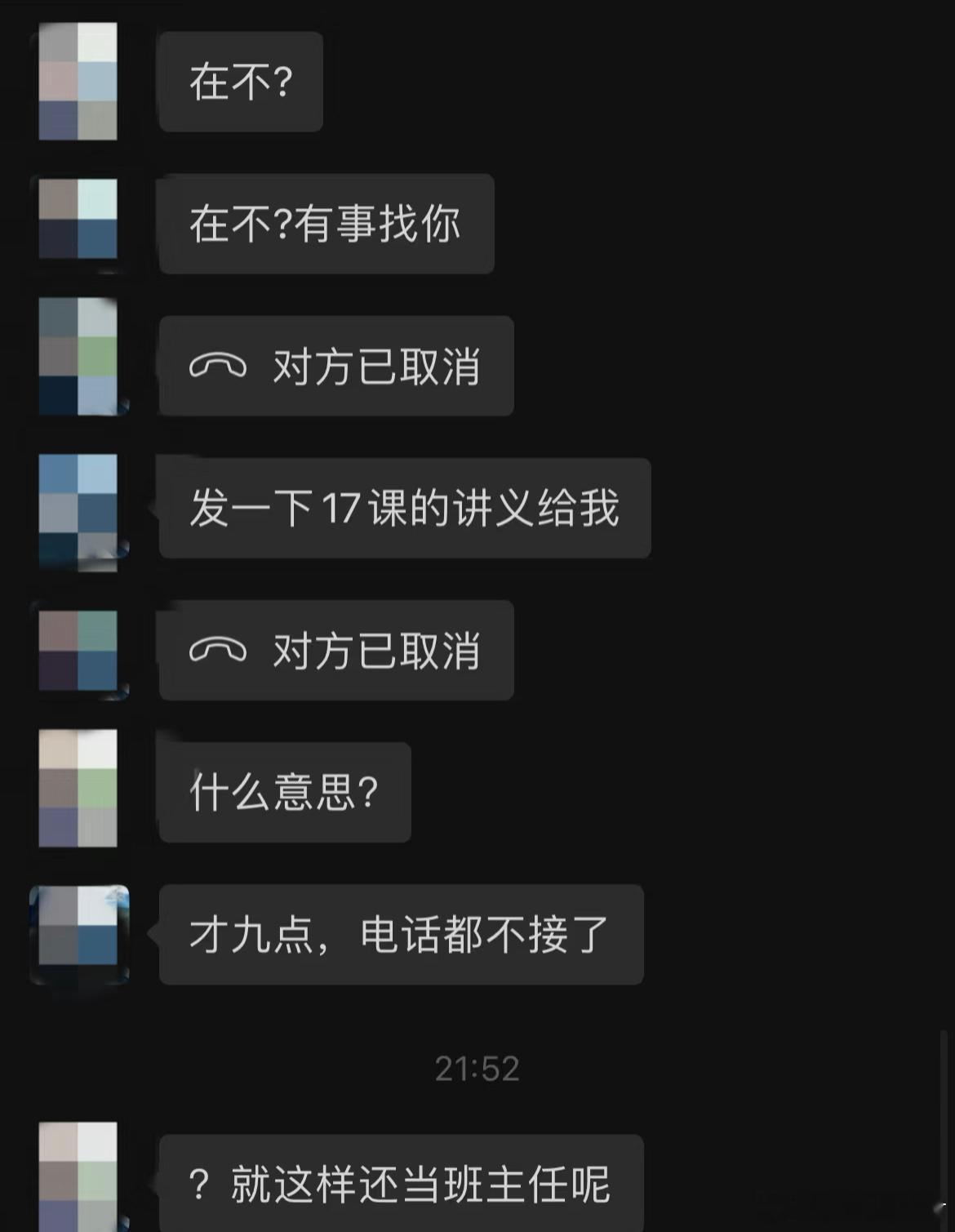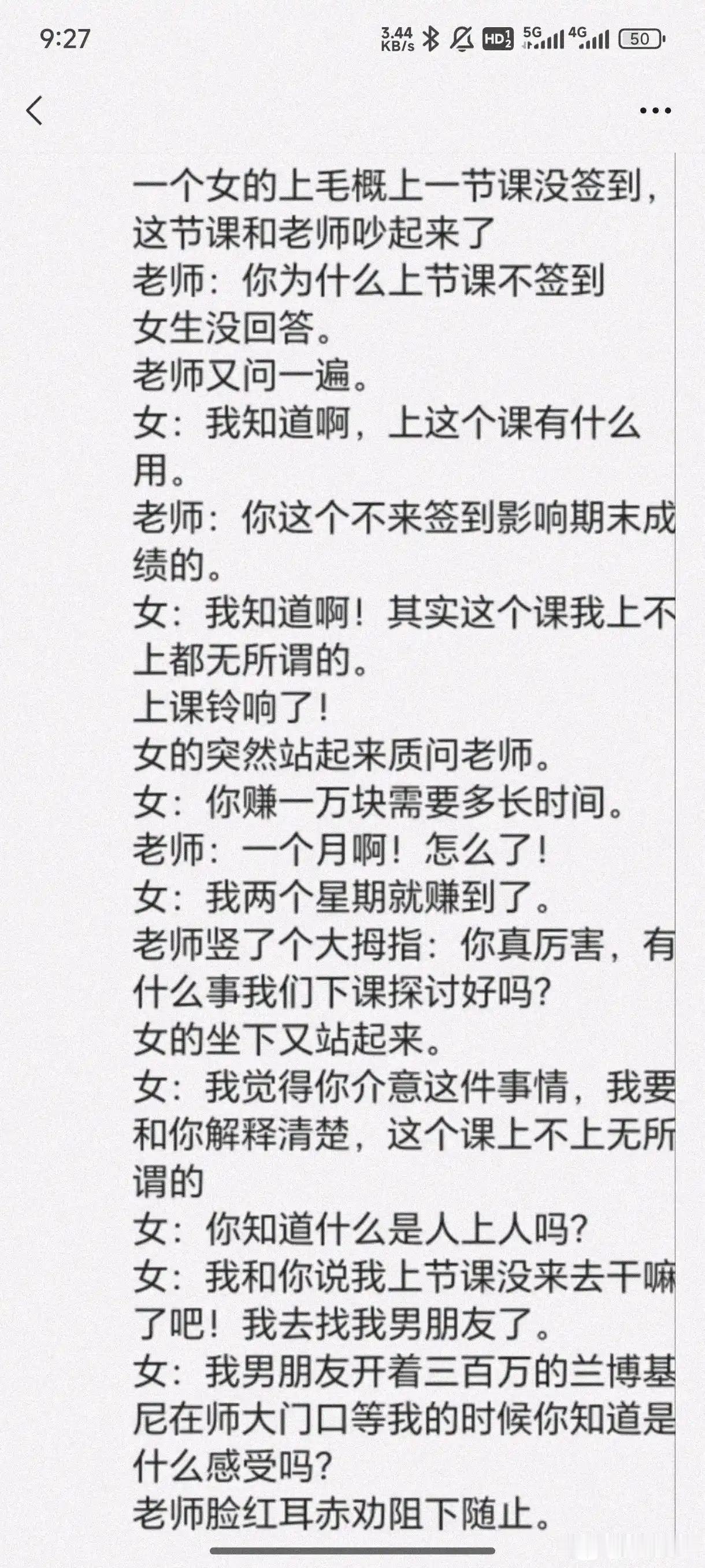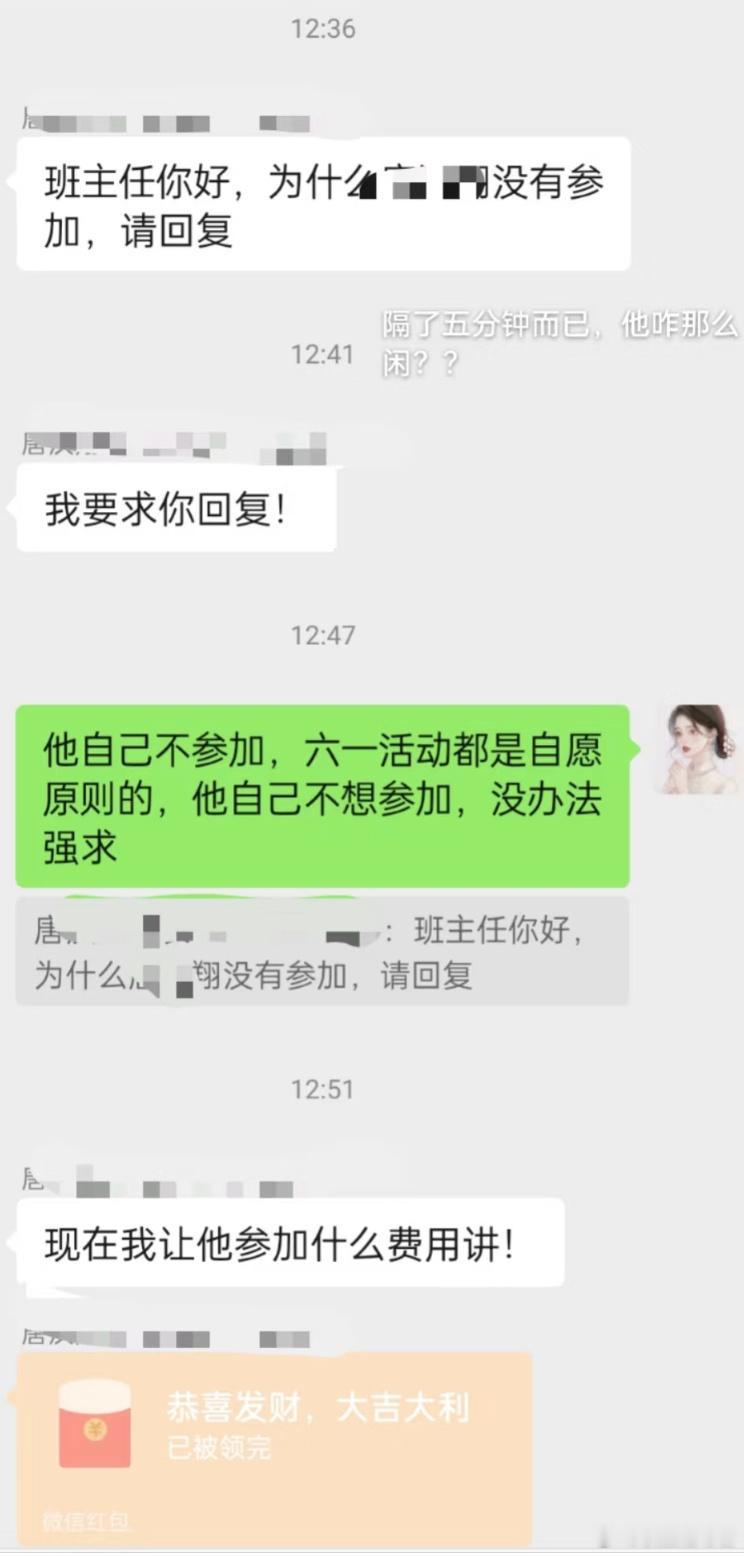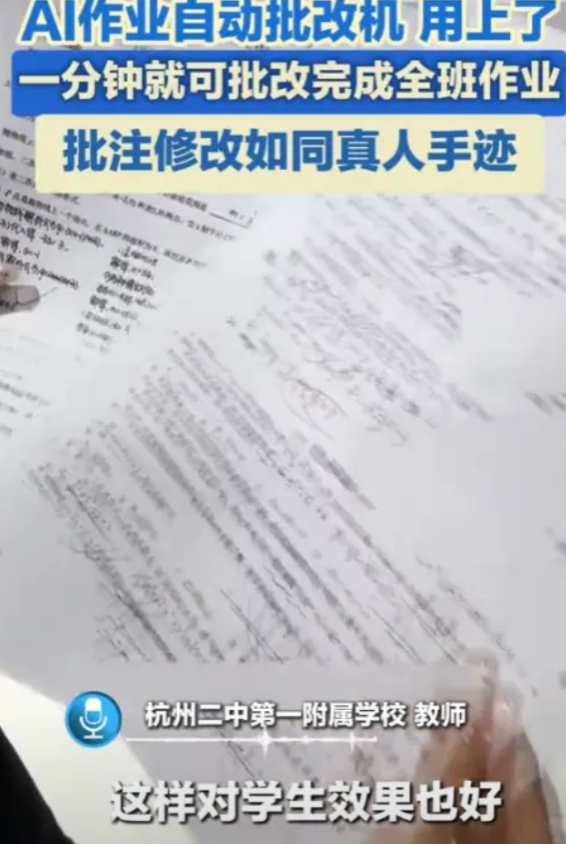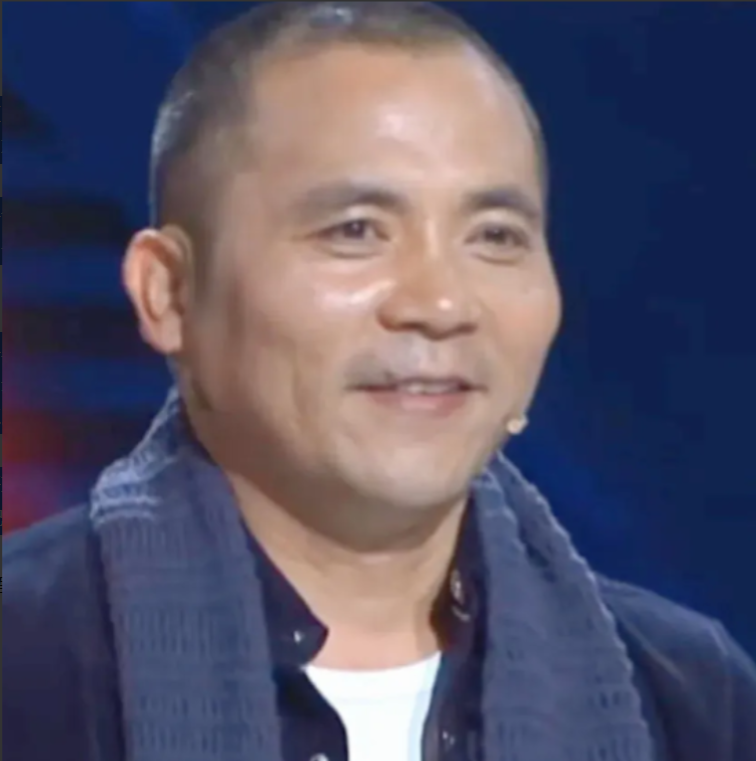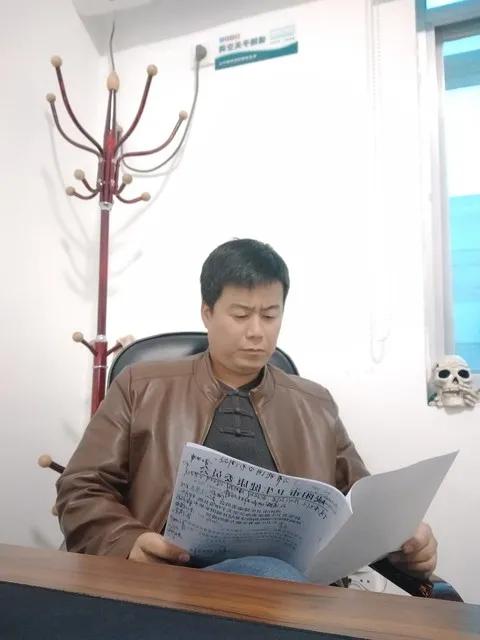2010年,长春一学校正上课间操,一女体育老师突然看到,好多孩子捂着鼻子,指着一个小女孩喊:“臭、臭!”女老师找到女孩班主任询问:“这女孩怎么脏兮兮的?”她这才得知,小女孩母亲生下她就跟别人跑了,她跟着智力有问题的爸爸生活,女老师:“走,跟我回家!”谁曾想,就是这个决定,改变了女孩的一生!
2010年深秋,长春宽城区实验小学的课间操铃声响起,体育老师张引吹着哨子整队时,突然听见三年级队列里传来嗤笑:"臭死了!离她远点!"
顺着孩子们的目光望去,扎着乱蓬蓬马尾的小女孩正往队列里缩,露在凉鞋外的脚趾冻得通红,校服袖口磨得发亮,隐隐透出酸腐的汗味。
张引跟着班主任走进德育处,看见办公桌上摊着楠宝的档案:母亲在她出生后改嫁,父亲因脑膜炎后遗症丧失劳动能力,监护权暂时落在智障的姑妈手中。
"上周美术课,她把蜡笔藏进袖口,"班主任揉着眉心,"因为这是她唯一的文具。"
窗外的梧桐叶打着旋儿落下,张引想起刚才看见楠宝用指甲在地上画的小人——那是她见过最生动的儿童画,却沾满了灰尘。
第一次带楠宝回家洗澡,张引准备的草莓味沐浴露在澡盆里堆起泡沫。
当搓澡巾触到孩子后背时,灰黑色的泥垢混着跳蚤卵簌簌掉落,露出下面密密麻麻的红疙瘩。
楠宝像只受惊的小兽蜷缩着,直到热水冲过发梢时,才用蚊子般的声音说:"阿姨,这是我第一次用香皂。"
张引的手指在水流中停顿三秒,突然想起自己女儿床头的HelloKitty浴巾——同样6岁,命运却如此不同。
晚饭时,楠宝捧着青花瓷碗的手在发抖。张引夹起的糖醋排骨刚落盘,碗里的米饭已下去半寸。
"慢点吃,都是你的。"看着孩子狼吞虎咽的样子,张引悄悄把自己碗里的肉拨过去。
女儿朵朵趴在厨房门边,突然跑回房间,再出来时抱着崭新的卡通水杯:"给妹妹用这个。"
那一刻,窗外的暮色与屋内的灯光,在两个孩子的眼中映出温暖的光晕。
2015年冬夜,张引在台灯下计算补课费:楠宝的素描班800元,朵朵的钢琴课600元,加上两个孩子的校服费,工资条上的数字像融化的冰棍般消失。
母亲寄来的信封躺在桌上,里面是省吃俭用的2000元,附言写着:"你爸说楠宝画的牡丹,比他养的花还好看。"
卧室里传来楠宝的翻书声,这个总把"谢谢老师"挂在嘴边的女孩,早已在户口本上变成"张楠"。
2020年教师节,天津卫视的演播厅里,20岁的张楠握着话筒哽咽:"妈妈第一次给我买羽绒服时,我才知道衣服可以这么软和。"
镜头扫过观众席,张引鬓角的白发在聚光灯下闪烁,身旁的朵朵正把剥好的橘子递过来——这对相差五岁的"姐妹",早已分不清血缘与亲情的界限。
当"我爱你"三个字从楠宝口中溢出,张引终于读懂十年前那个深秋的决定:有些遇见,就是为了让生命重新发芽。
当制度化救助尚未覆盖每个角落,普通人的善意就是最温暖的补丁。
2008年河南李芳老师,收养父母双亡的学生,退休后用养老金创办留守儿童之家,照顾过37个孩子;2016年云南刘秀祥,背着患病母亲上学,毕业后返乡任教,帮助1200名贫困学生重返校园。
我国单亲家庭儿童超2000万,其中15%面临教育断层风险,而像张引这样的"编外家长",正用民间力量编织着社会支持网络。
宽城区实验小学的荣誉墙上,张引的照片旁贴着楠宝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每当新生入学,班主任总会说起那个"臭烘烘的小女孩"如何变成素描特长生,如何在作文里写"妈妈的哨声是世界上最温暖的铃声"。
这场始于课间操的生命交集,最终在时光中酿成最动人的教育诗篇。
张引用十年光阴证明,教育从来不限于课堂,真正的育人者,会在看见尘埃里的种子时,愿意蹲下身子浇水施肥。
当她为楠宝搓去污垢时,洗掉的不仅是身体的尘埃,更是命运的阴霾;当她把糖醋排骨拨进孩子碗里时,传递的不仅是食物的温度,更是人性的光芒。
正如教育学者顾明远所言:"好的教育,是用一个生命去温暖另一个生命。"
张引与楠宝的故事,是对这句话最朴素的诠释——在世俗的眼光里,她们是老师与学生、养母与养女,而在生命的本质里,她们是彼此的星光,一个在尘埃里托起希望,一个在温暖中破茧重生。
当课间操的哨声再次响起,操场上的每个孩子都该知道,这个世界总会有人,为了你的笑容,愿意停下脚步,张开怀抱,成为你生命里的第二个春天。
对此,您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文章为真实事件整理评述,无不良引导,文中均使用化名)
创作来源:天津卫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