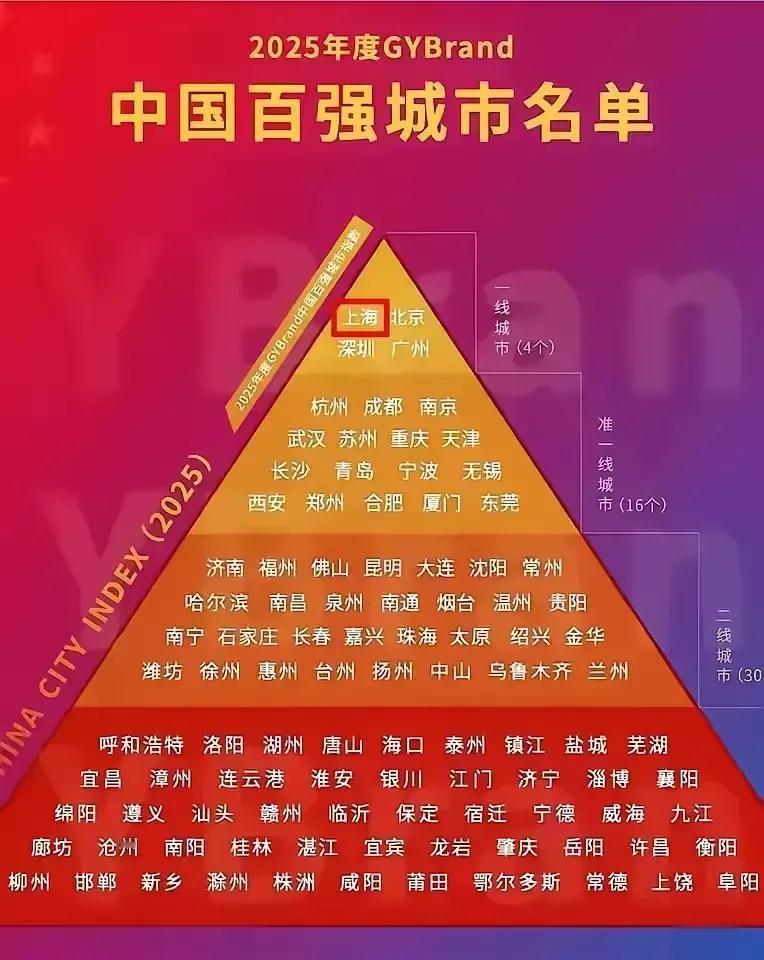1991年沈阳郊区的刑场上,19岁的吴晓莉跪在黄土地上。 这个本该绽放青春年华的姑娘,此刻双手反绑着等待枪决。 她突然仰起脖子朝天空嘶喊:"查查我的身份!我是清白的!" 这声哭喊穿透了围观人群的窃窃私语,也惊动了在场的执法人员。 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板上钉钉的杀人案背后,藏着个让人揪心的故事。 事情得从十九年前说起。 1972年开春,沈阳郊区老吴家添了个闺女。 村里人听说生的是女娃,都摇着头叹气。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盼男丁,老吴两口子看着襁褓里的女婴,脸上也挂不住笑模样。 这丫头打小就机灵,五岁会帮家里烧火,七岁能跟着下地拔草。 可爹娘总觉得闺女是赔钱货,平日里连口热乎饭都舍不得给她留。 等到吴晓莉上学那年,村里小学来了个年轻女老师。 这老师瞧着晓莉水灵灵的大眼睛,摸着她的羊角辫说:"这丫头长得真俊,好好念书准能有出息。" 可这话传到老吴耳朵里就变了味。 庄稼人眼里,姑娘家长得好看就是祸根。 果然,打从初中开始,班上那些半大小子成天围着晓莉转悠,不是扯她辫子就是往她书包里塞蛤蟆。 晓莉回家抹着眼泪跟娘诉苦,换来的却是劈头盖脸一顿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要不招摇人家能欺负你?" 自打那天起,这丫头就再没跟家里说过心里话。 她憋着股劲儿用功读书,本想着考上中专就能飞出这穷山沟,哪知道刚上初二,她爹就把书包往灶膛里一扔:"女娃读书顶个屁用!明儿跟你三叔进城学裁缝去。" 十五岁生日那天,晓莉揣着包袱皮跟着三叔进了城裁缝铺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老婆带着孩子在乡下住。 头两个月还算太平,晓莉白天学踩缝纫机,晚上把铺子里的条凳拼起来当床睡。 直到有天老板娘带着孩子回娘家,老板半夜摸黑进了铺子。 那天晚上要不是老板娘提前回来,晓莉怕是连命都要折在裁缝铺里。 打那以后,老板变本加厉地动手动脚。 晓莉躲着藏着,有天实在受不了顶了句嘴,谁知老板倒打一耙,冲着自己婆娘嚷嚷:"这小姑娘成天勾搭人!" 老板娘抄起熨斗就往晓莉身上砸,当街扒了她的外褂,连人带包袱扔出了门。 街坊四邻围着指指点点,吐沫星子能把人淹死。 晓莉缩在墙根底下哭到半夜,摸着兜里仅有的五毛钱,心里那团火越烧越旺。 她想起裁缝铺老板八岁的儿子天天在胡同口踢毽子,想起老板娘骂她"勾人精"时狰狞的脸,牙关咬得咯咯响。 那天晌午头,晓莉蹲在裁缝铺对面的杂货店门口。 看着老板儿子蹦蹦跳跳往家走,她摸出兜里攒了半个月的糖块:"小弟弟,姐姐带你去个好地方。" 孩子哪知道人心险恶,乐呵呵跟着进了城西的乱葬岗。 等四下没人的时候,晓莉掏出藏在怀里的老虎钳,照着孩子后脑勺就是几下...... 警车鸣着笛满城搜捕的时候,晓莉正躲在桥洞底下啃冷馒头。 她摸着口袋里染血的糖纸,又哭又笑地念叨:"让你们糟践人,让你们糟践人......" 不出三天,公安就在货运站逮住了要扒火车逃跑的姑娘。 公审大会上,法官念判决书的声音嗡嗡作响,晓莉只听见"死刑"俩字在耳朵里来回撞。 临刑前那个晚上,看守所的老管教给她送了碗猪肉炖粉条。 晓莉捧着碗突然说了句:"叔,我真没勾搭过人。" 老管教叹着气收拾碗筷时,听见身后传来压抑的呜咽:"我要是男娃该多好......" 刑场上那声喊冤惊动了市局的领导。 后来据办案民警回忆,他们重新走访了裁缝铺周围的街坊,有个卖冰棍的老太太哆哆嗦嗦地说:"那闺女被赶出来那天,裤腿上还有血印子呢......" 可惜等这些证言凑齐的时候,吴晓莉的坟头草都长老高了。 这事在沈阳城里传了小半年,茶余饭后总有人唏嘘。 纺织厂的女工们说,那裁缝铺老板后来搬了家,听说他婆娘疯了,见着穿花褂子的姑娘就吐唾沫。 倒是晓莉老家的人始终不信闺女会杀人,逢年过节往她坟上摆两个煮鸡蛋,念叨着:"下辈子托生个小子吧......" 二十多年过去,城里盖起了新法院大楼。 有回几个实习的法官助理翻旧档案,看见泛黄的案卷里夹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的姑娘梳着两条麻花辫,眼睛亮得像星星。 带教的老法官敲着桌子说:"这案子要搁现在,指不定能办成防卫过当......" 话没说完,档案室窗外突然刮过一阵穿堂风,吹得案卷哗啦啦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