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武汉一女教师,新婚后不久怀孕,不料,孩子刚出生,丈夫竟然脸色大变说“我们分手吧”,随后扭头就走,再也没有回来! 1988年,一位年轻女教师正经历着人生最艰难的抉择,邹翃燕浑身被汗水浸透,耳边传来医生严肃的谈话声——她刚出生的孩子因产程过长导致颅内出血,极有可能发展成脑瘫。 当丈夫说出“放弃抢救”四个字转身离去时,这个虚弱的母亲用尽力气抓住床单,指甲在消毒水味弥漫的空气中掐出深深的白印。 这个被父亲抛弃的男婴在保温箱里躺了五天五夜才发出第一声啼哭,邹翃燕抱着轻得像片羽毛的儿子,在病历本上工整写下“丁丁”两个字。 最初的3个月看似风平浪静。邹翃燕把家里挂满彩色气球,三个月大的丁丁虽然还不会翻身,但眼珠能随着红气球转动。 这种微小的进步让年轻母亲欣喜若狂,直到孩子六个月时显露出异常——手脚绵软得抓不住拨浪鼓,连最轻的塑料玩具都拿不稳。同济医院的诊断书像块寒冰:运动神经受损,未来可能无法正常行走。 从那天起,武汉三镇的街头多了个背着孩子的单亲妈妈,邹翃燕白天在中学教语文,下班后要赶三份兼职,晚上背着丁丁挤公交去做康复治疗。 九十年代的康复机构条件简陋,医生教她用热毛巾给孩子敷关节,用木棍绑着矫正腿型。有次在电车上,丁丁被矫正支架硌得直哭,旁边老太太看不下去要帮忙抱孩子,邹翃燕谢绝时才发现自己肩膀早被泪水打湿。 3岁生日那天,丁丁突然扶着墙颤巍巍站起来,邹翃燕举着相机的手抖得按不下快门,看着儿子像喝醉似的摇摇晃晃迈出第一步,她蹲在地上哭得比孩子出生时还厉害。 这来之不易的进步背后,是日复一日跪在地上帮孩子压腿的酸楚,是寒冬腊月里搓热双手给孩子按摩的坚持。 上学成了新难题,普通小学不愿接收行动不便的孩子,邹翃燕跑了七所学校才找到愿意尝试的校长。课间操时间成了丁丁最难熬的时刻,有调皮同学学他走路的姿势,班主任委婉建议让孩子转去特殊学校。 那天晚上,邹翃燕把《海伦凯勒传》放在儿子床头,轻声说:“咱们用成绩让他们闭嘴。” 这句话像粒种子在丁丁心里生根发芽,别人课间玩耍时他预习课文,体育课自由活动时他趴在单杠上练臂力。 五年级期末考试,他举着全年级第一的成绩单回家,路上摔了三个跟头都没松手。邹翃燕看着蹭破皮的膝盖和完好无损的奖状,既心疼又骄傲。 2007年,武昌实验中学光荣榜贴出喜报:丁丁以660分考上北大,穿着褪色校服的少年站在红榜前,阳光把他矫正鞋的金属支架照得发亮。 没人知道这个看似普通的考生,每天要比别人早起两小时做肢体训练,更没人注意到人群中那位鬓角泛白的母亲,她攥着录取通知书的手上还贴着膏药——那是常年给孩子按摩落下的腱鞘炎。 4年后飞往波士顿的航班上,丁丁行李箱里装着母亲手写的菜谱,在哈佛法学院图书馆通宵备考时,他总想起小时候练走路的场景:母亲在前方张开双臂,眼睛却紧张地盯着他脚下。 如今他穿着定制皮鞋站在模拟法庭上,依然能感觉到背后那道温暖的目光。 现在的丁丁是北京某律所金牌顾问,办公室抽屉里珍藏着三十年前的老照片:年轻的邹翃燕抱着襁褓中的婴儿,背后挂满彩色气球。每当有人问起他的成长经历,他都会指着照片说:“看,这就是我的超级英雄。” 而远在武汉的邹老师依然保持着20年前的作息,清晨总要在江滩快步走五公里——她说这是当年背孩子锻炼出来的脚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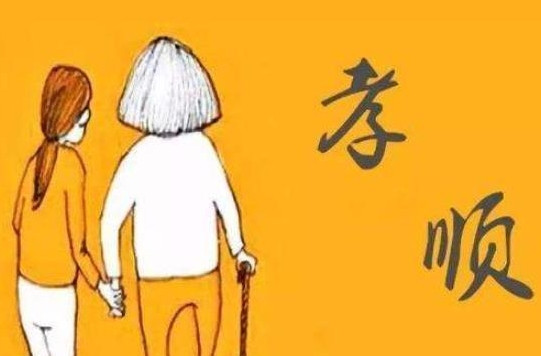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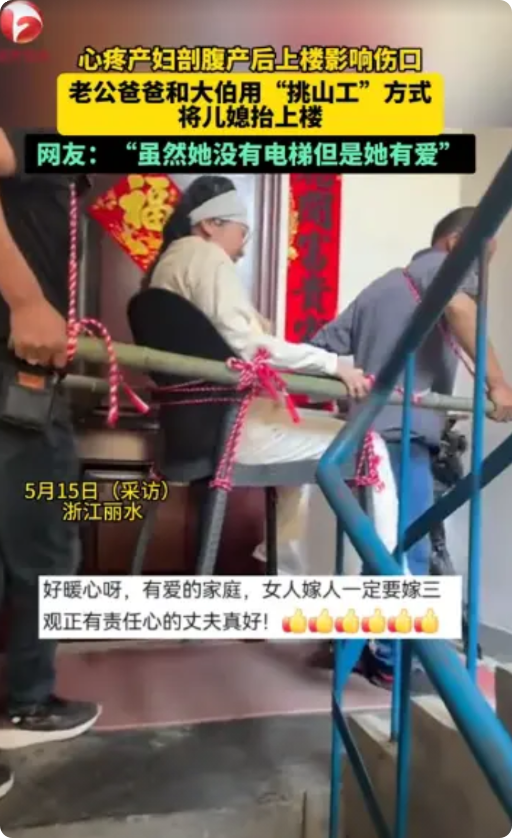

猎狼之旅
伟大的母亲!女生本弱,为母则刚!
友友
[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