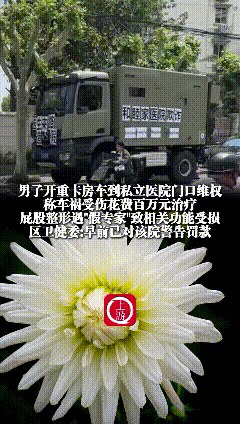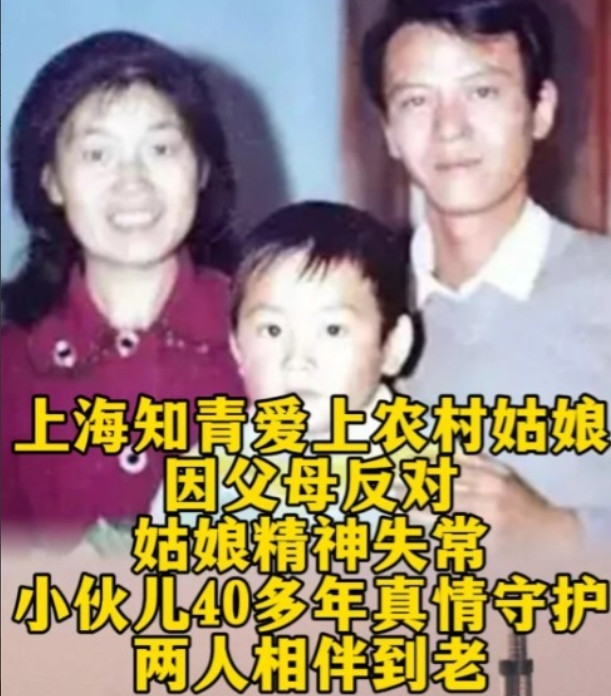1970年,黑龙江鲁民屯飘着鹅毛大雪,上海女知青张菊芬蜷缩在老乡家的土炕上。这个原本家境优渥的姑娘此刻正攥着被角,额头上沁出的冷汗把枕头洇湿了一大片。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四十二年前那个飘雪的腊月初八,黑龙江某个偏僻村庄的土坯房里传出婴儿啼哭。 刚满三岁的张淑凤趴在门缝上,看见养母和一个陌生女人在院子里拉扯。 那个穿着蓝布棉袄的女人频频回头张望,眼睛里蓄着化不开的愁绪,这个画面像枚生锈的图钉,牢牢扎进小女孩的记忆深处。 七岁那年夏天,张淑凤蹲在井台边玩泥巴,村头王奶奶摸着她的羊角辫感叹:"这丫头越长越像上海来的知青了。" 正在打水的养母突然摔了水桶,拽着她就往家走。 那天夜里,张淑凤躲在被窝里数着窗棂外的星星,第一次模模糊糊意识到自己身世的秘密。 十二岁生日那天,堂叔家收留的孕妇在粮仓里生下女婴。 张淑凤帮着烧热水时,听见产妇压抑的哭声像受伤的母兽。 七天后女人留下襁褓中的孩子独自返城,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足足哭了半小时。 这个场景让张淑凤突然想起三岁时的蓝布棉袄女人,她开始在每个腊月初八跑到村口张望,直到十七岁那年被宣大叔拦在放学路上。 "你亲妈从上海来了,在招待所等你。" 宣大叔搓着冻红的手说。 张淑凤看着远处冒炊烟的农家小院,养母正在灶台前忙活晚饭。 她咬着后槽牙说了句"让她滚",扭头跑回家摔上门。 那天夜里她蒙着被子哭湿枕头,却不知道招待所二楼某个房间的灯亮到天明。 结婚前夜,王中美阿姨带来个牛皮纸信封。 泛黄的信纸上爬满褪色的蓝墨水字迹,记录着1969年冬天上海女知青张菊芬的遭遇。 怀孕七个月被房东赶出,临盆夜在牲口棚里挣扎生产,跪着央求村支书给孩子找户好人家。 信末附着张菊芬这些年寄来的汇款单存根,金额从五块、十块慢慢变成五十、一百,最近一张的日期停在1987年。 2004年春天,张淑凤攥着写有"张菊芬"三个字的纸条走进上海闸北区派出所。 户籍民警在电脑前敲打键盘的嗒嗒声,像极了当年粮仓里老鼠啃木头的动静。 屏幕上一百个"张菊芬"的名字晃得她头晕,养母临终前说的"上海和田中学"成了最后的线索。 十年后的某个周末,电视机里正在播放寻亲节目。 丈夫看见妻子盯着屏幕里相拥而泣的母女,悄悄记下了节目组的联系方式。 当编导带着摄像机走进家门时,张淑凤正对着梳妆镜练习微笑。 她怕生母看见自己眉心的川字纹会难过。 节目组翻遍了和田中学发霉的档案柜,终于在某个落灰的牛皮档案袋里找到线索。 退休教师蔡则良说起1969年的知青名单时,浑浊的眼睛突然发亮:"张菊芬啊,干活最卖力的上海姑娘,后来肚子藏不住了......" 演播厅的空调呼呼吹着冷风,张淑凤的手心却沁出汗来。 当那位自称张菊芬弟弟的老人走进演播室时,挂在墙上的电子钟正好跳转到下午三点整。 张文斌从人造革手提包里掏出个铁皮饼干盒,生锈的盒盖里嵌着张黑白照片。 十岁的张菊芬扎着两条麻花辫,眼角微微上挑的模样和张淑凤十一岁的证件照如同复刻。 "2006年正月初十走的,临走前非要买去黑龙江的火车票。" 张文斌摩挲着饼干盒上的牡丹花纹,"我们当她惦记着当年插队的朋友,哪知道......" 演播厅的射灯在张淑凤眼前晕开光斑,她仿佛看见生母蜷缩在病床上,枯瘦的手指在列车时刻表上反复摩挲。 节目录制结束后的第三天,张淑凤收到个来自上海的包裹。 褪色的蓝布棉袄里裹着本红色塑料封皮的日记本,1970年的日历页上画着歪歪扭扭的婴儿脚印,腊月初八那天用铅笔写着:"今天把心留在黑龙江了。" 棉袄口袋里还装着张泛黄的车票,2004年3月12日,上海至哈尔滨的硬座票,票根上印着"已退"的蓝色印章。 如今张淑凤的衣柜深处,那件蓝布棉袄和养母织的枣红毛衣叠放在一起。 每年清明,她都会往东北方向摆两碗饺子,一碗撒上养母爱吃的辣椒油,一碗浇着生母寄来的虾子酱油。 窗外杨树梢上的麻雀叽喳吵闹,屋里电视机正重播着当年的寻亲节目,片尾曲悠悠唱着:"时光偷走的选择,总在用另一种方式回来......" 对此您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