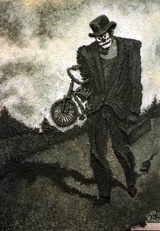那年我17岁,秋日的傍晚,我蹲在灶台前,小心翼翼地往火堆里添着干柴。 灶膛里的火苗忽明忽暗,映照着我那张被烟熏得有些发黑的脸。 十七岁的少女,本该是如花般的年纪,可生活的重担早已在我眉间刻下与年龄不符的纹路。 屋外,暮色笼罩着这个位于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几盏昏黄的灯光稀稀落落地亮起,像是被遗忘在群山中的萤火虫。 我家所在的青石村,是县里有名的贫困村,人均年收入不足两千元。 晚饭后,我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亮,在斑驳的木桌上摊开课本。今年初三,即将面临中考。 班主任李老师说,以我的成绩,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不成问题。 可每当想到这里,我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 五年前,父亲在县城打工时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没等送到医院就断了气。包工头赔了三万块钱,可父亲治病欠下的债就有五万多。 这些年,母亲一个人种地、打零工,硬是把债一分一分还清了。 “要不...我初中毕业就去打工吧。”我咬着嘴唇说,“隔壁王婶说,她女儿在南方工厂,一个月能挣两千多呢。” “林小梅,你给我听好了。”母亲一字一顿地说,“你爸临走前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闺女读书'。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高中!” 那一刻,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炸开,热流涌向四肢百骸。扑进母亲怀里,泪水浸湿了母亲洗得发白的衣襟。 中考结束后的那个夏天,李老师顶着烈日,走了两个多小时山路来到小梅家。 她带来了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还有一个好消息——学校了解到我家的情况,决定减免部分学费,李老师自己也愿意资助一部分。 “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李老师对母亲说,不继续上学太可惜了。 就这样,带着全村人凑的八百块钱和母亲熬夜纳的三十双鞋垫(卖了二百多块钱),我踏上了去县城的路。 临行前,母亲把缝在内衣里的五百块钱交给她,那是家里最后的积蓄。 县一中的生活远比我想象的艰难。城里同学谈论的明星、电视剧、网络游戏,对她来说如同天方夜谭。 我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乡音,经常引来哄笑;她不知道自动取款机怎么用,第一次见到电梯时手足无措。 但我有一个谁都比不上的优势——比任何人都刻苦。每天清晨五点,当室友们还在熟睡时,我已经悄悄起床,在教学楼前的路灯下背书。 晚上熄灯后,我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做题。三年里,她的成绩始终保持在年级前十。 高考那天,母亲特意从村里赶来,在校门外等了一整天。当最后一科结束的铃声响起时,我冲出考场,看见母亲站在烈日下,手里捧着一瓶已经晒得温热的矿泉水。 “妈,我觉得我能考上!”我兴奋地说。 一个月后,录取通知书送到了青石村——我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被省城师范大学录取。 消息传开,整个村子沸腾了。我是青石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 大学四年,我靠着奖学金、勤工俭学和助学贷款,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 我在食堂打工换取免费三餐,在图书馆整理书籍赚取生活费。 每个寒暑假,我都留在城里做家教,把攒下的钱寄回家。 毕业季,当同学们忙着投简历、参加各种招聘会时,我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她报名参加了农村教师特岗计划,申请回到家乡所在的县城中学任教。 回到县城任教的第一天,我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四十多双或好奇或怀疑的眼睛。他们中有一半来自周边农村,有些孩子的鞋子上还沾着泥巴。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新语文老师,林小梅。"我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转身时,看见教室后排一个瘦小的女生正低头摆弄着破旧的文具盒,那神情像极了当年的自己。 下课铃响起,我叫住了那个女生。“你叫什么名字?”她轻声问。 “老师,我叫周小花。”女孩怯生生地回答,手指不安地绞着衣角。 “小花,放学后能留下来吗?老师有些书想送给你。” 夕阳西下,空荡荡的教室里,我把自己珍藏的几本课外书递给周小花,还有一盒崭新的文具。“老师也是从山里走出来的,”她柔声说,“只要你愿意努力,一定能走得更远。” 回家的路上,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电话那头,母亲兴奋地告诉她,村里通了水泥路,乡里还建了个小型农产品加工厂,她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工资不高,但比种地强多了!”母亲的声音里满是喜悦,“对了,你李老师退休了,昨天还问起你呢...” 挂断电话,我站在新修的大桥上,望着远处连绵的群山。暮色中,山脚下的村庄亮起点点灯火,像散落的星辰。 我想起十五年前那个蹲在灶台前添柴的小女孩,想起煤油灯下苦读的夜晚,想起母亲那句“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学”。 一滴泪水滑过脸颊,我轻轻擦去。我知道,自己改变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还有那些像周小花一样的孩子们未来的可能性。 这条路很长,但我会坚定地走下去,就像当年走出大山时一样,一步一个脚印。 (来源于身边人的故事,以第一人称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