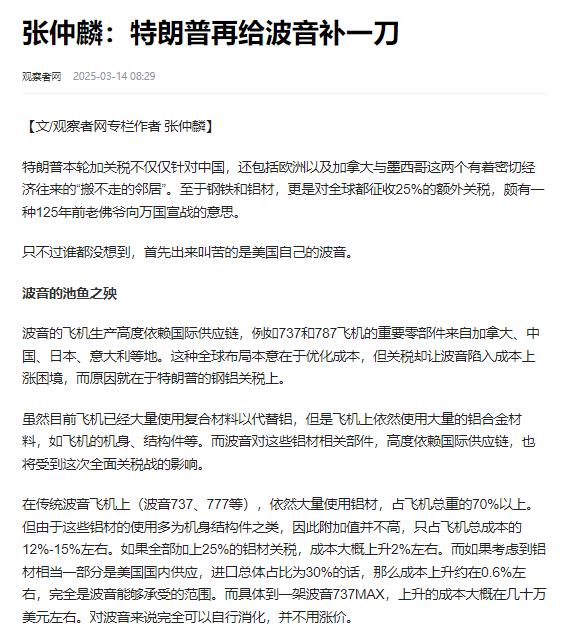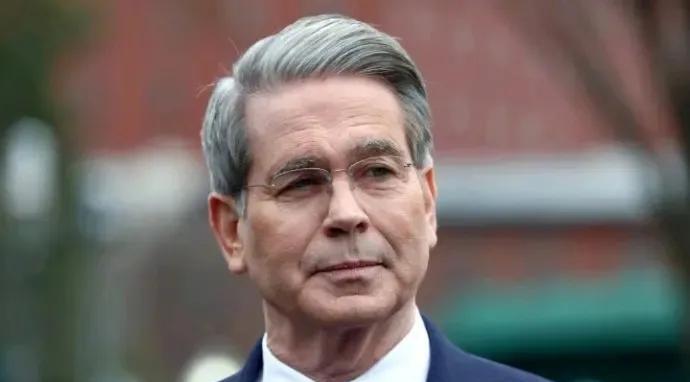看了李嘉诚,才知道霍英东有多伟大!听了他的事,你就明白了,霍老花60亿搞了个大项目,眼看要赚翻了,却用1块钱卖给了国家,别人忙着捞钱,他忙着给国家出力。这1块钱,买不了啥,却换来了国家的未来。 九十年代南沙新城的工地上,戴着安全帽的霍英东正用广东话和工程师讨论着填海方案,海风掀起他灰白的发梢;同一时刻,李嘉诚的私人飞机正从伦敦希斯罗机场腾空而起,舷窗上映出他翻阅财务报表的侧影。 这两幅画面定格着香港商业史上最意味深长的镜像——有人把算盘珠子拨得噼啪作响,有人把家国账本刻进血脉。 要说霍英东的生意经,得从他七岁那年说起。那时候他家住在香港的舢舨上,全家老小挤在不足十平米的船舱里,咸鱼味和海腥味浸透了童年记忆。 日军打来那年,母亲带着他们逃到岸上,少年霍英东在码头扛大包,肩膀磨出血泡也不敢吭声。五十年代初,这个浑身鱼腥味的穷小子带着几条旧船闯荡江湖,谁也没想到他能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 抗美援朝那会儿,西方列强把大陆围得铁桶似的。霍英东的船队昼伏夜出,橡胶、药品、汽油这些紧俏物资藏在煤堆底下,英国军舰的探照灯扫过来,水手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 有回在公海上被截住,霍英东急中生智把整船白糖倒进海里,等海关人员登船检查,只剩空荡荡的船舱对着他们冷笑。这种提着脑袋做买卖的日子,他硬是撑了三年,大陆的军需物资供应线愣是没断过。 到了改革开放春风吹起来的时候,别的港商还在观望,霍英东已经带着施工队进了广州城。白天鹅宾馆的蓝图刚铺开,外国专家直摇头,说中国人根本造不出五星级酒店。 霍英东蹲在工地啃着盒饭,亲自盯着大理石地面拼花,大厅里那组"故乡水"假山景,是他特意请岭南画派大师设计的。 开业那天,穿着补丁衣服的老广们挤在大堂看西洋镜,霍英东站在旋转门前笑得见牙不见眼——这是新中国头一回让老百姓随便进出高级宾馆。 南沙那片烂泥滩,霍英东前后砸进去六十个亿。九十年代初的六十亿是什么概念?够在尖沙咀盖十栋写字楼。政府批文没下来,他就自掏腰包修路架桥,围海造田的推土机轰隆作响,连他儿子都嘀咕这是往咸水海里扔钱。 等到自贸区的金字招牌挂起来,老爷子掏出皱巴巴的合同,以一块钱象征价把三千亩黄金地块转给国家。记者会上有人问亏不亏本,他摆摆手:"南沙搞好了,全中国都赚了。" 比起霍英东的"赔本买卖",李嘉诚的生意经透着股精明劲儿。五十年代靠塑胶花发家,六十年代抄底香港楼市,九十年代进军内地基建,这位"李超人"总能在时代转折点精准下注。 北京东方广场项目谈下来的时候,长安街沿线的机关单位都得给他腾地方,这份魄力确实了得。不过老百姓茶余饭后嚼舌根:李老板的吊塔立在哪里,哪里的房价就得翻跟头。 要说这二位最大的不同,得看他们怎么对待钱袋子。霍英东的霍英东基金会,钱像流水似的往内地教育医疗里灌。韶关山区的希望小学、中山医院的CT机、亚运会的游泳馆,处处都有他捐钱的影子。 非典闹得最凶那年,他带着医疗队往北京冲,小汤山医院的地基还没打完,霍家的建筑材料已经堆成小山包。反观李嘉诚的慈善账本,虽说汕头大学建得气派,可媒体总盯着他海外基金会避税的传闻不放。 政商关系这门学问,两位大佬也走出了两条道。霍英东八十年代就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常有他的身影。他家老二霍震寰跟着国家代表团出访,见着外国元首也不怯场。 李嘉诚倒是把"在商言商"挂在嘴边,九七回归前夜,人家请他当政协领导,他摆摆手说要专心做生意。可等到抛售内地资产转战欧洲时,官媒那句"别天真"的敲打,到底让他折了面子。 南沙海滨的霍英东纪念馆里,参观者总要在那块"一元钱地价"的展板前驻足。玻璃柜里泛黄的合同书上,霍英东的签名力透纸背。 讲解员说,老爷子晚年坐着轮椅都要来南沙转转,看见集装箱码头灯火通明就咧嘴笑。 如今自贸区每年上千亿的进出口额,哪个数字里没浸着当年那六十亿本钱? 维多利亚港的夜景依旧璀璨,太平山上的豪宅亮着星星点点的光。霍家的第三代开始涉足体育外交,李家的孙子辈在伦敦搞科技投资。当人们比较这两位传奇人物时,常说霍英东赚的是民心,李嘉诚攒的是真金。 可要论谁在历史长河里留下了更深的水痕,看看广州城里的白天鹅展翅,看看南沙新城的车水马龙,答案早已写在神州大地的春风里。 主要信源:(中国日报网——霍英东:一生爱国的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