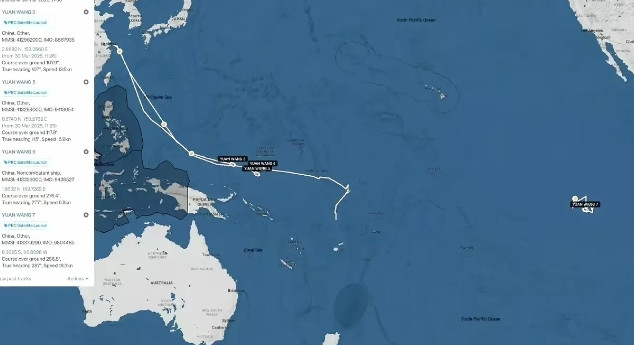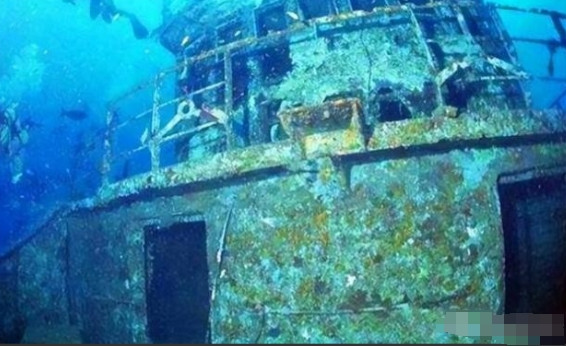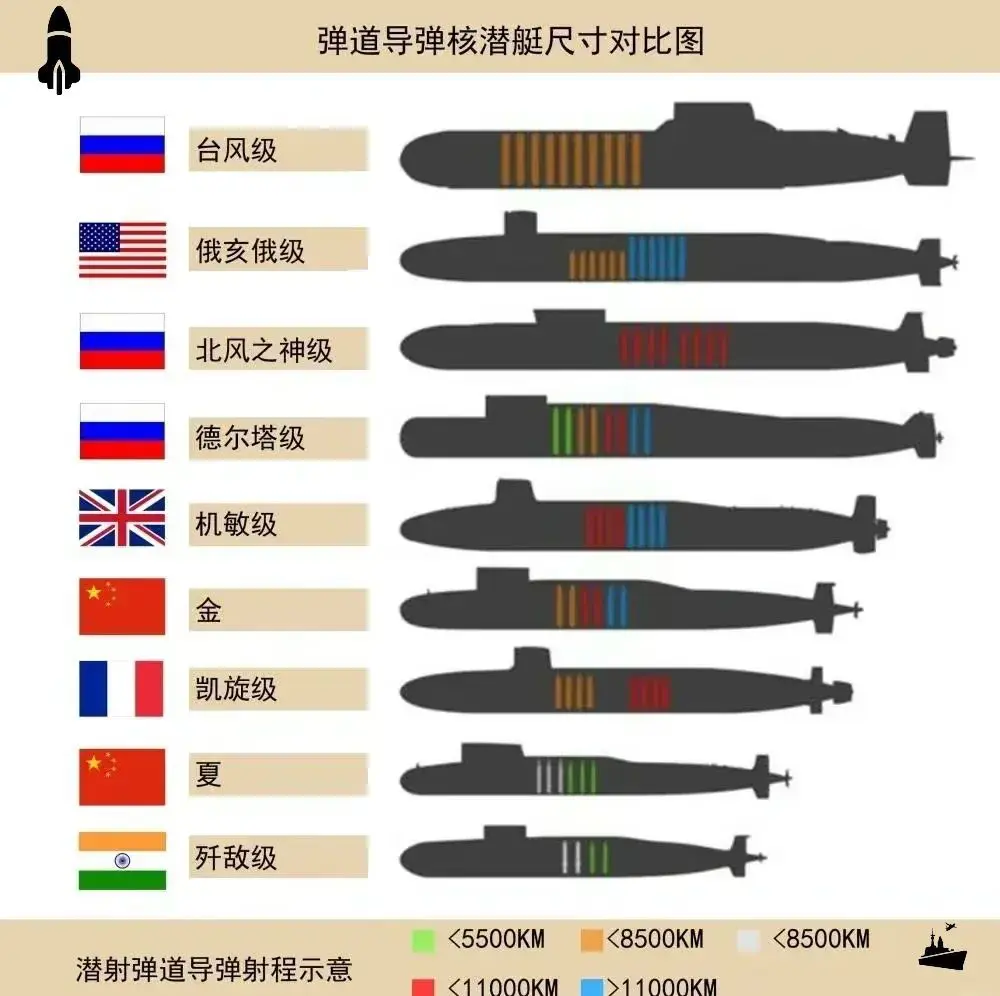1988年,“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便回家看望93岁的母亲。谁知母亲看着多年未见的儿子,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988年春天,一辆黑色轿车颠簸着开进广东汕尾的乡间小路,车里坐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贴着车窗往外张望,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公文包上的铜扣。 依稀记得30年前离开时,这条路还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如今柏油路面平整宽阔,路两旁盖起了三层小楼。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见老人眼眶泛红,递过纸巾时问了句:“黄总师,这趟回家该高兴啊?”老人摆摆手没说话,目光落在远处山坡上一棵歪脖子老榕树,那是他离家前和兄弟们爬树摘果子的地方。 老宅门口晒着咸鱼干,穿灰布衫的老太太正弓着腰翻竹篾,他下车时踩到块松动的石板,响声惊得老太太直起身子。 两人隔着十来步距离对望,老太太手里的咸鱼“啪嗒”掉在地上,她颤巍巍往前挪了两步,突然用潮汕话喊出句:“老三?”这声呼唤像把钥匙,“咔嗒”拧开了尘封30年的记忆。 事情得从1958年春天说起,刚满30岁的黄旭华在上海造船厂干得风生水起,某天突然被领导叫去北京“临时出差”。 他拎着个藤条箱就上了火车,以为顶多3个月就能回来,谁知到了北京西郊的破旧办公楼,领导指着墙上的批示说:“从今天起,你就是19号信箱的人。” 核潜艇属于最高机密,他签完保密协议才知道此事,不能说自己在哪,也不能透露工作内容。 头两年还能往家里寄信,信封上永远只写“北京XX信箱”,母亲来信问他在哪个单位,他咬着笔杆想了整宿,最后回信说:“我在首都当技术员,单位管得严。” 1964年深秋,黄旭华跟着团队搬上渤海湾的荒岛,岛上连棵遮阳的树都没有,七八级海风刮得人脸生疼,他们在油毡棚里搞研究,冬天裹着棉被画图纸,夏天光着膀子打算盘。 有回为了算潜艇耐压数据,30多人打算盘算了整礼拜,草稿纸堆起来比人还高,隔壁木工棚的老师傅看不下去,用边角料给他们做了个潜艇模型。 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木头模型后来成了攻克“水滴型”设计的关键道具。 奈何家里情况越来越糟,弟弟来信说父亲咳血住院,末尾添了句:“全家就你不知道爹病了。”他捏着信在礁石上坐到半夜,涨潮海水漫过脚背都没察觉,第二天去工作时,他裤脚上还结着盐霜。 一直到1970年冬天,黄旭华带着团队在葫芦岛做耐压壳试验,零下20度的天气里,他裹着军大衣盯了三天三夜,当直径四米的钢铁巨兽成功扛住30个大气压时,现场突然爆发出哭喊声,几个东北汉子抱着结冰的钢管又哭又笑。 那天食堂破例给每人发了二两白酒,他抿了口就呛出眼泪,不知是辣还是想起病榻上的老父亲。 深潜试验前夜,基地来了群特殊客人,海军司令员带着两筐苹果走进宿舍,挨个和科研人员握手,走到黄旭华跟前突然立正敬礼:“黄总师,明天我陪你们下潜。”这话把在场所有人都震住了。 要知道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试潜时,艇上129人全部遇难,黄旭华攥着苹果的手直发抖,最后只说:“司令员要坐镇指挥,我替您下去看数据。” 1988年4月29日,南海某海域波光粼粼,当他套上橘红色救生衣时,小刘突然冲过来抱住他:“总师,我媳妇快生了,您给娃起个名吧?”他愣了下,看着浪花,脱口而出:“叫海生,怎么样?” 潜艇下潜到200米时,钢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呻吟,黄旭华贴着内壁听声响,手里钢笔在记录本上戳出好几个洞。 当深度表跳到300米临界点,整个舱室安静得能听见冷汗滴在钢板上的声音。 10分钟后,艇长哑着嗓子宣布:“所有设备正常!”黄旭华这才发现后槽牙咬得生疼,松开时满嘴血腥味。 3个月后,黄旭华带着“共和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头衔回到汕尾,街坊邻居早从电视上见过他领奖的画面,先前说他“不孝”的几个老人臊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母亲把政府送来的“英雄之家”牌匾挂在堂屋正中,每天拄着拐杖在巷口转悠,逢人就指着电视重播的新闻片段:“瞧见没?这是我老三!” 石榴树还是30年前的模样,黄旭华蹲在树下烧纸钱,青烟缭绕中仿佛看见父亲坐在藤椅上看报,火苗燃烧到纸角瞬间,忽然想起离家的清晨,父亲往他箱子里塞了包猪油糕:“在外头别饿着。” 灰烬被风卷着飞过院墙,落在远处新修的核潜艇主题公园雕塑上,那座10米高的钢铁巨兽昂首向海,阳光在流线型外壳上折射出耀眼光斑。 如今90多岁的黄旭华仍保持着早年的习惯,每天清晨沿着武汉东湖走3公里,经过湖边那座刻着“水下长城”的纪念碑时,总会驻足摸摸基座上密密麻麻的姓名。 有回被晨练的市民认出,老人笑呵呵指着碑文说:“这上头该添我老伙计的名字,他们才是真英雄。”湖面掠过一群白鹭,翅膀拍打声惊碎了水中的倒影。 信息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黄旭华:隐“功”埋名三十载,终生报国不言悔、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中国核潜艇之父”的深潜人生——央视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