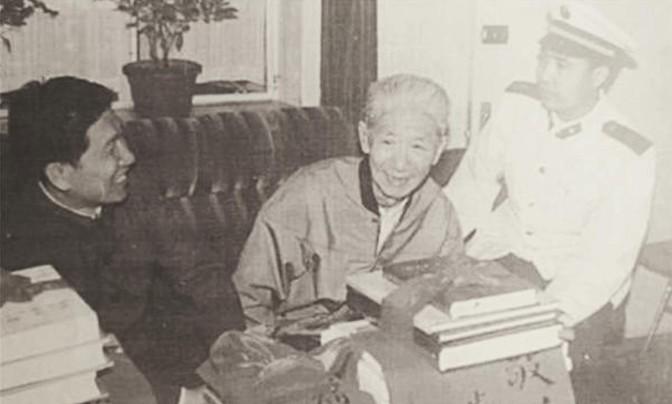1945年,陈芝秀抛下年幼子女和丈夫常书鸿,跟下属私奔。多年,与女儿在杭州相遇,她衣衫褴褛,目光呆滞,已下嫁工人并生下一子。她的一句话,让女儿深感理解,还每月寄钱给她。 1927年,二十出头的常书鸿怀揣着艺术梦想踏上了法国的土地,第二年,他的妻子陈芝秀也跟随而来。这对表兄妹组成的夫妻,就这样开始了他们在艺术之都的生活。 在巴黎的光影交错中,常书鸿的画笔越发挥洒自如,他的作品多次获得法国国家级的金质奖与银质奖,成为华人艺术家中的佼佼者。而陈芝秀也不甘示弱,在丈夫的鼓励下,她学习法语,钻研雕塑艺术,最终与常书鸿一同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她衣着时尚,热爱法式香水,戴着画家帽,完全融入了巴黎的精致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中国留学生圈子里,这对夫妻可谓是令人羡慕的艺术伴侣。 然而,美好的巴黎时光在1936年迎来了转折。那年,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一个旧书摊上偶然发现了一本敦煌石窟图录。翻开这本书,大量精美的敦煌唐代绢画震撼了他的心灵。这位在西方艺术殿堂中浸淫多年的画家,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无穷魅力,也意识到这些文化瑰宝正在遭受风沙侵蚀和外国掠夺。 在一个平常的晚餐上,常书鸿向妻子宣布了回国的决定。陈芝秀起初以为是个玩笑,但看到丈夫坚决的神情,她慌了。他们为此争执不休,常书鸿谈理想和责任,陈芝秀则指出现实的困难。最终,陈芝秀还是做出了迁就,她对常书鸿说,愿意陪他一同回国,实现他的理想。 1937年夏天,陈芝秀带着六岁的女儿和大量行李,依依不舍地踏上了归国的轮船。然而,命运给这对夫妻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就在她的船即将靠岸时,全面抗战爆发了,北平已经沦陷。转眼间,陈芝秀满心期待的回国生活,变成了无尽的逃难。 终于,在重庆的山城,他们暂时安定下来。尽管生活条件依然简陋,陈芝秀仍然竭尽全力让这个小家温馨舒适。她常对女儿说,即使外面天下大乱,家里也不能乱。在这段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他们的小儿子嘉陵也出生了,给这个饱经风霜的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 1942年,常书鸿接受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主任的职务,决心前往更为艰苦的大西北工作。在这片黄沙漫天的土地上,陈芝秀的信仰和耐心都被无情地磨蚀。离教堂遥远的环境让她只能对着墙上的圣母像祷告,而艰苦的生活条件和与丈夫日益增长的矛盾,让她的内心愈发绝望。 1945年4月19日,陈芝秀借口到兰州教会医院看病,却与研究所里一位国民党退役的小军官悄然离去。起初,常书鸿毫无察觉,直到学生递来截获的信件,他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常书鸿立刻骑马追赶,一路风尘仆仆直奔玉门关。然而命运弄人,他在途中从马上摔下,昏迷不醒。等他被人救起后,仍不顾一切想要继续追寻,却被人递上一份报纸,上面赫然是陈芝秀在兰州登出的离婚启事。 对于陈芝秀来说,私奔后的生活并未如她所愿。与那位军官结婚后不久,丈夫就因政治原因入狱,并在狱中去世。失去依靠的陈芝秀,从一个曾经在巴黎艺术圈闪耀的女雕塑家,沦落为社会底层。 最终,这位曾经穿着时尚、喷洒法国香水的艺术家,改嫁给了一个普通工人,生下了一个儿子。那双曾经创作精美雕塑的手,如今只能为街道干洗衣服,勉强维持生计。从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的天才学生,到杭州街头的洗衣工,陈芝秀的命运跌宕起伏,令人唏嘘。 直到1962年,已是中年的常沙娜在苏杭公干时,通过大伯的牵线,与失散十七年的母亲重逢。这次相见,让常沙娜震惊不已。站在她面前的,不再是记忆中那个优雅美丽、打扮入时的母亲,而是一个头发蓬乱、面无表情、衣着朴素的老妇人。 在一块青阶石板上,母女俩没有预想中的热泪盈眶,而是平静地交谈。当常沙娜质问母亲是否真的不爱父亲时,陈芝秀回答说她爱,但爱得太累了。她并不爱那个军官,他只是能带她离开的人。 这句话触动了常沙娜的心弦。虽然当时她没有表现出来,但这次见面后,她开始背着父亲每月给母亲寄钱,从五块到十块不等。尽管中间有段时间因压力而中断,但后来又恢复了,一直持续到1979年。 就在那一年的八九月份,陈芝秀的丈夫和儿子向常沙娜报告了一个噩耗:母亲因过度激动突发心脏病猝死了。讽刺的是,就在她去世前一天,她年轻时的好友马光璇刚到达杭州,正准备第二天去探望她。这成为了生命中最后的遗憾。 同年十月,已经成为国宝级艺术家的常书鸿带着现任妻子李承仙到日本出访,常沙娜也随行。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常沙娜简单地告诉父亲:"妈妈去世了。"这个消息让常书鸿的表情凝固了,他反复询问何时何故,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无法接受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