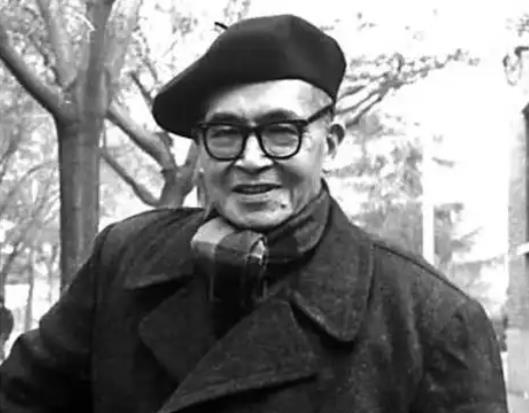1933年,钱钟书追求燕大校花赵萝蕤,可赵萝蕤根本没有看上他,而是喜欢当时一文不名的穷小子,没想到她的原因非常简单又实际:他长得好看。 北京,燕京大学校园里春意正浓,赵萝蕤坐在图书馆门口晒太阳。 有人问起“怎么看上了陈梦家”,她没犹豫,眼一亮,说了句:“长得太漂亮了。” 一句话砸下来,旁边人笑,有人摇头,有人说“肤浅”,赵萝蕤抬眼看天,一脸坦然。 “他睫毛在灯笼下忽闪忽闪的,像极了《牡丹亭》里的柳梦梅”,她说得认真。 这不是玩笑,也不是矫情,是一种本能的偏爱。 一个在诗书堆里泡大的姑娘,看惯了才子才女,忽然碰见一个眼睛亮、鼻梁高、轮廓干净的少年,自然心动。 陈梦家那时候穿着洗到发白的旧长衫,借住在赵家阁楼,常常一根馒头配一碗水,但眉眼疏朗,站着像棵竹。 周围人议论,赵萝蕤不解释,她从来不掩饰对外貌的执着,也从不觉得这有错。 喜欢美,是底色,不是什么羞于启齿的事。 尤其是在那个“婚姻听父母”的年代,赵萝蕤开口说喜欢谁,就像当街扔块砖,砸得人措手不及。 偏偏她还不太买账陈梦家的诗。 问起来就一句:“不喜欢,但他长得太漂亮了。”坦白得像个刺。 不是才华,不是家世,单就一张脸,一个身形,一个不肯低头的背影,值了。 这份“看脸”的感情,起初并不被祝福,赵紫宸,赵萝蕤的父亲,宗教学院院长,自认斯文门第,看不上陈梦家这副“寒酸骨”。 一个靠写诗混饭的青年,拿什么娶自己女儿? 于是断了生活费,软硬兼施,连朋友也被拦着不许资助。 赵萝蕤不听,死扛,靠奖学金吃饭,向杨绛借钱,一本书一本书翻译赚稿费,衣服补了又补。 两年时间,水米无声,连一句抱怨都省了,父母不松口,她就不松手,死磕到底。 这场恋爱里,钱钟书是绕不过的插曲。 那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国文、英文双满分,出身好、文凭硬,留洋背景加满分才气。 追求方式也够铺张:中英法三语十四行诗、夹玉兰花的《唐璜》、信封边上写满希腊文注释……一整个套装的“文人浪漫”。 但赵萝蕤只皱眉:“太匠气。” 写得多,不如写得准;才华重,压得人喘不过气。 她要的不是纸面才子,是那种写诗唱歌、专注挖甲骨的自由气。 钱钟书太用力,反而显小家子气。 陈梦家反而松弛,拉着吉他唱英文民谣,研究甲骨时能整整几天不说话,眼神里全是事。 赵萝蕤盯着他看,看出一个“沉进去的人”,看出个不靠炫技、不做作、不卖弄的骨头。 这一看,就是一辈子。 1936年,两人终于顶着全家的反对,在司徒雷登办公室结婚,连婚礼都省了,随手订个日期,签完字走人。 陈梦家去了西南联大任教,赵萝蕤也辞职,搬去跟着过日子。 没房没地,床是旧的,碗是缺的,她却照样洗衣做饭,空了翻译《死了的山村》,一边照顾家,一边写作不辍。 婚后几年清苦,靠翻译赚点小稿费,孩子吃药的钱都得先问人借。 可两人一合眼,依旧觉得日子有意思,有柴有米,没光没电,都能靠着对方撑下去。 陈梦家后来进了考古界,发掘甲骨文,参与编写《甲骨文合集》,身份从“浪漫诗人”变成了“严肃学者”,一头扎进黄土里不出来。 赵萝蕤继续翻译、教学、辅佐,文艺圈、学术圈两头有人记住名字。 风雨从未断过,1966年陈梦去世,赵萝蕤身边连个纸条都没留下。 之后,是独活,是病痛,是精神崩裂,脑子开始分不清人,记忆断成一块块,可她咬牙翻完了《草叶集》,翻得慢,也翻得准,每翻一页都像往胸口砸一锤。 这部书,是她送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赵萝蕤走的时候,没惊动多少人,那时的书刊不再提这对恋人,不再提他们的美貌、冲撞、顽抗、坚持,只剩翻译目录里一个名字。 可在那个时代,要坚持自由恋爱,要顶着门第压力选“穷书生”,要用自己的一生证明“美也值钱”,不是容易事。 她没妥协,也没装高尚,她说喜欢,就是喜欢,她要过,就真去过。 陈梦家早走了,赵萝蕤迟了一步,他们像两个时代的哑火焰,一前一后,烧在纸面,也烧在人心上。 参考资料: 傅国涌,《赵萝蕤:漂亮是正义》,载《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