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著名二胡演奏家储师竹正在上课,突然叫停学生的训练:“这是什么曲子,谁写的?”学生老实回答:“这是无锡街头一个瞎子艺人瞎拉的。”没想到,这件事竟然拯救了一首世界名曲。 南京,一个学生无心拉了一段旋律,全班静了,讲台上的储师竹一愣——这旋律像刀子,往心口扎问了来源,学生说是在无锡听一个盲人拉的。 储师竹没多说,课一结束就直奔无锡。 街头巷尾问了几天,终于在小桥边找到了那人——脏袍破帽,满脸胡茬,坐在小凳上拉琴,腿边搁着个破碗,琴音一响,四下安静,像下雪一样静。 那人叫华彦钧,江湖上喊“阿炳”,不是普通的瞎子,生得复杂,爹是道士,娘是寡妇,小时候被丢养观里。 天生耳朵灵,手指快,八岁拉道教音乐能顶半个乐班,十八岁开始出名,一出庙门就跑江湖,交友混乱,染上鸦片、梅毒,三十五岁彻底瞎了眼。 家产败光,从“天才道士”落到街头乞讨,拉琴卖艺。 但谁听过他拉一遍,都忘不了那旋律,像命运在嘶吼。 储师竹不敢耽误,把消息火速写信给杨荫浏——当年学琵琶时就听说阿炳,早年还拜过他学曲。 两人合计,要把这音乐抢救下来,可阿炳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再不录,怕是带着绝响走人间。 1950年清明,黎松寿先记了谱。 阿炳不识字,全凭耳朵听、手感拉,每一个指法,每一段停顿,全靠几十年街头风雨磨出来。 秋天,杨荫浏设法借到一台钢丝录音机,几人扛到无锡——大件,重得要命。 那天,阿炳破天荒洗了澡,换了件干净长衫。 拉琴时背挺得笔直,没人敢说话,第一段一出来,杨荫浏眼圈就红了——不是音准的问题,是那股劲儿,从骨头缝里冒出来的。 那天共录了六首,《二泉映月》排在第三,阿炳拉完就喘,牙关发紧,额头冷汗直冒。 录完后,几人都没说话,只听阿炳低声说:“这下安心了。” 三个月后,阿炳去世,没挺过那个冬天,可这首《二泉映月》,从那天开始变了命。 曲名是现场起的,灵感来自无锡惠山,那地方有口“天下第二泉”,旁边龙光塔影照水面。 杨荫浏说,像极了这曲子:一半是水的清凉,一半是塔的沉重,名字起得稳准狠——听着像风景,实际是人生。 旋律里没有大起大落,没有花哨炫技。 主旋律反复十几次,但每次都不一样,像人活着,每天都差不多,可谁心里没点波澜? 一弓下去,不是哭,是活着撑出来的那口气。 有人听见的是孤独,有人听见的是哀悼,有人听见的是盼。 阿炳没说过曲子什么意思,他自己也说不清,但街头雨雪、亲人早逝、眼前黑暗、骨子里那点傲气,全都在里头了。 这不是一首曲,是一条命的浓缩。 遗憾也从这开始,阿炳一生写过三百多首曲,没记谱的全没了,唯独《二泉映月》因为这一晚,留下来,成了人类文明的一块化石。 后来这首曲飞得更远,1977年,美国NASA发射旅行者一号探测器,带着“金唱片”——里面塞了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音乐。 除了巴赫、贝多芬,还有这首出自中国街头盲人艺人的《二泉映月》。 阿炳没听说过太空,他活着的时候,饭都吃不饱,但留下的旋律,比大多数人活得都久远。 人死了,琴还在拉,有人说阿炳是“中国贝多芬”,也有人说他比贝多芬苦多了——贝多芬耳聋,他是眼瞎; 贝多芬有房子住,他住道观屋檐;贝多芬有酒喝,他喝凉水;贝多芬被尊为大师,他拉完琴还要等人扔铜板。 可两人音乐里那种怒、那种忍,那种没说出来却让人听懂的火,一模一样。 中国早年老百姓穷,没几人写谱、记声、录音。民间音乐就像草原野火,烧过就没了痕迹。 阿炳要是再晚死两年,说不定哪天路边一病倒,琴一扔,这首《二泉映月》也跟着灰飞烟灭。 所以这曲能留下,是个奇迹。 现在谁都说它是民族遗产、艺术经典,但那年冬天在无锡,谁也没想到。 一位快死的盲人艺人,几位拼命抢救的学者,还有一台沉得像铁块的录音机——就靠这几样,硬是把一个快灭的声音从岁月缝里拉出来。 有些艺术,不靠天赋,不靠系统,全靠命悬一线时那口气。 参考资料: 王建国. 阿炳与《二泉映月》:音乐史上的传奇.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8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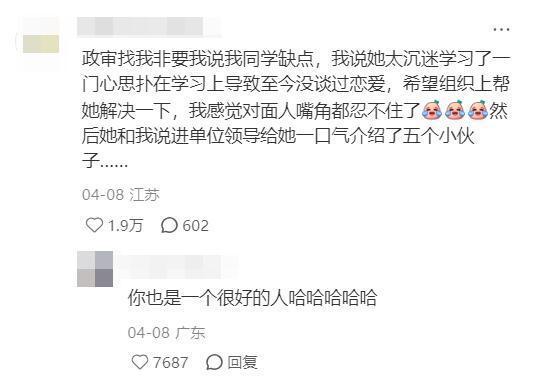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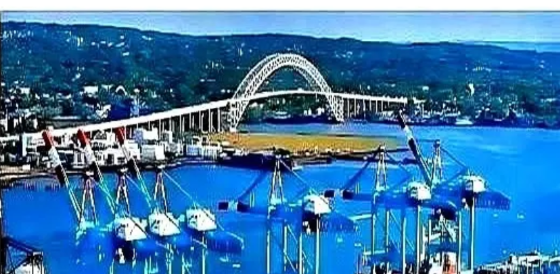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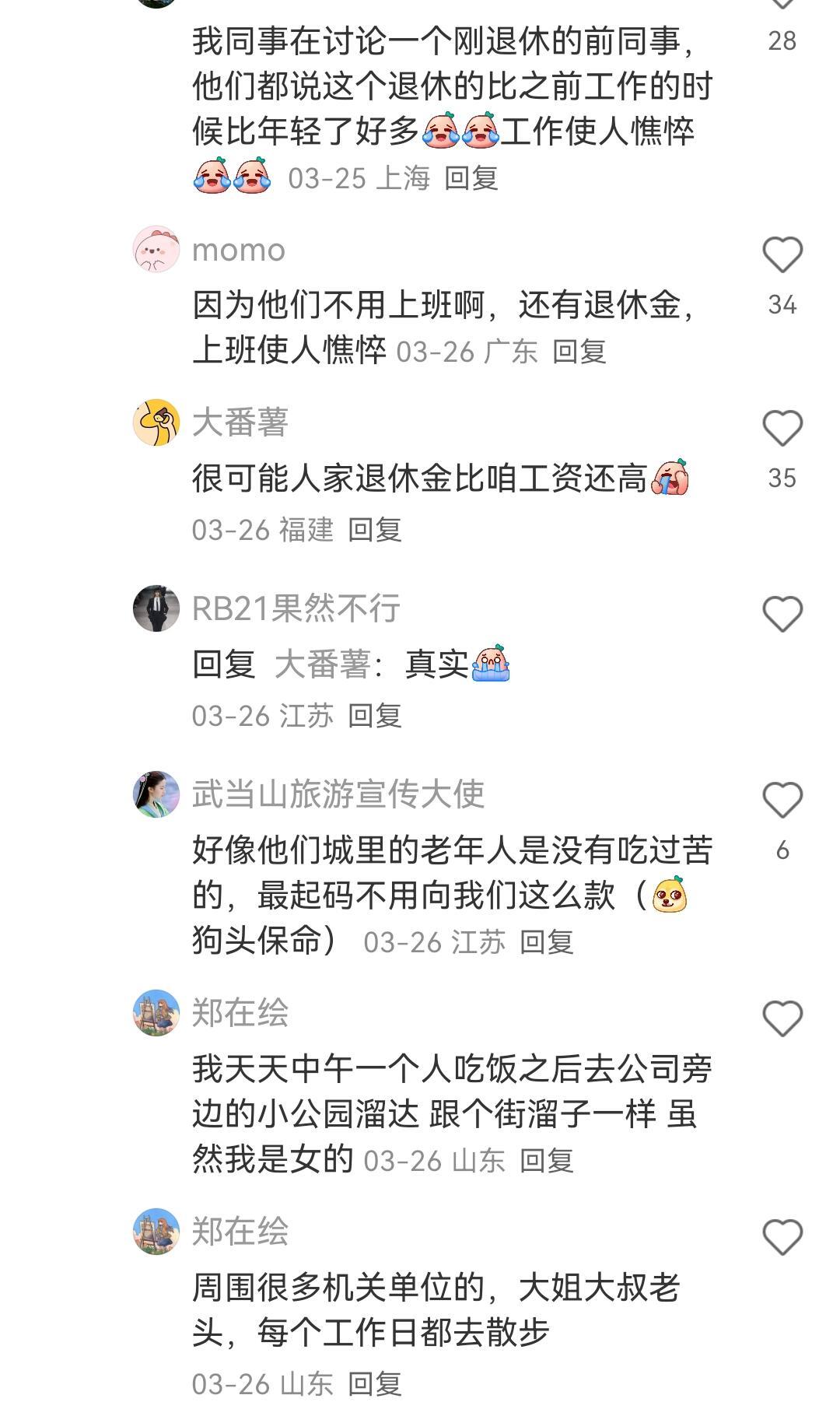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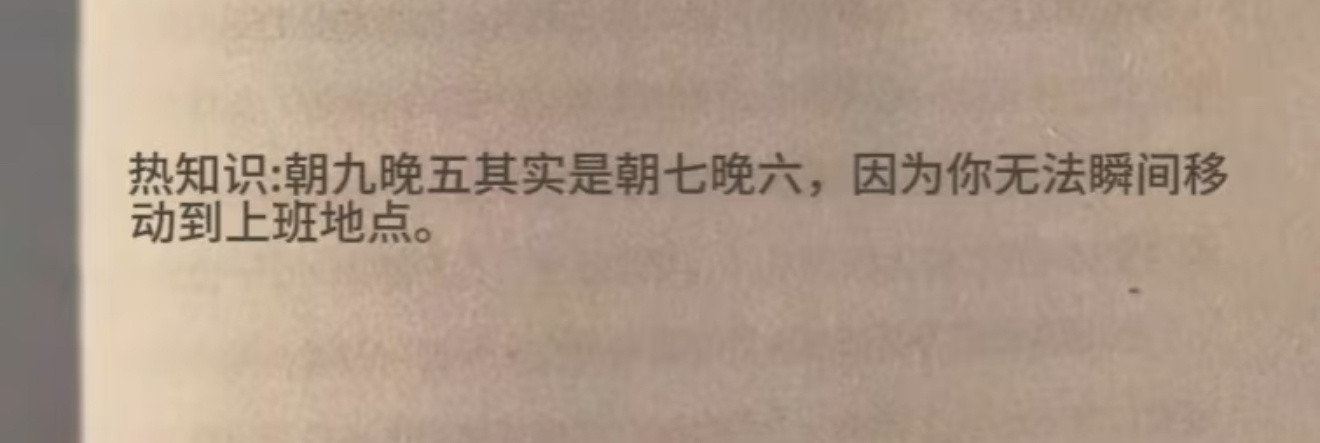
![央妈这发文速度和莎莎球速,也和莎莎下班一样快[赞][赞]这手速太快了](http://image.uczzd.cn/5469089903124741202.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