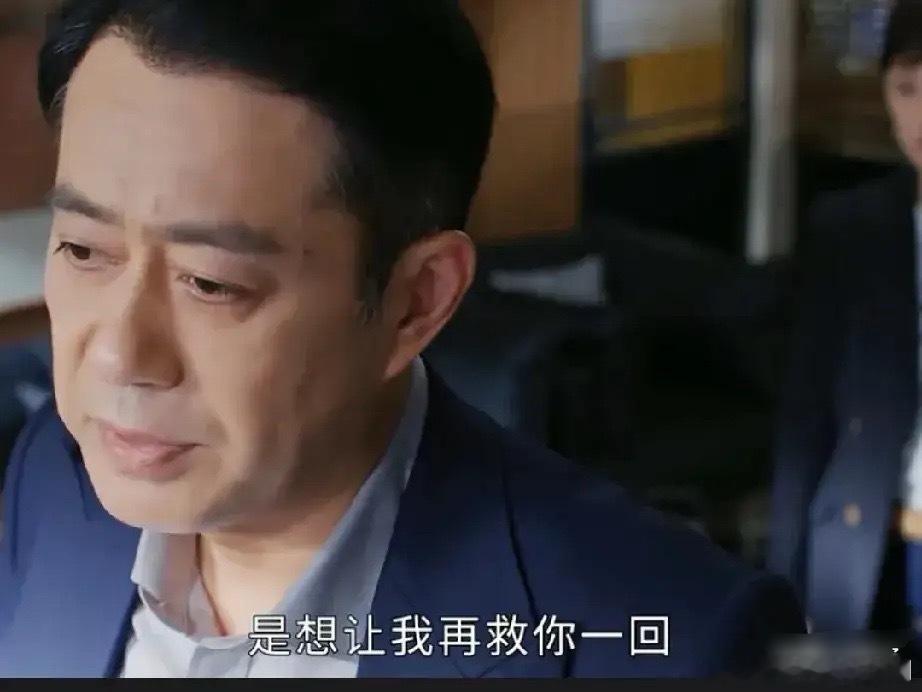1930年,25岁的《雨巷》诗人戴望舒,站在楼顶上,对着楼下一名20岁的少女哭喊:“不和我订婚,我就跳下去!”少女吓得面色发白,连声道:“我答应你!”谁知,几年后,戴望舒却当着众人的面甩了少女一耳光。 这一幕,成了许多年后许多人口中的谈资,也成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抹不可忽视的情感裂痕。 施绛年,是文化人施蛰存的妹妹,施蛰存与戴望舒私交甚笃,两人同为新文学倡导者,经常在上海各文艺沙龙中一同露面,讨论诗艺与人生。 也正因这层关系,戴望舒才得以在施家出入,才得以第一次,在一个春日下午见到施绛年。 她不过是静静坐着,一袭淡蓝旗袍,眼神清澈,笑意浅浅,却在戴望舒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他甚至在日记中写下:“如梦中少女,忽然临凡,来唤我魂。”他心动了,而且是彻底的沉溺。
对他而言,那是“灵魂的伴侣”,但对施绛年而言,却是一个像哥哥一般的长辈,温和却无趣。 她欣赏对方的才气,却从未对戴望舒动过心思,面对他的诗、他的眼神、他的试探,女孩选择了回避,却也让戴望舒更加痛苦。 终于,他忍无可忍,直白地表白了,可回应他的却是沉默。 在之后的日子里,他情绪愈加激烈,不止一次在友人面前哀叹:“我把心掏给她看,她却连瞥都不愿意瞥。” 直到那日楼顶之事,他终将脆弱、热烈的情感演绎成了极端,以生死相逼。 施绛年终究还是被吓坏了,那年她才20岁,还不懂拒绝与拒绝后果的界限。 她答应了,条件却是:你必须出国深造,待你学成归来,再议婚事。 戴望舒欣然接受,他相信这是一场考验,只要他足够优秀、足够坚定,她终将被打动。 于是他远赴法国,主修文学与哲学,写下大量忧伤缠绵的诗篇,那些诗多半为她而写,字里行间,皆是沉溺和宠爱。 可这段情感,终究只是他一个人的执着,在他漂泊异国之时,施绛年却另有所恋。 这个消息在上海文坛传开之后,迅速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震惊、愤怒、失落、羞辱,一股脑袭来,他以为自己赌上了全部,得到的却是一场“背叛”。 当他归国,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再次与施绛年重逢。 他已不是当年那个青涩的诗人,眉眼间多了几分深沉。 但当他得知施绛年与他人有染的消息竟是真的,愤怒终究压过了理智,在众人面前,他一掌甩在了她的脸上。 施绛年没有哭,也没有辩解,只是低下头转身离开,那一巴掌,打碎了所有残存的情谊,也让戴望舒彻底明白,这场感情从未真正开始过。 之后的岁月里,戴望舒又遇到了穆丽娟,一个温婉聪慧的女子,他们结婚了,生活初时甜蜜。 他以为找到了真正的归宿,穆丽娟不是施绛年,不带伤疤的重来,或许可以让诗人安放自己漂泊的灵魂。 可戴望舒身上固有的“诗人毛病”却始终未改,他多疑、敏感、渴望控制。 在那年代,“大男子主义”如同空气,潜藏在日常细节中,他希望穆丽娟既要温柔贤惠,又要崇拜他、围着他转。 他无法容忍妻子有独立思想,甚至为她交际过多而大发雷霆。 最终,穆丽娟选择离开。任凭戴望舒如何挽留、悔恨,甚至以诗忏悔,都无济于事。 在感情上屡屡受挫的戴望舒,诗作愈加沉郁哀婉。 他的《雨巷》曾让千万人记住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而现实中的“丁香姑娘”们,却一个个离他远去。 1950年,戴望舒因病早逝,年仅46岁,世人悼念这位“忧郁的诗人”,却鲜有人知,他这一生,为爱所困,为情所伤。 他爱得炽热,也伤人至深,他写尽缠绵悱恻,却难守一段平静长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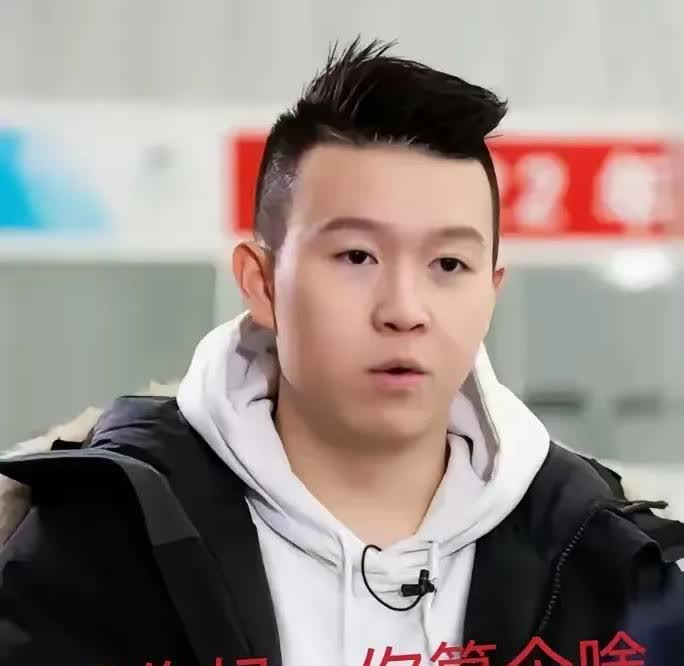
![天道酬勤莎莎老天会眷顾你的、你是最棒的勤劳🐝善良的女孩👧![赞][祈祷][比](http://image.uczzd.cn/13891807116617818839.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