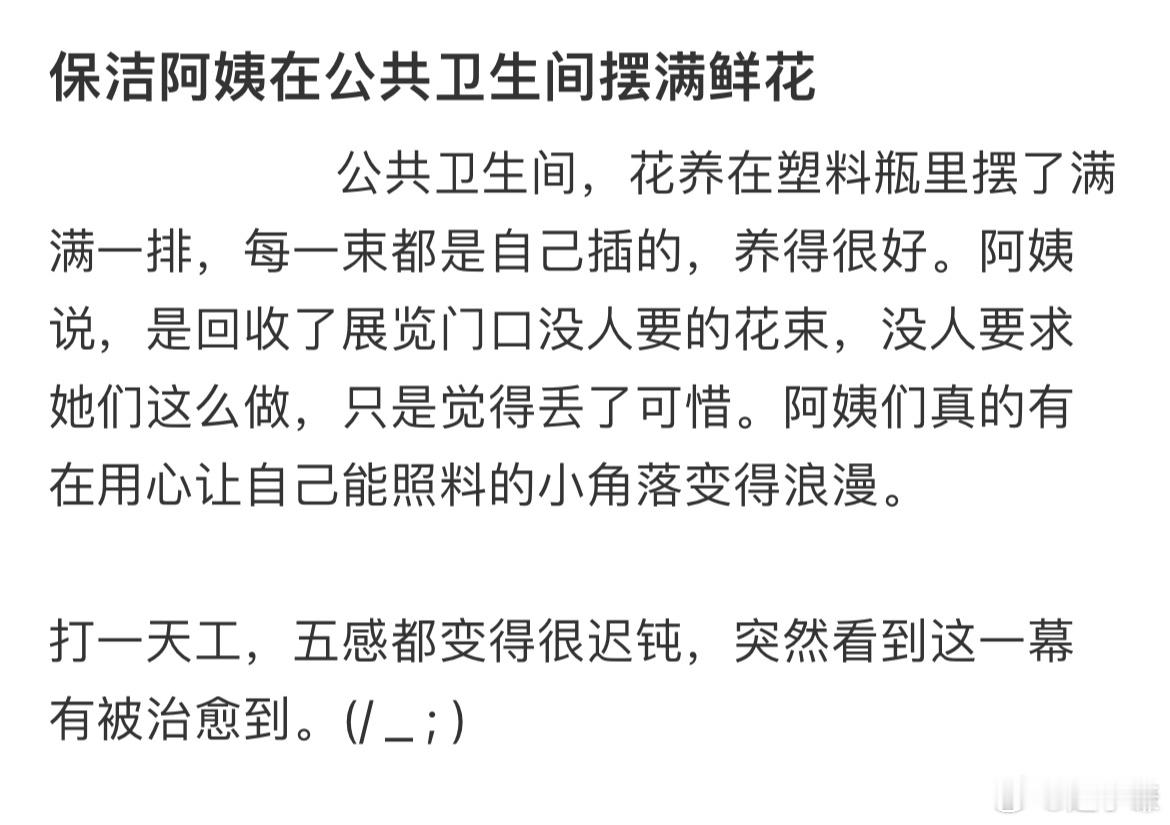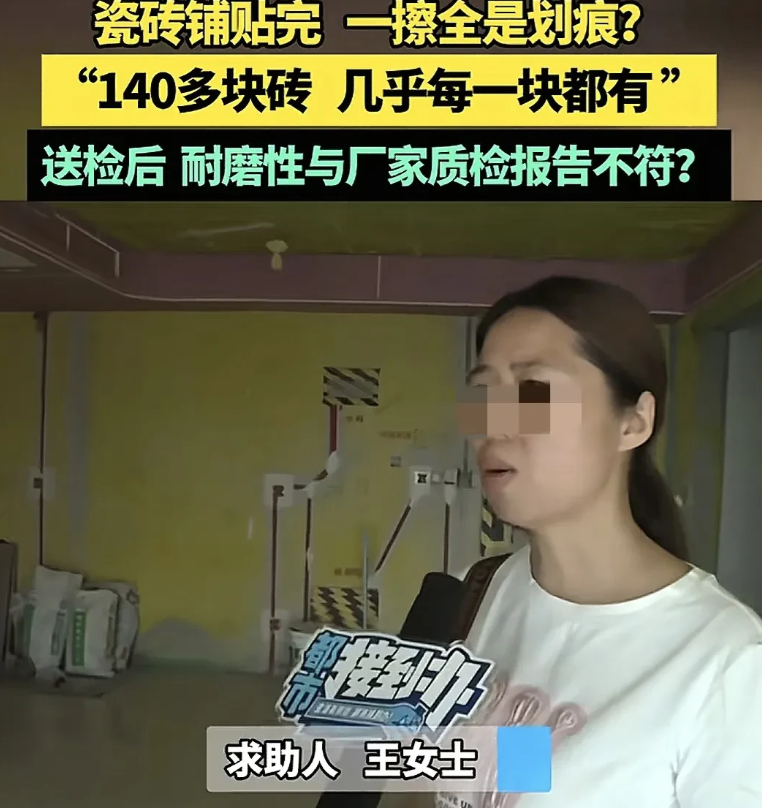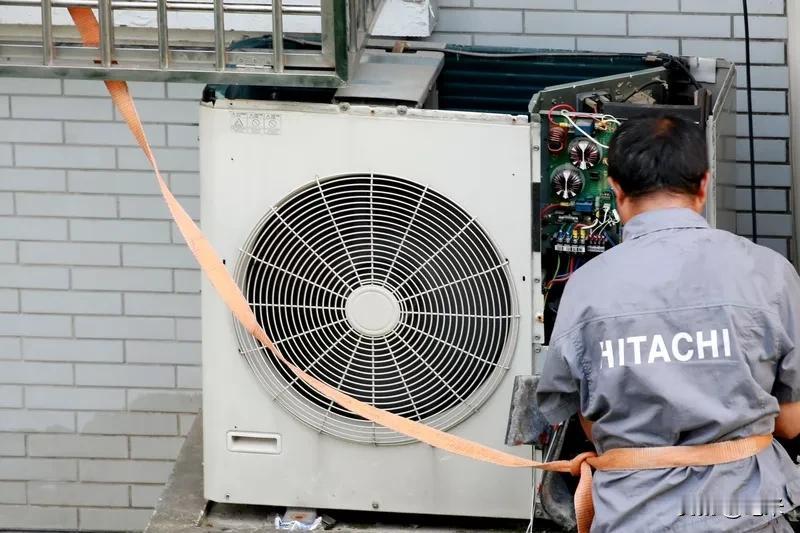腊月二十八的傍晚,我蹲在厨房择菜,听着客厅传来的嬉闹声,指甲深深掐进了白菜帮里。小姑家的表妹正举着我新买的平板电脑玩游戏,堂弟把瓜子壳吐得满地都是,二伯叼着烟在我刚擦干净的真皮沙发上烙下深色印记。 “阿宁啊,帮你堂弟把书包拿出来,明天还要上补习班呢。” 二婶斜倚在玄关换鞋凳上,涂着蔻丹的手指敲着堂弟鼓鼓囊囊的书包,“你这屋子宽敞,住两天怎么了?” 我攥着沾满菜汁的围裙,喉咙发紧。从五年前父母车祸去世后,每到年关,亲戚们就像候鸟般涌进我这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起初我还感激他们填补了冷清,后来才发现,所谓的 “照顾” 不过是把我家当成免费旅馆。 “表姐,这瓶红酒我带走了啊,我爸说超市卖两百多呢!” 表弟晃着酒柜里那瓶朋友送我的进口红酒,不等我回应就塞进了后备箱。我望着被翻得乱七八糟的酒柜,那些珍藏的杯子碎了两个,杯底还沾着可乐渍。 年夜饭的餐桌上,气氛诡异得像块冻住的猪油。我数着碗里的白米饭,听着亲戚们讨论新买的貂皮大衣和海外旅游计划。小姑突然把筷子往碗上一搁:“阿宁啊,你二伯单位发的购物卡用不完,你去帮着花了吧?年轻人会买东西。” “是啊,顺便给你堂弟买双限量版球鞋,听说现在小孩都流行这个。” 二婶补了一句,嘴角挂着意味深长的笑。 我握紧发烫的瓷碗,突然想起去年年夜饭,二伯说生意周转困难,我二话不说转了五万块;小姑说表妹要学钢琴,我又资助了三万块学费。这些钱,他们从未提过归还。 “以后过年别来我家吃饭了,” 我的声音像是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要么过年大家轮流请,要么不要喊我。” 饭桌上的空气瞬间凝固。二伯的酒杯重重砸在玻璃转盘上,发出刺耳的声响:“翅膀硬了?要不是我们,你早成孤儿了!” “孤儿?” 我猛地站起来,碰翻了手边的汤碗,滚烫的鸡汤在桌布上晕开深色痕迹,“这些年你们吃我的、住我的、用我的,什么时候把我当亲人?不过是把我当提款机!” 小姑涨红着脸指着我:“忘恩负义的东西!当年要不是我们...” “当年?当年你们争着要分我父母的遗产,要不是舅舅出面,这房子早被你们瓜分了!” 我浑身发抖,这些话在心里憋了太久太久,“我每个月还房贷、养车、付水电费,你们谁问过我难不难?” 客厅陷入死寂。堂弟偷偷把平板电脑塞进书包,表妹低头玩着指甲,二伯的烟在烟灰缸里积了长长的灰。我深吸一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沓借条:“这些钱,该还了。” 窗外的烟花突然炸开,映得满屋人影斑驳。我望着这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第一次觉得过年不再是团圆,而是一场精心编排的闹剧。或许,真正的亲情不该是索取与算计,而是互相尊重与体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