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二年,一个下雨的夜晚,北京紫禁城里,军机处的门悄悄开了,一封密折刚刚送进养心殿,太监不敢喘气,皇帝披着蟒袍亲自打开。 上面写的是山东巡抚密报,说有地方官私吞赈银,雍正没说一句话,朱笔一点:“即刻拿办。” 第二天,那个地方官被五花大绑,押往刑部,谁也不敢问一句,这年,全国密折送京四万多件,几乎每个文官每天都要写三次。 这套制度把所有人的眼睛、嘴巴、手脚,全都系在皇帝身上。 雍正开始当皇帝的时候,文官系统还想着怎么左右逢源,可没过两年,皇权像铁箍一样把这帮人死死箍住了。 他先动手的是军机处,原本国家的大事小情都要进内阁、走六部,大家议一议。 但他不耐烦这些流程,直接搞出个“军机房”,任命几个亲信,比如鄂尔泰、张廷玉,抄近道给他写建议。 他们一句话能改动全国的官制,六部的大员也只能点头照做。 制度上讲叫“简政提效”,实际上就是绕开整个文官班子,皇帝一句话能让一省巡抚掉脑袋。 有了军机处,他还不放心,雍正搞了一个密折制度,说白了,就是谁都能越过上司,直接给皇帝写信。 但这封信只能他看,他让地方的知府、知县,甚至驿站的驿丞都可以写。 大事小事,比如谁哪天早退、谁吃空饷、谁和商人勾结,密报,雍正看完,批上红字,锁进铁匣,亲自存档。 据故宫档案统计,雍正年间密折数量超过四十万,雍正每天最少看三百件,最多一次批了七百封。 他批奏折的地方在养心殿西暖阁,一个连太监都不能进的小屋,只有军机大臣进出过。 这地方2018年修复时还发现一个密折匣子,上面写着“钦命军机大臣收”。 这样一来,大臣们人人自危,有次江南闹灾,刘统勋照实上奏,说灾民饿死不少。 雍正朱笔划一句:“虚报灾情,杖责三十。”从此再没人敢讲坏消息。 雍正还特别强调:“无实据奏事者,杖责四十。”文官从此闭嘴,只管传话、办事,不敢出头。 乾隆继位后,更加注重对文官脑子的控制。 乾隆五年,他亲自规定,科举考试必须考四书五经,不能出题离经叛道,考八股文就像打算盘,每句都得对仗讲义理,谁要是加点现实批判的意思,马上拿下。 官员出身的来源基本就是进士,乾隆统计过,朝中有七成官员都靠八股出头,可真让他们升官的,不是写得好,而是密折写得勤。 到了文字狱最严的时候,随便一句诗词都能掉脑袋,胡中藻原本是个大学士,诗里写了“浊清”两个字,被人翻出来告了御状,说是影射朝廷。 乾隆二十年,他被下诏处死,还牵连六十三人,包括一位巡抚、一名知府和数位书院讲师。 有案底记载,清代1723年到1799年间,一共发生文字狱一百三十多起。 平均下来,一个文官活不过五十二岁,不是病死的,就是被办了。 可怕的是,文官虽多,日子却穷,一个七品知县,一年俸禄四十五两银子,换成今天的钱,也就两千块出头。 这点钱还不够他请门房、买纸笔,怎么办?朝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他们收“火耗”,就是每笔税银抽点“操作费”,这成了他们的灰色收入来源。 1850年的财政统计显示,八成以上官员年收入过万两,比他们本职工资高二百倍。 乾隆又搞了个“秋审”,说贪污百两就绞刑,可真按这个办,衙门能空一半人,实际执行里,这条律例像橡皮泥,能捏。 《大清律例》里写得清楚,但真判死的只占五个百分点,朝廷也知道问题大,但一层层的官员都靠“潜规则”活着,不敢真动。 1810年,有统计显示,一个省的按察使受贿金额平均三十万两银子,这个数据在《道光朝奏折汇编》里有记。 最开始,明朝官员还有点骨气,御史能“风闻言事”,听说啥都能进宫告,万历年间,一年就有一千二百件奏章进宫。 可到了清朝,风闻变成“风声鹤唳”,没人再敢多说。雍正说得明白,没证据就告人,就打你板子。 乾隆年间有件事最典型,和珅贪腐案,乾隆一手提拔他,把国库管得跟自家钱袋似的。 嘉庆帝一登基,马上动手审他,朝中那些文官,平时拍马的最勤,关键时刻一个个闭嘴。 连军机处都不敢吭声,和珅被查出抄家二十亿两,够当时全国两年的财政开支,但他在位期间,没人敢动他一个字,所有人都学会了装聋作哑。 这些东西今天还能看到,2018年故宫考古发现的实物里,有密折残片,上面还留着朱批:“此奏迂腐,着存档。”铁证如山。 养心殿西暖阁改造的时间也有记载,在1730年,专门为了让皇帝可以一个人看密折。 而文渊阁的防火墙厚达一米二,只为保护朱批奏折,不让它们泄漏出去。 这些制度、这些规矩,把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绑死在皇帝身上。 文官不能说真话,不能办实事,只能往上看、向下压。 一切靠皇上开口、点头、写红字,这就是清朝最稳也最冷的机器,直到它自己再也动不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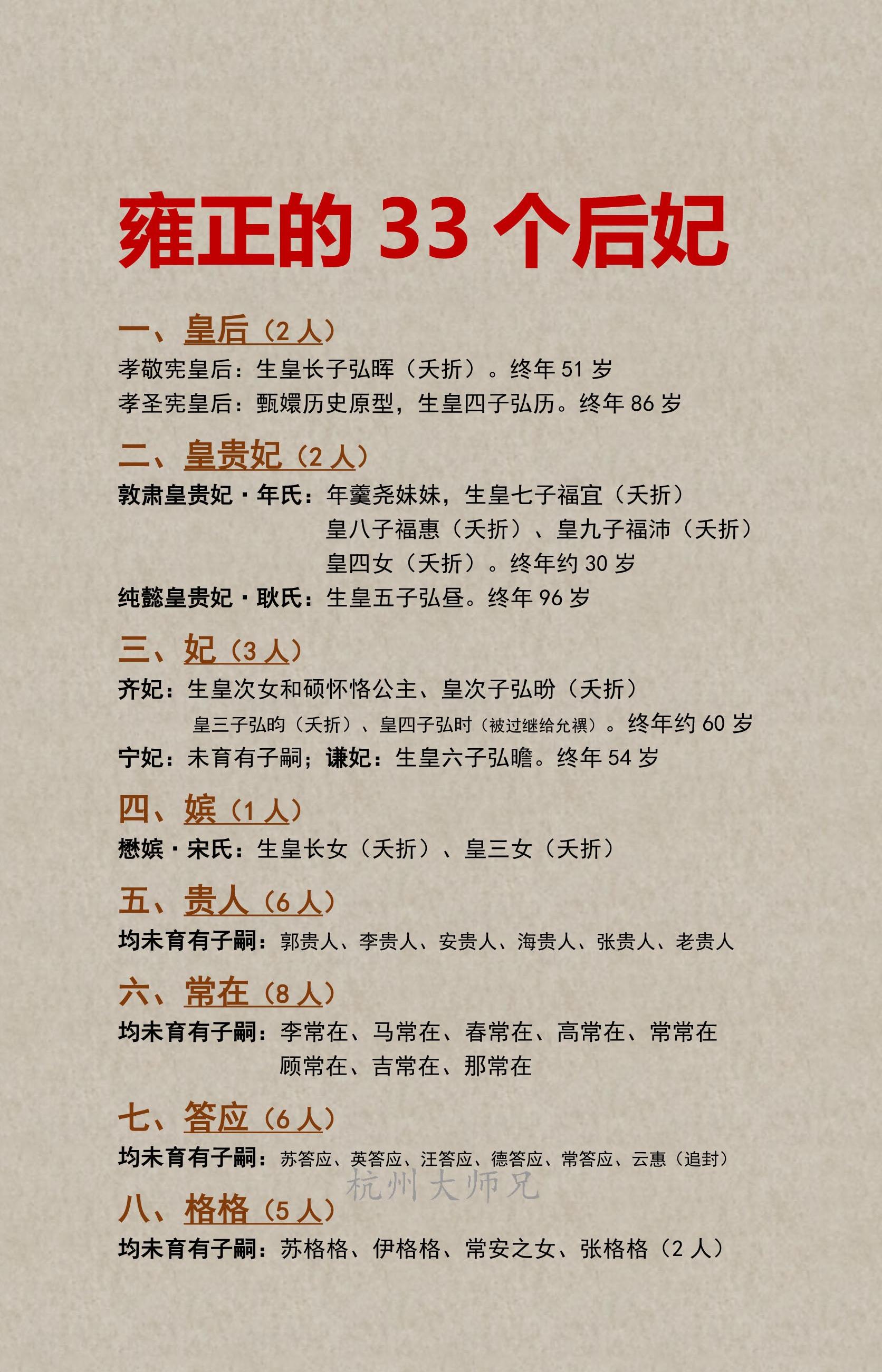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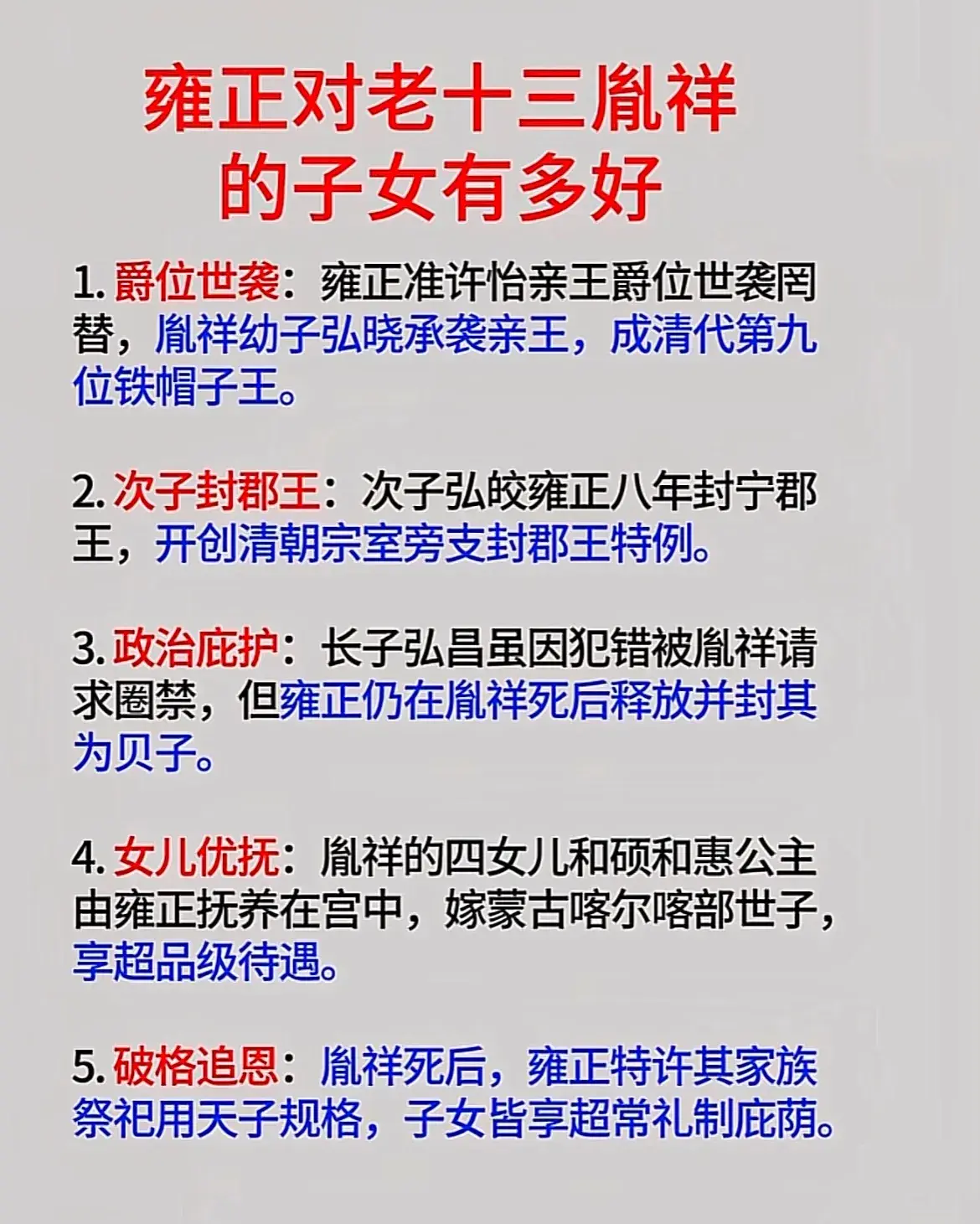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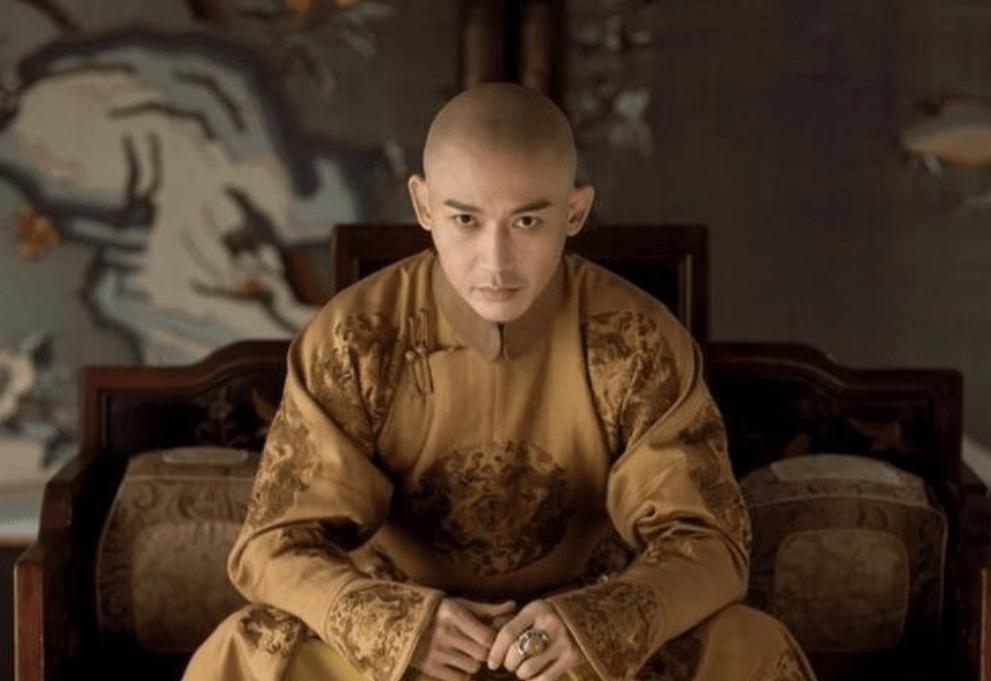


赵小胖
军机处是雍正八年设立,雍正二年有军机处?有点常识再来写历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