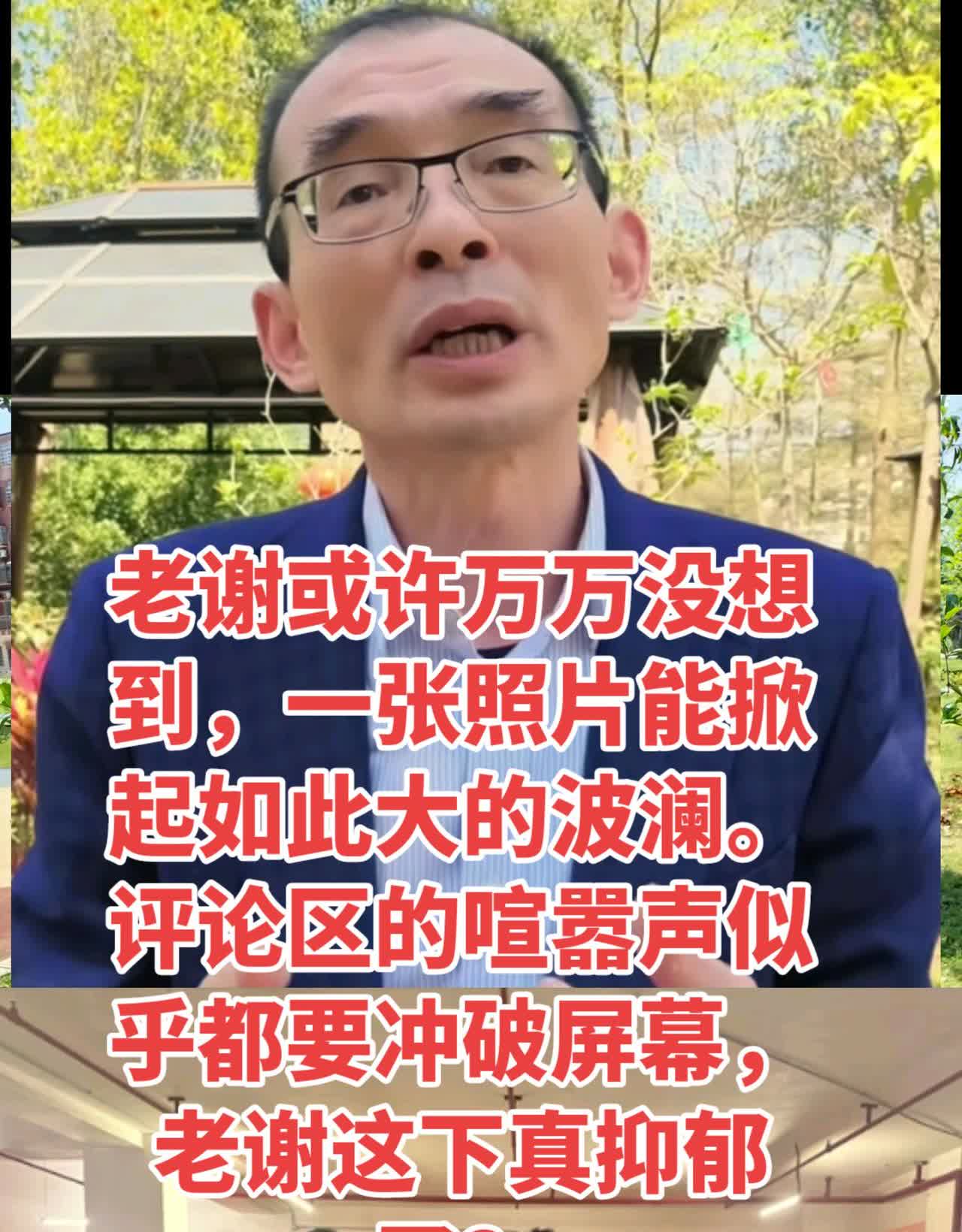1973年,女知青黄丽萍携农村丈夫回宁波父母家,一进门,丈夫看到墙上挂着的照片大吃一惊,问:“照片上的人是你父亲吗?” 得到妻子肯定的回答后,丈夫果断提出了离婚。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正上演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宁波城里长大的姑娘黄丽萍就是这股洪流中的一朵浪花,她原本可以在将军父亲的庇护下过着安稳日子,却偏偏选择背着行李卷儿去了北大荒。
黄丽萍刚到农场那会儿可真没少遭罪,东北的冬天冷得能冻掉人耳朵,夏天又有成群的蚊子追着咬。
城里姑娘细皮嫩肉的,没两天手上就磨出了血泡,胳膊晒得跟黑炭似的。
可这姑娘骨子里带着军人的倔劲儿,硬是咬着牙跟着老乡们学播种、学割麦,连最费腰的插秧活都抢着干。
农场里那些大娘大婶看着心疼,常往她兜里塞烤土豆,手把手教她纳鞋底。
在农场管账的秦升就是这个时候走进黄丽萍生活的,这小伙子长得敦实,说话带着东北人特有的敞亮劲儿。
别看他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农闲时候还爱捧着书本看。
两人在秋收时节的谷堆旁对上眼,一来二去就好上了。
那年月谈恋爱没现在这么多讲究,赶集时帮着挑担子,下雨天送把伞,就算是处对象了。
结婚那天特别简单,公社大院里摆了三桌杂粮饭。
黄丽萍穿着改小的碎花布衫,秦升套着浆洗得发白的中山装。
小两口的新房是土坯砌的,窗户纸糊了两层还是漏风。可俩人心里热乎啊,合计着要在这黑土地上扎下根,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变故发生在结婚第三年,黄丽萍带着丈夫回宁波探亲,刚迈进将军楼的门槛,秦升就盯着墙上挂的大幅军装照挪不开眼。
照片里那个挂满勋章的老军人,让这个庄稼汉头回知道自家媳妇儿是将军千金。
那天夜里秦升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清早蹲在弄堂口抽了半包烟,末了红着眼睛说要离婚。
黄丽萍急得直跺脚,她爹黄老将军倒是稳得住,老爷子把女婿叫到书房,指着满墙的作战地图说:"我当年也是放牛娃出身,如今这位置是拿命拼出来的,人活一世贵在踏实本分,你们小两口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
这话像盆热水浇化了秦升心里的冰疙瘩,他蹲在院子里抽完最后半支烟,起身把媳妇儿的行李重新捆结实了。
回到北大荒的小两口更卖命了,秦升把算盘珠子拨得更勤快,黄丽萍带着妇女队搞科学种田。
寒来暑往十几年,当初漏风的土坯房换成了砖瓦房,农场里添了拖拉机,粮仓堆得冒了尖。每到收获季节,金灿灿的麦浪能从山脚铺到天边。
后来农场搞承包制,夫妻俩带头包下五十垧地,秦升负责跑农机采购,黄丽萍琢磨着搞玉米大豆轮作。
赶上好年景,他们家粮囤子能比别人多出两成收成。
乡里乡亲都说这两口子是文武配,一个精打细算,一个敢闯敢干。
再后来孩子们都去城里念书了,老两口还是守着那片黑土地。每天天蒙蒙亮就扛着锄头下地,傍晚炊烟升起时扛着晚霞回家。
有次县里电视台来采访,问他们这么多年咋坚持下来的。
秦升搓着满是老茧的手憨笑:"庄稼人嘛,守着土地心里踏实。"黄丽萍在旁边补了句:"当年说要在这扎根,哪能半道撂挑子。"
如今北大荒早变成了北大仓,当年知青们住的地窝子都成了纪念馆。
黄丽萍和秦升的故事被写进农场发展史,照片挂在展览厅最显眼的位置。
两张饱经风霜的脸庞上,还能看出当年那个宁波姑娘和东北小伙的影子。
每到金秋时节,老两口还是会手牵手去田埂上转悠,看着收割机在麦浪里穿梭,就像看着自家孩子似的满眼欢喜。
要说这日子过得可真快,转眼青丝变白发。可有些东西倒是没变——秦升还是习惯把最好吃的菜往媳妇碗里夹,黄丽萍照样会在老伴算账时递上老花镜。
农场里年轻人都说,看他们二老就知道啥叫相濡以沫。这话传到老两口耳朵里,秦升嘿嘿一乐:"啥沫不沫的,过日子不就是你搀我、我扶你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