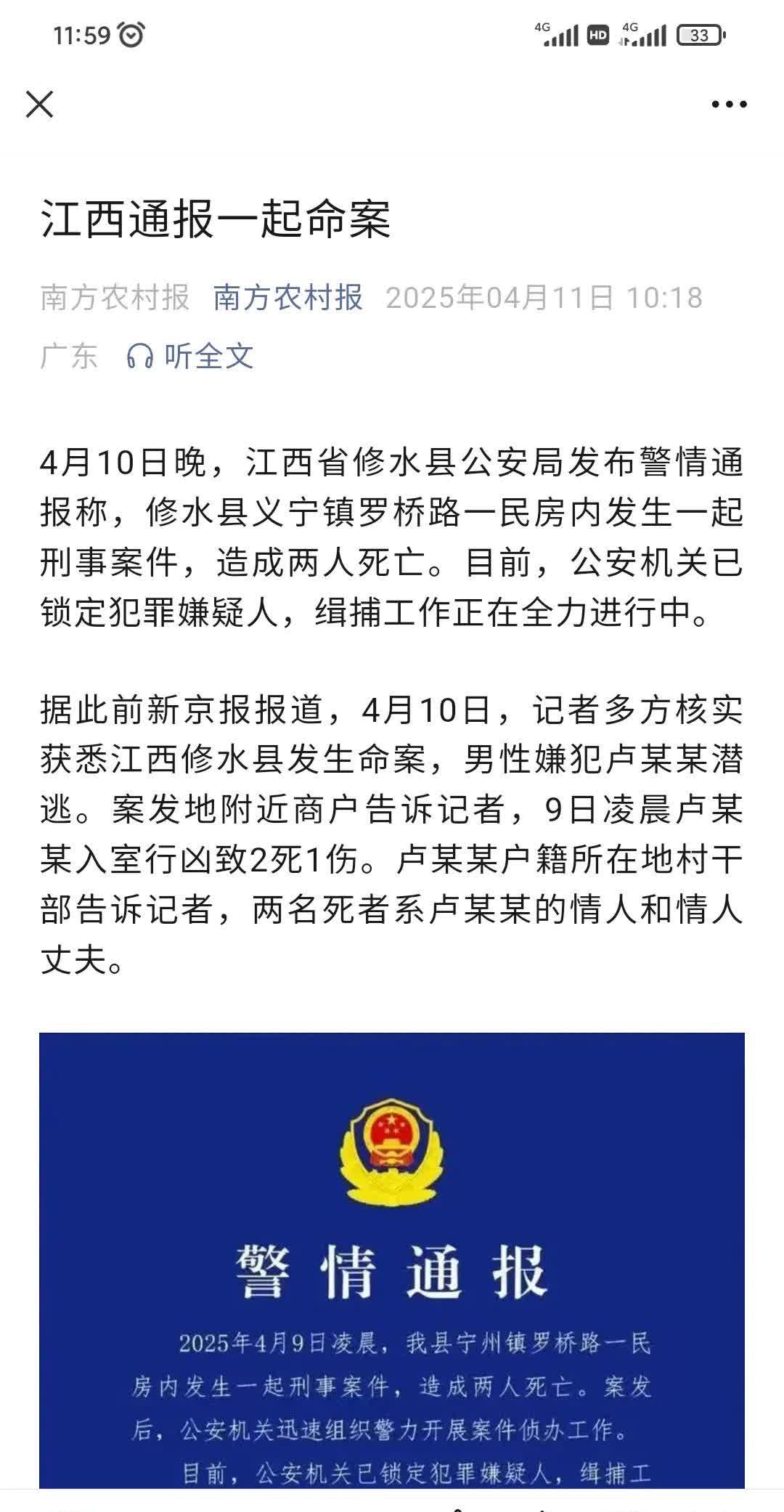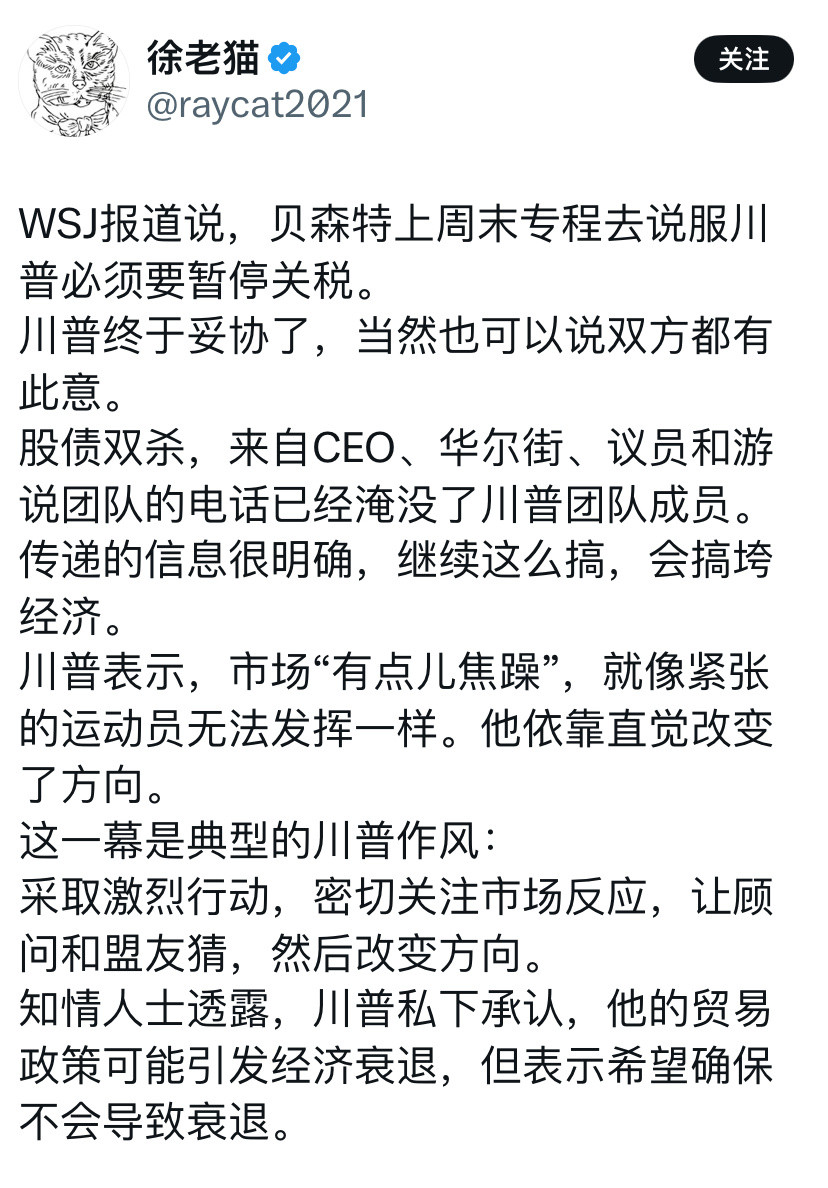因为卫氏触碰了汉武帝的底线威胁皇权。
卫青死的时候,长安的人心才真乱了。这个出身平民的外戚,靠着一杆长枪,从宫门骑进朝堂,从侍卫做到大将军。
七次出征匈奴,次次大胜,手下二十四个校尉,全封列侯。
北军、羽林卫,全是他旧部,连未央宫的侍卫队长,都是他亲自挑的心腹。
一个人死了,却等于整个汉朝的七成精锐军队,失了主心骨,汉武帝站在甘泉宫里,听完报,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手边一封奏章撕了。
那奏章,是要封卫不疑进宫做太子少傅的。
卫家太强了,长子卫伉,承袭长平侯,娶的是公主;次子卫不疑、幼子卫登也都封侯。
外甥公孙敬声虽然丑闻缠身,但其父公孙贺,是堂堂丞相。卫氏一门,统军的、理政的、管后宫的、守城门的,一个不少。
更要命的是卫氏人多还讲义气。门生、部将、姻亲、同乡,一封信就能动一营兵。朝堂上有人说:“卫氏今日,不逊当年吕氏。”
这话传到汉武帝耳朵里,夜里他没睡,召人查未央宫守卫的调动图。
怕了,真怕了,不是怕卫青生前造反,他知道这人最会装谦虚。问题在于他死了,卫家没散。
皇权空了一个位子,军权却还攥在别人手里。
武帝年轻时吃过一次亏。吕后称制、吕氏外戚当道,几乎架空整个刘家天子。
后来周勃起兵平诸吕,那场血战让他懂了权力的结构,外戚、军功、文臣,三股力量,一个出头,就有人要死。
卫氏不是蠢,而是太稳,卫子夫从歌女做到皇后,三十年恩宠不衰。
卫家人不张扬、不骄横,连对太子刘据都以礼相待。可正是这份“懂事”,让汉武帝警觉。
一个不会惹事的外戚,才最可怕,时间到了征和元年,朝里出事了。
先是太子宾客与宦官江充在街上争道,一言不合拔刀,再是有人举报卫伉私藏甲胄,说他常与军中旧将密谋,想为太子预立“兵变预案”。
汉武帝听完,脸都黑了,前脚江充被人打了,后脚他就翻出十年前的一道旧案“巫蛊之祸”。
他开始查“宫中施咒”,让江充去主办,结果不出意料。
太子宫中“挖”出桐木小人,上书“祸延天子”。这玩意是真是假不重要,重要的是,借口有了。
太子急了,求母卫子夫,卫子夫更急,命人开武库,调兵护宫。
卫伉一听,带北军部将直奔东宫。全长安都看见了:太子调兵,卫氏出兵。不叫谋反,叫什么?
这时候,汉武帝没说话,他看着奏章,看着地图,连夜召集几名老将,密令调兵围城。不是要抓人,而是要动刀。
卫子夫明白了,那天晚上,她没说什么,只叫人给太子送了套旧袍子,是他小时候穿的。
然后服毒自尽,死在宫中,连遗言都没有。
太子刘据起兵失败,自杀未遂,被乱军砍死于长安城外的荒庙。卫伉被当街抓捕,腰斩,曝尸三日。
一门五万余人,被流放、处死、株连,三月之内,卫家从天子亲族,变成了反贼余孽。
江充笑了三天,第四天被人暗杀。刺客没人查,皇帝也不想查。他知道,这种人活太久,不吉利。
汉武帝终于能安睡了,卫家没有了,太子也没有了,军中没人敢大声说话,宫里也没人敢再怀孕。
甘泉宫冷得很,他每天只看两样东西星象图和皇储名册。
最后那份诏书,是他自己写的。字写得不稳,但句句狠:
“军吏敢窥神器者,虽亲必戮。”这不是给太子的,是给满朝文武的警告,谁敢伸手,手就没了。
卫青活着的时候,还能遮点风,死了之后,整个卫氏,被钉死在汉武帝“权力偏执”的棺盖上。
功高盖主,不是句空话,汉初的周勃、灌婴,后来怎么了?要么淡出权力,要么死得窝囊。
汉武帝看得太清,他年轻时靠文景积累的家底征战天下,到老了,只想收权收人收心,开始疏远霍去病,后者年纪轻轻却死得早,有人说是病死,有人说是被猜忌,不让活。
霍光能活下来,靠的是无血缘、讲规矩、识时务。他不像卫家那样,和太子、和皇后、和军中,都绑在一块儿。
霍光是替汉武帝留给汉昭帝的“保险”。
卫青死后,卫氏一门成了帝王心术的祭品,汉武帝用三十年把一个外戚捧上天,再用三个月把他们打进地里。
这不只是忌惮,是制度,是铁律,太近,必亡,太高,必折,人死如草芥,权力如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