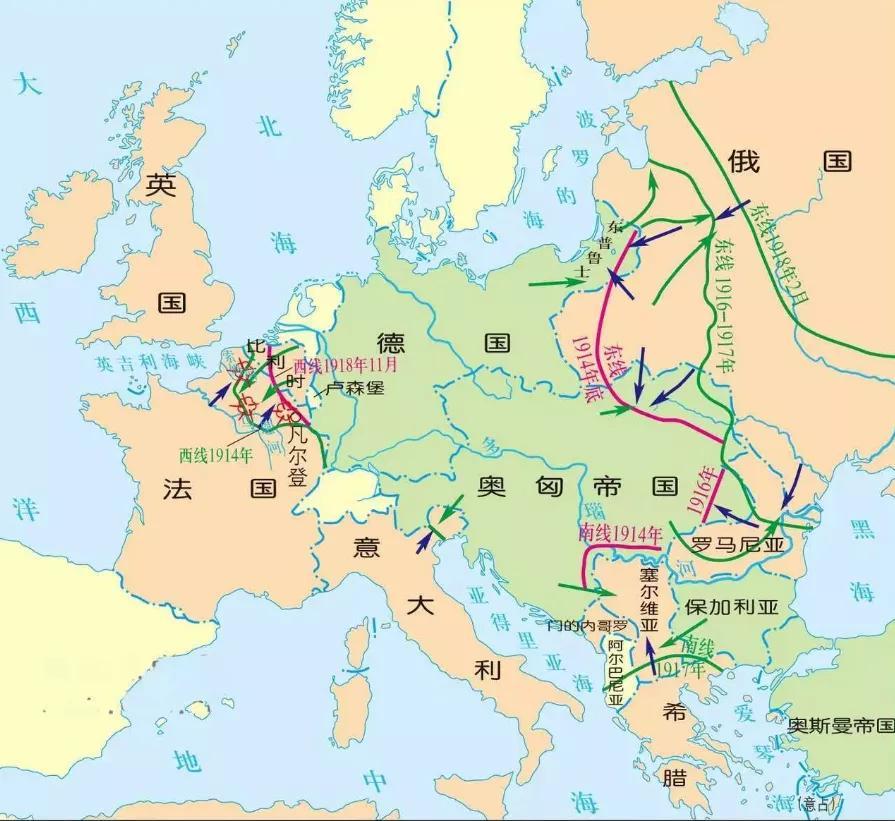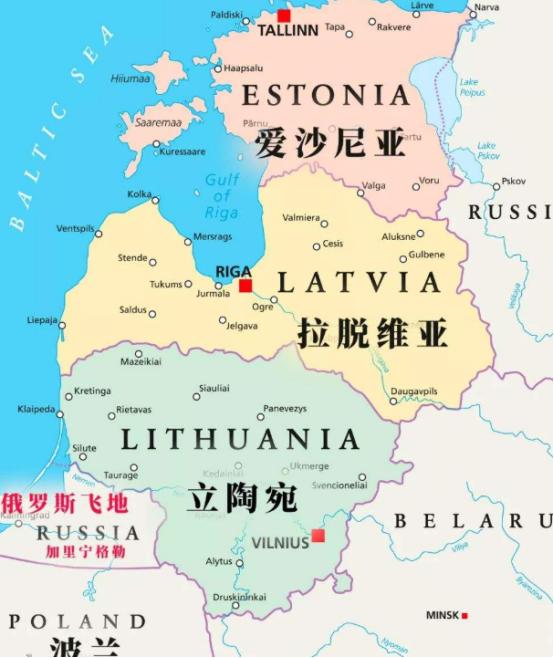这是二战时期,乌克兰最著名的“李森科十兄弟”,这10个兄弟全都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与德军浴血奋战,最后10兄弟竟然全都奇迹般活了下来,回到母亲的身边。 乌克兰南部,村子名叫Brovacaha,地太薄,人太多,地里刨食,刨不出命。 1933年,苏联还没从大饥荒里缓过来,男人死了,留下十五个孩子。 十个儿子,五个女儿,排开一个个跟树干似的,母亲叶夫多基亚站在风口上,没掉过一滴泪,她说,哭没用,活下来才是本事。 八年后,1941年,德国人推着铁皮怪兽碾过来。 东线战场轰地一声拉开,乌克兰成了绞肉机的前门,苏军强制征兵,十个儿子,一个不剩,全数上战场。 全村人都等着看这家人怎么崩塌。 可她没躲没藏。头天晚上坐在炕上,点着一盏油灯,一针一线给每个儿子缝军装,第二天一早送到村头,像送去赶集一样利索。 “不是你上,就是别人家上,保命不能靠苟着,得靠挡在前面。” 没一个儿子回头,她也没追,只把那根拐杖杵得死死的。 炸弹、机枪、集中营、战壕、冻土、劳改营,一个个像钉子钉进这十兄弟的命里,想死太容易,想活得等机会,赌命。 伊万更绝,被德军抓走,扔进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逃出来后又偷渡到罗马尼亚前线继续打。 问他图啥?他说:图家还在,娘还等。 最狠的是米哈伊尔和费奥多西,一个胸口挨弹,一个腿被炸飞,居然在雅西战壕里重逢。 费奥多西躺在烂泥堆里看见哥哥,没哭,骂了一句:“你个王八羔子,怎么也来这儿送死。” 瓦西里当上了中尉,三次挂彩,硬是爬回阵地,红星勋章挂在胸前,半边身体都麻了。 斯捷潘最晚回来,德国人投降他还没赶上,转战东北抗日,扛到最后一枪才卸甲。 那年他从哈尔滨回乌克兰,火车慢得像老牛拖车,但没人催,全车都在听他讲“日本兵窝在碉堡里怎么不敢冒头”。 这十兄弟,分散得像散弹枪打出去的钢珠,战线长达八千公里。 有人东线扛枪,有人蹲罗马尼亚壕沟,有人在德国工厂里刷马桶,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谁都没死。 这是运气吗?不是,是拆散,是硬扛。 一次能让一个人死,十次让十个人散,就可能全活下来。 兄弟之间不是哭嚎着思念,而是用命护命,那年战壕里重逢,费奥多西扛着断腿,也拉着米哈伊尔走,像拖着家一样。 而村口那个女人,还是每天站那儿,风雪再大也不回屋,她不信命,只信脚下站得稳,孩子就能活。 战争熬过去了,1946年,苏联政府送来一个红绶带和一块奖章,叫“英雄母亲”。 她没哭,接过勋章扔进了锅里熬汤,“铁的,总比没饭强”。 村子后山立了一尊铜像,十棵白杨笔直站在后面。那不是纪念,是数人头。 瓦西里没等到揭幕,早走一步,弟兄们在他墓前点了根烟,“你快点儿,咱还差你一个人喝酒。” 苏联卫国战争打了四年,死了1260万军人,平均每三个参战青年,死一个,这十个能活下来,是整场战争最野的一张牌。 可这故事不是用来煽情的。那时候战死的人没有名字,只剩编号和铁盒。 母亲站在风雪里不动,是因为怕动了,魂就不认门。 媒体把她捧上了神坛,讲“母爱伟大”“民族血性”,可没人问她一声愿不愿意让十个儿子去送命。 她没得选,国家要,命就得上。 而她,咬牙把每一个儿子送出去,再一点一点把他们等回来。 一边等,一边种地、喂猪、熬粥、补衣,手上开裂流脓都不皱眉。 1984年,乌克兰重新修了她的雕像,比之前高一倍,白杨树更粗更壮,可那年,苏联的风已经有点不对劲,油水短缺,兵役延期,战场上没人愿意再打命。 再没有十兄弟,也没人愿意再等一个母亲。 现在讲这个故事,不是为了喊口号,俄乌又开战了,坦克轧着旧路碾过村庄,和当年德军走的差不多。 一个国家变了名字,但母亲还在送儿子上前线,只不过不是十个,是一个个独生子,是不想打却逃不掉的兵。 有人问叶夫多基亚活着是不是后悔? 没人能答她的心思。可有人记得,她最后一次在村口站着,看的是太阳,不是路。 有些伤口不结痂,是因为风雪还在刮。 参考资料: 李娜:《苏联英雄母亲制度研究——以叶夫多基亚一家为中心》,《现代历史视野》,2021年第4期,第45-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