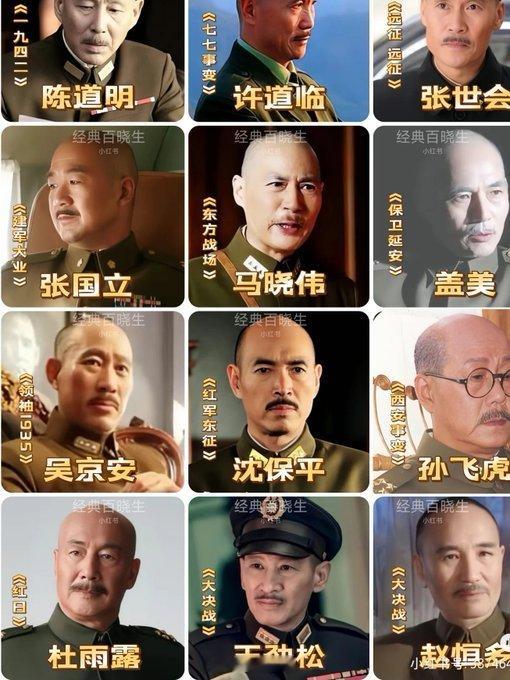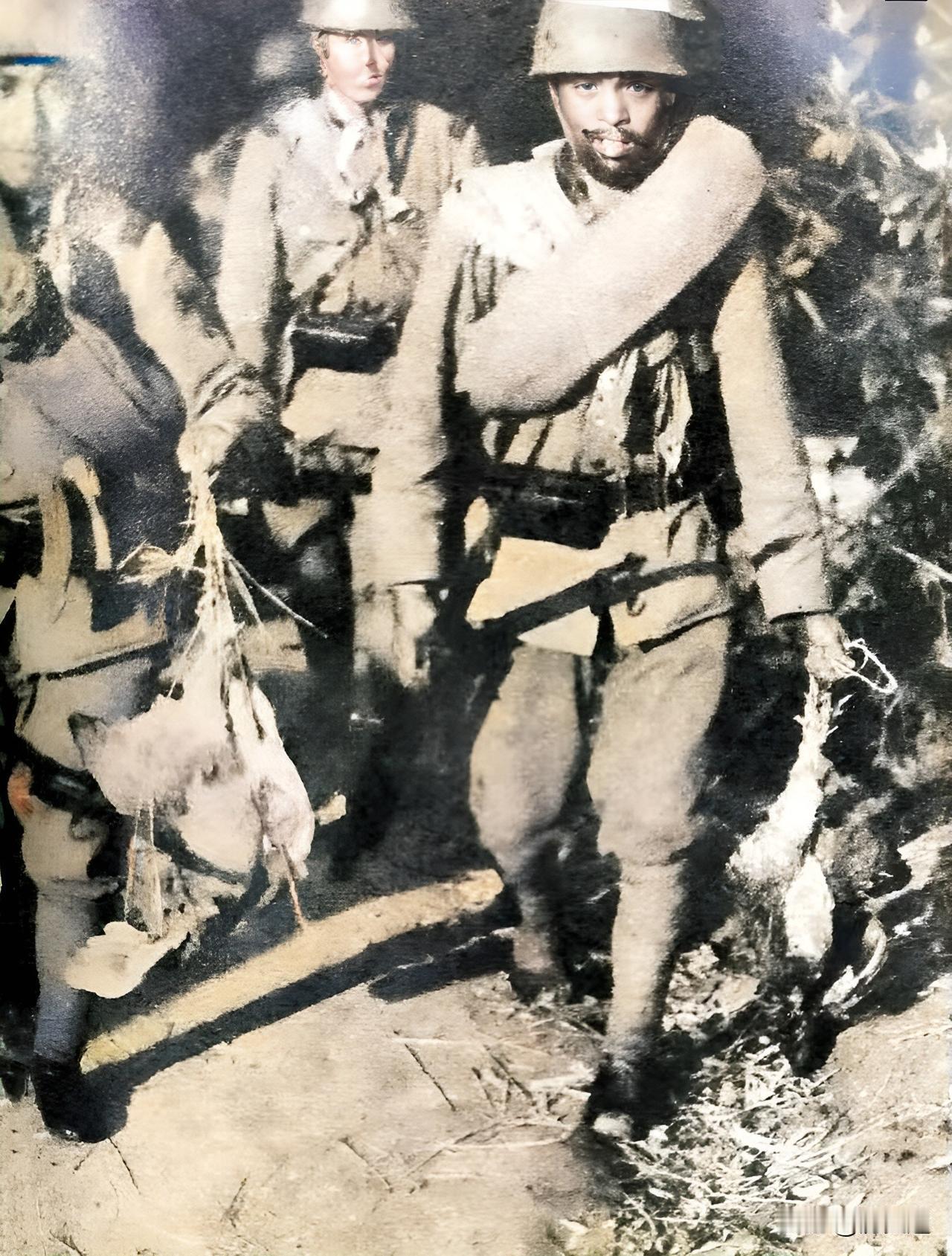1940年,重庆军统监狱里,戴笠声嘶力竭地喊着:“继续打!打到她开口为止!”,他面前是一个双手被反铐在铁架上的女孩。女孩全身血肉模糊,但目光坚毅,不发一声,只有此起彼伏的鞭打声在屋里回荡…… 戴笠原名戴雨农,早年因落榜黄埔军校,第二次报考时改用“戴笠”作为报名姓名。关于这一名字的来历,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解释源自算命师的建议,认为他命格中五行缺水,宜用带“水”意的字补救,而“笠”为雨具,意含水意;另一种说法则与他当时参加考试的两位好友有关。为了纪念徐亮、王孔安两人,他引用《车笠交》中的典故,“君乘车,我戴笠”,表达朋友间不以贵贱论交的情义。 1927年国民党发动清党时,戴笠协助揭发二十余名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共产党员同学,引起蒋中正注意,此后被纳入情报系统,开始长期从事特务工作。1928年起,他便协助蒋介石收集政治与军事情报。1930年进入国民政府“调查通讯小组”,参与核心行动。 两年后,军事委员会设立特务情报组,由戴笠主导。同年他受命筹建“力行社”和“中华复兴社”,两个组织均为秘密情报与行动机构。戴笠担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建立起与中统局平行但独立运作的特务网络,扩大情报体系的控制范围。 在此期间,他通过组织体系不断加强对军队、政府和社会各层级的渗透,逐步建立起覆盖全国的情报系统。他以复兴社为基础,吸纳忠于党国的青年分子,在各地设点布局,形成对政敌、异见分子和潜在反对势力的监控网。 1938年,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为统一和规范国民党的特务系统提供了制度平台。戴笠被任命为副局长,实则全面负责局内工作。自此,军统成为国民党控制情报、反间谍及执行特殊任务的中枢机构。该局不仅负责对外刺探情报、打击中共地下组织,还处理涉及国民党内部政治斗争的敏感事务。 1940年的重庆,一座阴森的军统监狱里,正上演着一幕惨绝人寰的拷打。戴笠厉声喝道:"继续打!打到她招供为止!"面前的铁架上,一个双手反铐的女孩浑身鲜血淋漓,遍体鳞伤,却始终不发一语。女孩目光如炬,倔强地直视前方。皮鞭的抽打声此起彼伏,在囚室里回荡,可她宁死不屈,誓与敌人斗争到底。 这位视死如归的女孩,正是轰动一时的"红色电台案"主角——年仅24岁的中共地下党员张露萍。回想她的革命生涯,短暂却如此闪耀。早在1939年,尚是少女的她便接受了一项秘密任务:化名"张露萍",打入敌人内部,与张蔚林一起收集情报。在那段如履薄冰的日子里,他们冒着随时被敌人识破的危险,默默坚持着地下工作,将一条条宝贵的情报传递给党组织。 张露萍机警而沉着,但战友张蔚林却因一时疏忽被捕。原来,他的电台发报机出了故障,被诬陷为蓄意破坏。惊慌之下,他仓皇逃离,不料被戴笠抓住把柄。张蔚林宿舍里的一本记事簿,详细记录了军统电台和地下党员的信息,落入戴笠之手。 当戴笠翻开那血红的记事簿时,他阴鸷的双眼里闪过一丝惊愕,随即被疯狂的兴奋取代。他知道,自己捏住了共产党的致命弱点,他将要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就这样,戴笠下令在全城搜捕张露萍等人。而远在成都老家的张露萍,尚不知大难将至。 戴笠在组织和建设军统时,注重将传统忠义观念与近代政治理念相结合。他不仅引入孙中山提出的革命信条,还在军统内部推行一种特殊的文化秩序。他将自己比作军统的“家长”,把局员看作“家人”,以“仁义”手段维系特务系统的稳定。例如,在部属牺牲后,他会资助对方家庭,承担丧葬费用、抚养孤儿,使军统在制度以外形成一种半家族式的组织纽带。 在日常工作中,他以身作则参与培训。无论工作多忙,每一批军统训练班他都亲自担任班主任,像蒋介石对待黄埔军校一样强调思想和纪律的统一。他经常向特工灌输“牺牲精神”,要求他们在面对生死关头要以国家利益为先,甘于无名无利地完成任务。 对已产生分歧的结拜兄弟王亚樵,他采取强硬手段。在掌握情报之后,他利用王亚樵部下的妻子安排约见,设伏并将其击毙。而对另一位仍效忠蒋中正的兄弟胡宗南,则采取截然不同方式。他安排叶霞娣出国深造,回国后再将其推荐至大学任教,有意使其成为胡宗南理想中的配偶,以此稳固彼此关系。 在戴笠看来,个人的荣辱并不重要。他在重庆军统局所在的山坡上立下一块无字碑,要求部属“清除私念,甘做无名英雄”,强调军统成员是领袖的工具,必须在默默中完成使命。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戴笠对前景有明确判断。 抗战期间,军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沈醉曾回忆,战争期间军统牺牲者达一万八千余人,而当时全系统登记人员仅约四万五千人,几乎每两个成员中就有一人阵亡。在情报战中,军统也展开过多起有影响的行动。1940年,高月保大佐在华北活动时被刺杀,成为军统暗杀行动的重要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