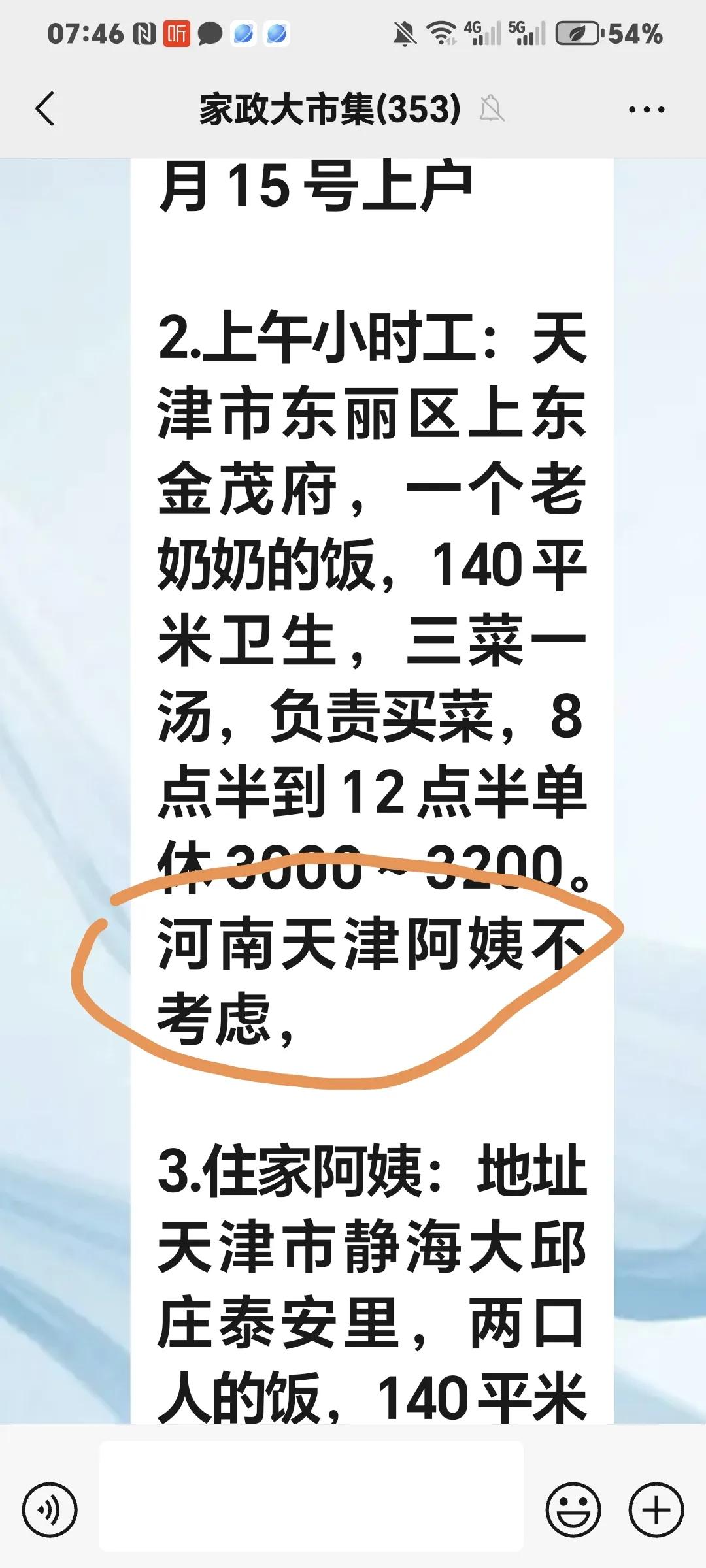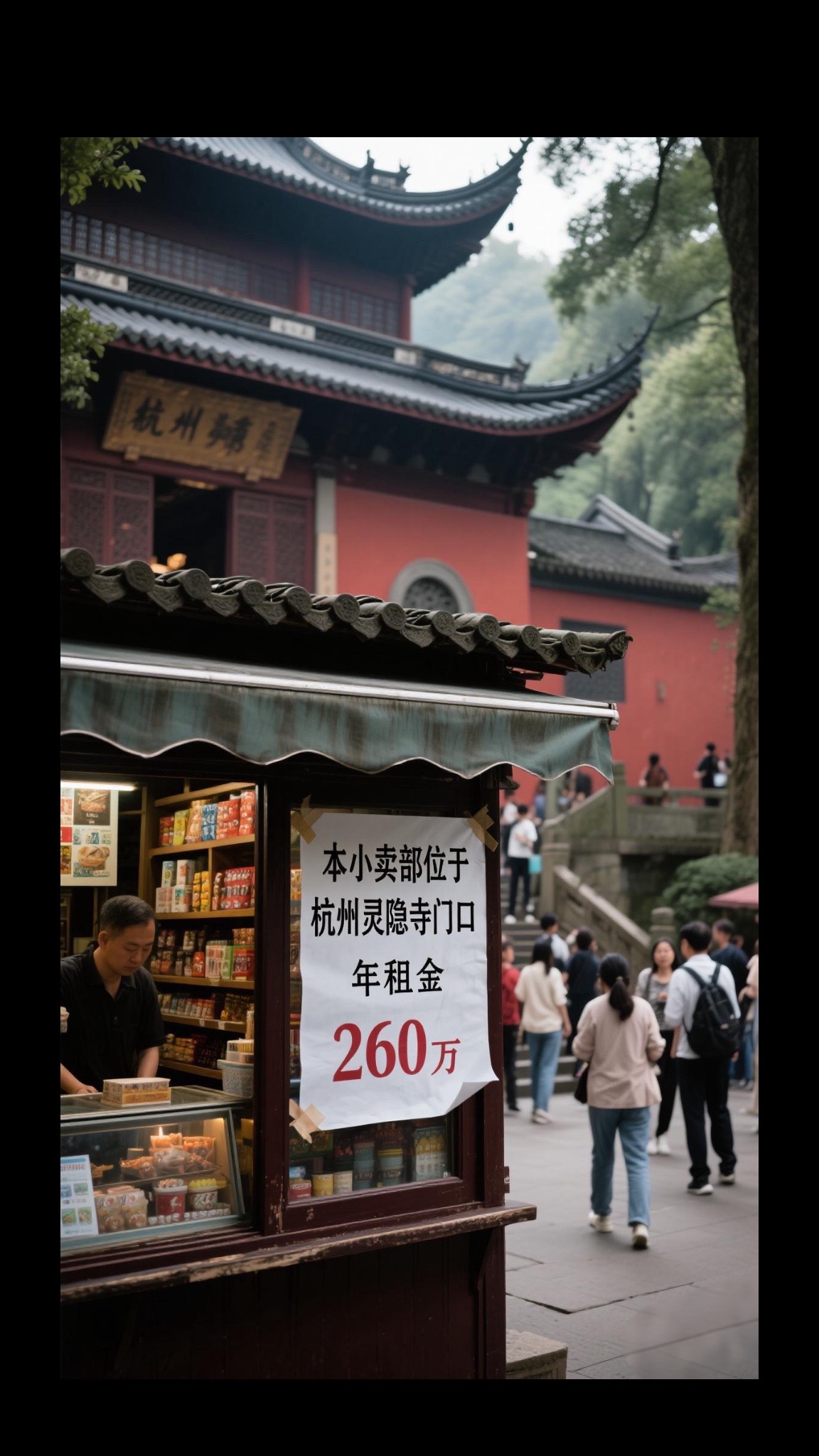1879年,杭州知府谭钟麟午睡时,梦见一位白须老者,笑呵呵地说:“恭喜大人,您将得一贵子,名‘何文安’,日后定是栋梁之才!”谭钟麟猛地惊醒,额头冒汗,喃喃自语:“何文安?莫非是天意?”他推开窗,望向后院,一个身影正在井边浣衣,低垂的发髻在风中微微晃动——那是李氏,一个卑微的丫鬟。 1879年的杭州,寒风刺骨。西湖畔的知府宅邸雕梁画栋,后院却阴冷潮湿。寅时刚过,天还未亮,李氏便拖着疲惫的身子,挑起木桶,走向井边。她的双手被冰水泡得发白,指缝裂开细细的血口,低垂的发髻在风中微微颤抖。身为通房丫头,她每日清晨洗衣、烧水,伺候正室夫人陈氏,稍有差池,便是劈头盖脸的责骂。 那天中午,谭钟麟推开窗,目光无意间落在李氏身上。白须老者的梦境犹在耳边,他心头一震:“莫非真是天意?”李氏清秀的面容和卑微的身份形成鲜明对比,谭钟麟一时心动,收她为妾。然而,封建礼教的铁幕下,妾室的命运远非想象中简单。 李氏怀孕的消息传出,陈氏怒不可遏,茶碗摔得粉碎,斥道:“贱婢也配生谭家骨血?”李氏跪在堂前,咬紧牙关,护着尚未成形的胎儿,谭钟麟碍于仕途,不愿多管。 1880年,李氏在后院偏房里挣扎了两天两夜,稳婆急得满头大汗,喊道:“再不使劲,孩子就保不住了!”李氏咬破嘴唇,拼尽全力,孩子的啼哭终于划破夜空。谭钟麟听到动静,推门而入,看到襁褓中的婴儿,眼神复杂。并为孩子取名“延闿”,字“祖安”,暗合“何文安”的预兆。 李氏却没时间沉浸在喜悦中。身为妾室,她连坐月子的资格都没有,产后第三天便被逼着站立伺候陈氏用餐。陈氏冷笑:“生了个庶子,也想翻身?”李氏低头不语,眼泪滴在粗布衣襟上。她知道,自己的希望全寄托在这个小小的生命上。 谭延闿从小就聪明伶俐,但“庶子”的身份如影随形。族中子弟嬉笑时,总有人指着他低语:“瞧,那就是通房丫头生的。”李氏心如刀割,却从不抱怨。她拉着延闿的小手,柔声说:“孩子,唯有读书,才能争得尊重。”五岁的延闿似懂非懂,点点头,从此埋头书卷,连玩耍都拒绝。 光阴似箭,谭延闿13岁中秀才,名震乡里。1898年,24岁的他赴京赶考,科场之上,笔走龙蛇,一举夺得会试第一名——会元!湖南200余年未出会元,消息传回,街头巷尾炸开了锅。谭钟麟捻须大笑,设宴款待宾客,唯独李氏站在角落,悄悄拭泪。那一刻,她终于被允许坐下,与正室同桌吃饭。饭菜咽下时,泪水却怎么也止不住。 李氏第一次感受到“母凭子贵”的滋味,但她仍保持谦卑,每日向陈氏问安,低眉顺眼。谭延闿看在眼里,暗下决心:“母亲的苦,不能白受。”他日后入仕,历任湖南省长、国民政府要员,被誉为“民国第一完人”,却始终坚持一夫一妻,拒绝续弦,甚至婉拒孙中山撮合的宋美龄,只因他不愿让任何女子重蹈母亲的覆辙。 1916年,李氏病逝,享年58岁。谭延闿从南京赶回杭州,亲自为母亲操办丧事。然而,族老却拦住灵柩,冷冷道:“妾室不得走正门,这是规矩!”谭延闿怒火中烧,回忆起母亲井边浣衣的背影、站立伺候的屈辱,他再也忍不了。 他猛地掀开棺盖,躺进去,嘶吼:“我谭延闿今日已死,抬我出殡!”族老们惊呆了,围观的百姓议论纷纷。最终,迫于压力,灵柩从正门抬出,李氏的灵魂终于以尊严的方式告别尘世。 那一刻,谭延闿泪流满面。他想起幼时问母亲:“为何我们不能同桌吃饭?”李氏含泪回答:“这是规矩。”如今,他用自己的方式,打破了这冰冷的“规矩”,为母亲争回了迟来的尊重。 白须老者的梦境,究竟是天意还是巧合?没人说得清。但李氏用一生的隐忍,换来了谭延闿的崛起;谭延闿用一生的奋斗,为母亲赢得了尊严。从井边浣衣到正门出殡,这对母子的故事,像一盏微弱却顽强的灯火,照亮了晚清的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