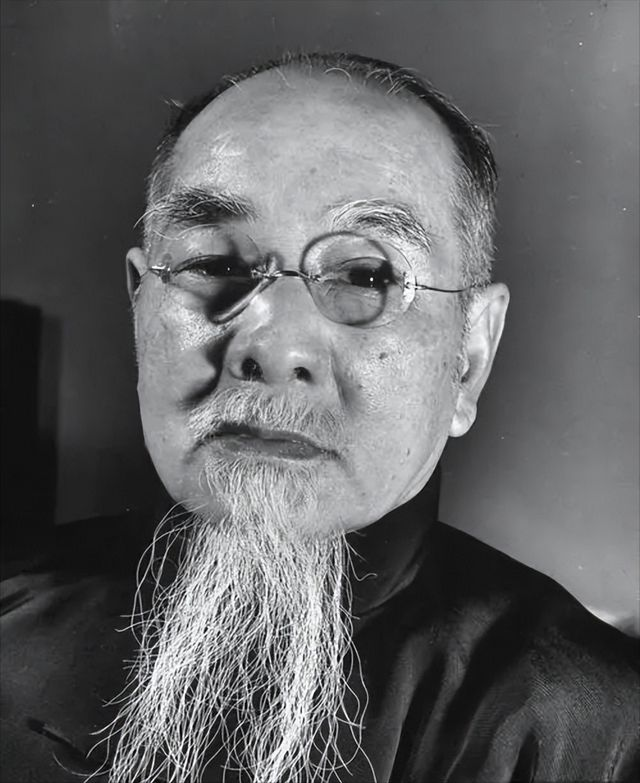1923年,戴笠在上海流浪,吃住在表弟张冠夫家里。张冠夫是商务印刷馆的职员,他和妻子王秋莲在小北门租了间小阁楼。夜里,张冠夫和妻子睡在床上,戴笠就睡在床前的地板上。这种生活让表弟媳王秋莲感觉十分不便。
天亮后,戴笠必须迅速卷起草席,藏入墙角,腾出空间让屋主人活动。
每到这时,王秋莲总会抱怨几句:"我家又不是收容所。"这种轻蔑的话语几乎成了戴笠每天的"起床铃"。
张冠夫在商务印刷馆做职员,工资微薄,仍收留了这位表弟。
张冠夫年长戴笠几岁,按辈分却是表弟,这种关系错位让家庭关系,更添几分微妙。
阁楼里的生活充满尴尬,夫妻俩如厕、更衣都要避开戴笠,而戴笠则常常装作熟睡,减少存在感。
这种刻意的回避成为三人之间无言的默契。
王秋莲尤其厌恶这种局面,她是戴笠的表妹,本就看不起这个不务正业的表哥。
"又赌了一晚上?输光了吧?"一天清晨,王秋莲看着衣衫不整、满身烟味的戴笠冷冷地说。
戴笠低着头,从口袋掏出几个铜板,默默放在桌上。这点钱连一顿饭都不够,却是他唯一能提供的"租金"。
王秋莲更加恼火:"混子,我家不养闲人"。
她直截了当地要求戴笠尽快另寻住处,张冠夫在一旁为难地劝阻,但妻子寸步不让。
戴笠每天早出晚归,白天在赌场打杂,晚上则在码头附近游荡。
他交友甚广,却都是些被主流社会视为"下三滥"的人物:赌徒、打手、青帮小混混,穿着破旧的长衫,却总能在最低层的社会空间里找到立足之地。
一次,张冠夫陪妻子逛百货公司,在南京路偶遇戴笠。让他们惊讶的是,戴笠居然穿着体面的西装,正与几名衣着光鲜的男子交谈。
张冠夫热情上前打招呼,王秋莲却拉住丈夫,冷眼旁观。
"认识他们吗?"回家路上,张冠夫问。 "不就是些流氓头子吗?和他一样,不是好货色。"王秋莲毫不掩饰她的鄙视。
她不知道,那群人中就有后来赫赫有名的杜月笙。
更不知道,戴笠凭借赌场里的眼力和胆识,已经引起了这位上海滩"大亨"的注意。
杜月笙欣赏戴笠的狠劲和脑子,开始有意扶持。
两人结拜为兄弟,戴笠称杜为"三哥"。很快,戴笠就有了固定收入,不再依靠表弟家的施舍。
但他并未立即搬离阁楼,而是继续忍受着王秋莲的冷言冷语。
1925年春,戴笠在杜月笙的引荐下,与蒋介石见面。
这次会面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不久后,戴笠突然收拾细软,离开了住了一年多的阁楼,张冠夫问他去向,他只是神秘地笑笑:"有机会再聚。"
几个月后,张冠夫收到一封信,是蒋介石办公室的聘书,邀请他去黄埔军校任职。
文件落款处赫然印着戴笠的名字,彼时的戴笠已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开始组建情报网络。
王秋莲对这个机会嗤之以鼻:"跟着那种人能有什么出息?"但张冠夫禁不住诱惑,辞去印刷馆的工作,前往广州。王秋莲无奈随行。
到黄埔军校报到的第一天,张冠夫就被安排了丰厚的职位和宿舍。
迎接他的却不是戴笠,而是一名年轻秘书:"戴先生公务繁忙,暂时无法会面。"这种距离感与过去的亲近形成鲜明对比。
最令王秋莲无法接受的打击在半年后到来。一个貌美如花的年轻女子被介绍给张冠夫,称是"组织安排的特别助手"。
所有人都心照不宣,这是戴笠为表弟安排的"小妾"。
张冠夫不敢拒绝,也不敢拒绝戴笠安排的各种差事。
很快,他成为军统系统内的财务管理员,负责经手大笔资金。
表面上是高升,实则是被牢牢掌控。
王秋莲终于明白,这是戴笠对她多年冷眼相待的报复。
她必须与丈夫的"小妾"朝夕相处,忍受年轻女子挖苦的眼神,曾经高高在上的家庭主妇,如今沦为无权无势的配角。
戴笠在公开场合仍尊称张冠夫为"表哥",私下却再无往日情谊。
每次家宴,他都故意安排"小妾"坐在上席,而王秋莲则被安排在角落,这种精心设计的羞辱,让王秋莲痛不欲生。
当年那个睡在地板上的落魄表哥,如今已成为让人闻风丧胆的特务头子。
当年那个鄙视他为"下三滥"的表妹,如今在他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出。
张冠夫夹在妻子与戴笠之间,进退两难。
他开始酗酒,常常独自一人在院子里坐到天亮,后悔当初带着戴笠去见王秋莲,更后悔没有阻止妻子对戴笠的轻视,但这一切已无法挽回。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往重庆。
张冠夫被调任西南后勤部门,远离戴笠的核心圈子,王秋莲终于摆脱了那个"小妾",却也失去了往日的地位和荣华。
多年后,一位研究民国史的学者,在访谈中问及张冠夫对戴笠的印象,这位已垂垂老矣的长者,沉默许久,只说了八个字:"宁可得罪君子,莫要得罪小人。"
从上海滩的赌场打手到军统特务头子,他的每一步都充满精准计算。
他深谙权力游戏,即使在最落魄的日子里,也能忍辱负重,积蓄力量。
而一旦掌握权力,便毫不犹豫地回击曾经的轻视者。
对于张冠夫夫妇来说,那间八平方米的阁楼,成为他们终生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