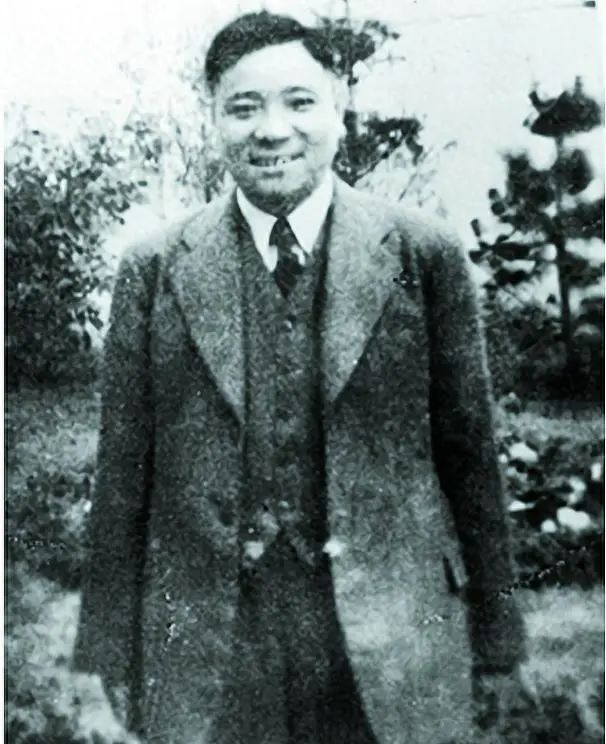1931年2月,欧阳立安被国民党杀害,他母亲讨要不到儿子的遗体就天天在刑场徘徊,可她不知道自己那只有17岁的儿子究竟被埋在哪里。 1931年2月的上海滩笼罩在白色恐怖中,闸北刑场附近的荒地新添了片长势异常的野草丛。 穿着灰布棉袄的中年妇女陶承每天挎着竹篮在此转悠,篮子里装着的冬青树苗在寒风中簌簌作响。 这位痛失爱子的母亲已经在此徘徊半月有余——她的长子欧阳立安被国民党秘密处决后,尸骨至今下落不明。 这个革命家庭的事要追溯到湖南长沙,父亲欧阳梅生早年参加同盟会,北伐时期担任湖南省总工会秘书长,在组织工人运动中积劳成疾。 1928年寒冬,这位革命者在伏案起草文件时突然栽倒,手中的毛笔在《为工人谋福利》的标题下拖出长长的墨迹。 当时刚满14岁的欧阳立安在父亲灵前攥紧拳头,接过母亲递来的针线包——这是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里面藏着地下党联络用的密写药水。 遗传了父亲倔强性格的少年很快在革命队伍中崭露头角,12岁那年他带领儿童团查获奸商囤积的食盐,15岁成为共青团骨干,16岁那年竟收到赴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的调令。 在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上,这个连俄文字母都认不全的年轻人帮女工代表黄菊英修改发言稿,用烧焦的树枝在草纸上逐字推敲。 少共国际会议上,他别在胸前的铜质代表证在镁光灯下闪闪发亮,这张证件后来却成为国民党特务指认其身份的铁证。 1931年1月17日,上海中山旅社的木质楼梯响起密集脚步声。 正在开会的欧阳立安与三十多名同志被捕时,特务们对这个满脸稚气的"小毛头"产生怀疑。 审讯室里,主审官将钢笔往墨水瓶里蘸了蘸:"只要你说出同党,立马就能回家。" 少年盯着审讯记录纸上的"自首书"三个字,突然抓起钢笔在空白处写下:"我是共产党员,筋骨成灰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这份如今珍藏在龙华烈士纪念馆的审讯笔录,字迹力透纸背的笔画间还夹杂着莫斯科带来的松油墨香。 二十天后,龙华警备司令部刑场的泥土还凝着霜花。 据1951年落网的行刑队长供述,当法官拖着长腔宣读判决书时,二十四名戴着铁镣的囚犯突然齐声高唱《国际歌》。 枪声响起时,连接二十四双脚踝的铸铁群镣发出金属碰撞的哀鸣——这副重达八十斤的刑具现陈列在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每根铁链的环扣都残留着深浅不一的抓痕。 陶承在儿子遇害三年间接连失去丈夫、幼女和长子。 当她发现刑场某处野草长得格外茂盛时,既不敢惊动看守,又怕野狗刨出尸骨,只能偷偷移栽冬青树作为标记。 这棵在乱石堆里顽强生长的常青树,直到1950年挖掘烈士遗骸时才被认出——考古人员翻开土层,二十四具交错叠压的骸骨脚踝处,铸铁群镣已与骨殖锈蚀成整体。 这位历经沧桑的母亲,在1943年又送别了参加抗日的次子欧阳稚鹤。 当小儿子牺牲的电报从太行山区传来时,十六岁的年龄数字让她恍惚看见长子当年在莫斯科红场挥动红旗的身影。 1960年代,陶承在《我的一家》中记录了这个红色家族的往事,书中关于母子诀别的章节被改编成电影《革命家庭》,周恩来总理观看后特意叮嘱剧组:"要拍出中国母亲的坚韧。" 1986年深秋,九十三岁的陶承在长沙安详离世。 殡仪馆工作人员发现,老人贴身口袋里除了全家福照片,还有片早已风干的冬青树叶。 如今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那棵移栽自刑场旧址的冬青树已亭亭如盖,树下纪念碑镌刻着二十四烈士的姓名。 每逢清明时节,总能看到白发老者驻足树下,用湘音轻声哼唱《国际歌》的旋律。 (官方信源: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展陈资料;《我的一家》陶承著,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中央档案馆《龙华二十四烈士案卷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