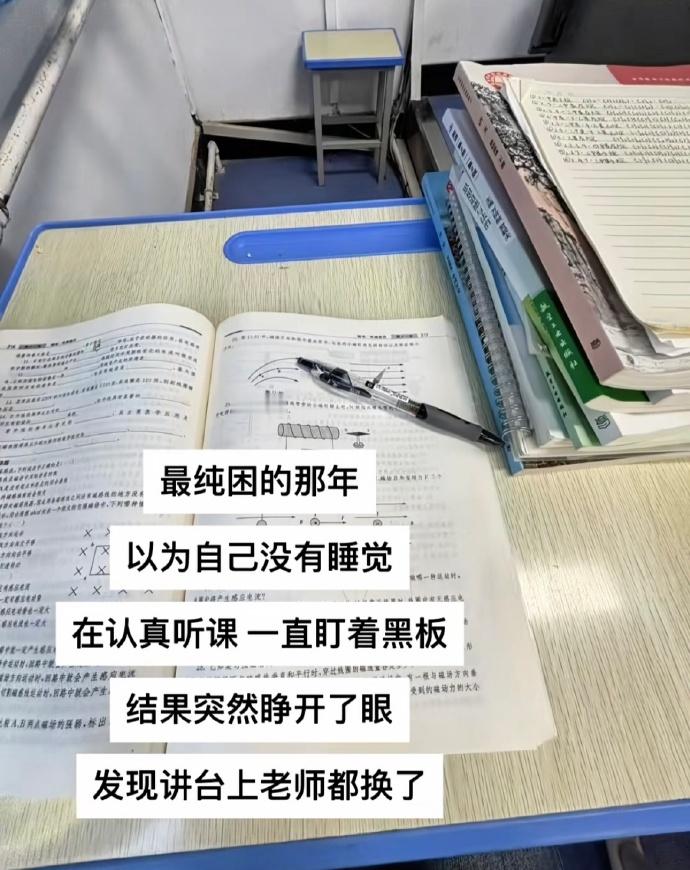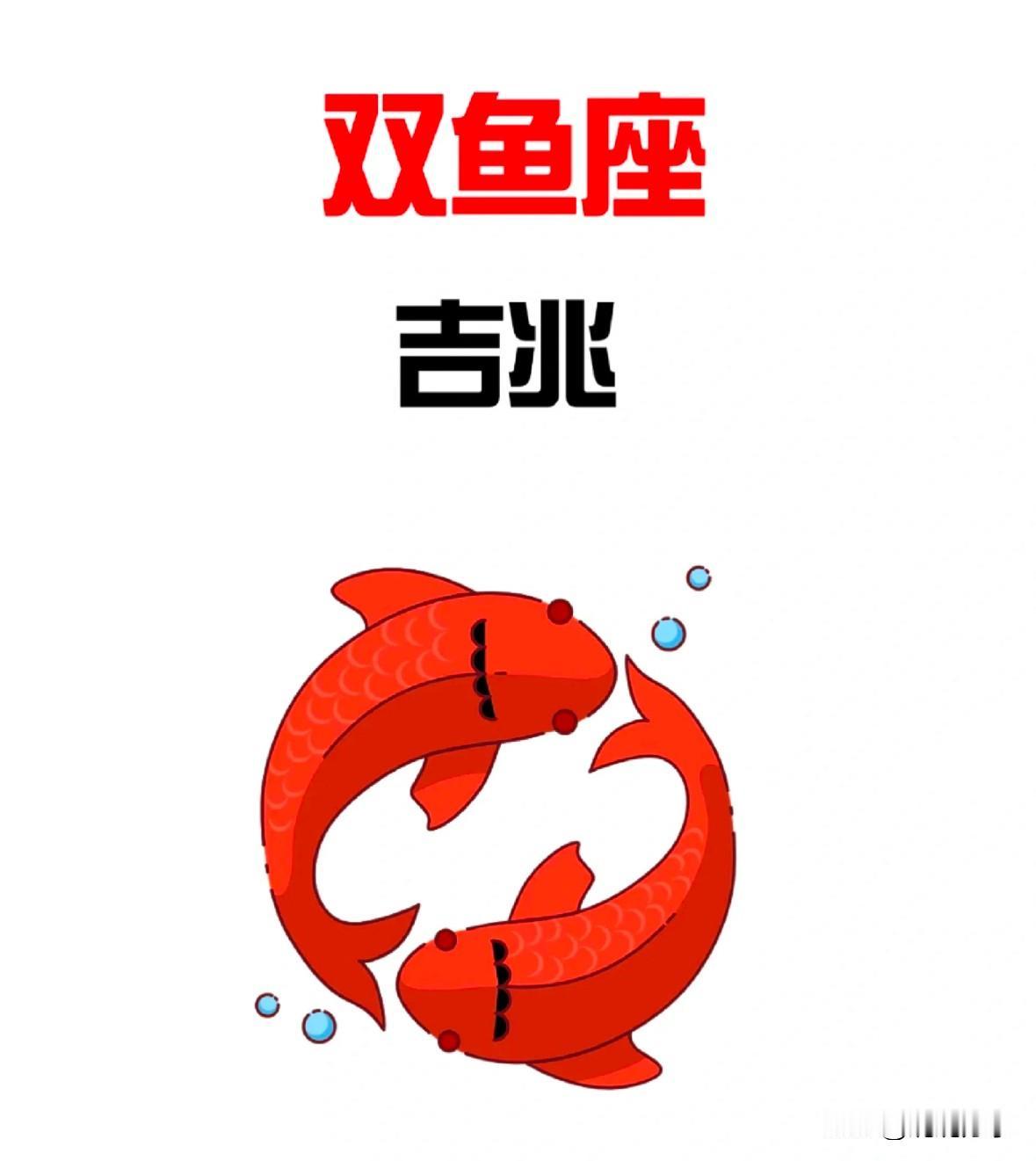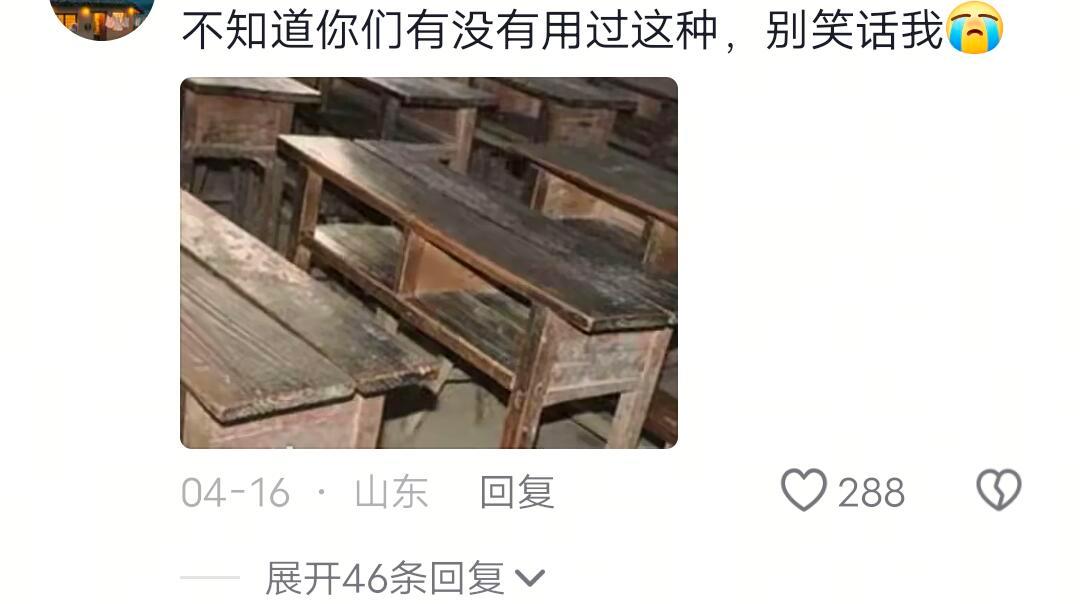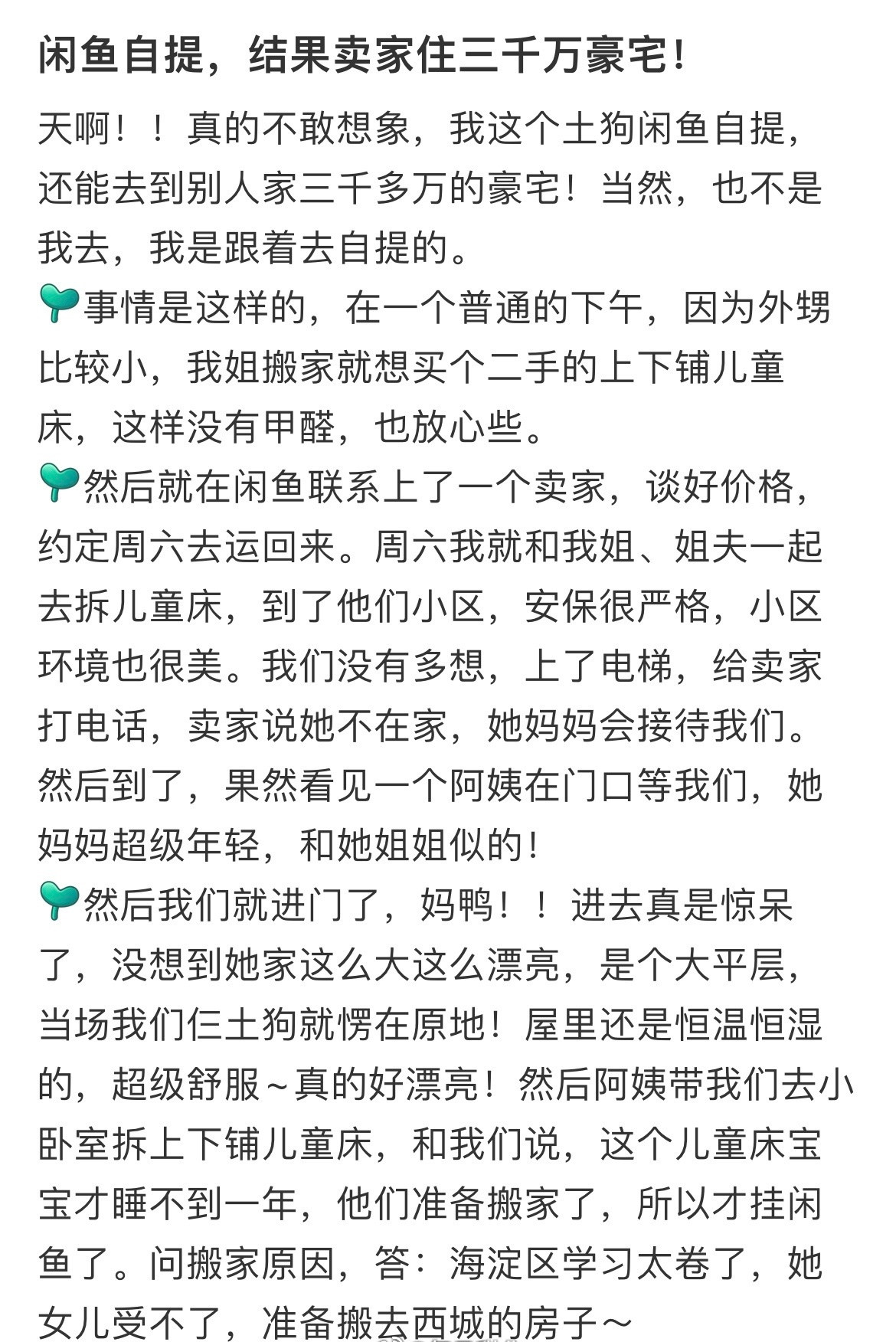1997年,86岁的杨绛看着已病若膏肓的女儿钱瑗,贴在她耳边轻声道:"安心睡吧,我和你爸爸祝你睡好。"话音刚落,钱瑗缓缓闭上了双眼。 在1997年3月4日,北京医院的病房里格外安静。杨绛坐在病床前,轻轻拉着女儿钱瑗的手。 这一刻,86岁的杨绛望着躺在病床上的女儿,用最温柔的声音说出了最后的话语:"安心睡觉,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听到这句话,钱瑗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这个笑容定格在了1997年3月4日,成为了母亲杨绛永远的记忆。钱瑗带着这个笑容离开了这个世界,永远停留在了她56岁的年纪。 从1966年开始,钱瑗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英语,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在课堂上,她是严谨认真的教师;在学术研究中,她是孜孜不倦的学者。 1993年,钱瑗被北京师范大学聘为外语系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这是对她学术成就的最高肯定。这个头衔背后,是她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和付出。 钱瑗继承了母亲杨绛淡泊名利的性格,从不追求虚名和地位。在她的世界里,只有教学、科研和学生。 每天深夜,北师大外语系的教室里常常亮着一盏灯,那是钱瑗在备课。第二天清晨,她又是第一个到达教室的老师。 由于学校师资紧张,钱瑗主动承担了大量的教学任务。她不计较个人得失,只在意学生能否真正学到知识。 然而,高强度的工作最终透支了她的健康。起初的咳嗽和腰痛,被她简单地归结为劳累和感冒。 直到医生诊断出晚期肺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她仍然惦记着自己的教学工作。即便在住院期间,她也时常询问学生们的学习情况。 1995年冬天,钱瑗住进了西山脚下的医院。这个消息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从确诊的那一刻起,钱瑗就下定决心要隐瞒病情的严重程度。在母亲杨绛面前,她总是表现得轻松愉快。 每天傍晚,母女俩都会通一通电话,这成了她们最重要的联系方式。她们给这种通话起了一个温馨的名字叫"拉指头",因为无法像见面时那样手拉手。 电话里,钱瑗总是报喜不报忧,谈论着学校的趣事和学生们的情况。尽管化疗让她失去了一头黑发,她在电话中依然笑着对母亲说:"我现在是尼姑。" 杨绛每周都会去西山医院看望女儿。但这些探视总是很短暂,因为钱瑗不愿让母亲看到自己日渐消瘦的样子。 在三里河的家中,杨绛还要照顾着丈夫钱锺书。为了不让丈夫担心,她对钱锺书说女儿只是得了骨结核。 钱锺书相信了这个解释,还说:"坏事变好事,阿圆从此可以卸下校方重担,也有理由推托不干了。"这句话让杨绛既欣慰又心酸。 1994年夏天,钱锺书也因病住进了医院。这让本就忙碌的杨绛更加奔波。 她每天都要去看望丈夫,为他送饭送菜,准备各种营养汤水。同时还要兼顾对女儿的照顾,在医院和家之间不停往返。 钱瑗的病情在1996年开始急转直下。尽管如此,她仍然坚持不让母亲经常来探望。 每次母亲要来看她,她总会找各种借口推辞。她说自己在休息,说正在做检查,说今天医生特别多。 在三里河的家中,杨绛依然维持着正常的生活节奏。她每天按时为丈夫准备饭菜,整理房间,就像过去的几十年一样。 然而,这个家已经不再完整。三里河的寓所少了欢声笑语,只剩下了一种沉默的等待。 这段时期,杨绛成了这个家唯一的纽带。她像是一个无声的使者,在医院和家之间往返,传递着爱与牵挂。 钱瑗离世后,她生前的同事们为她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告别仪式。在她充满笑容的遗像旁,摆放着一个精致的花篮,素带上写着:"瑗瑗爱女安息!爸爸妈妈痛挽。" 那天,杨绛没有出现在告别仪式上。她选择独自在家中,用自己的方式送别女儿。 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师生们难以接受钱瑗的离去。他们向杨绛提出请求,希望能够保留钱瑗的一部分骨灰。 最终,他们选择了校园里的一棵雪松。这棵树站立在钱瑗曾经每天必经的路上,见证过她无数次匆匆的脚步。 在钱瑗离世近百日的时候,杨绛独自来到了这棵雪松旁。她安静地坐在那里,用苏东坡的悼亡词表达思念:"从此老母肠断处,明月下,常青树。" 1998年的冬天,更大的打击降临到了杨绛的身上。她的丈夫钱锺书在岁末离世。 至此,曾经相濡以沫的"我们仨",只剩下了杨绛一人。三里河的寓所显得格外空旷。 在钱锺书离世后,杨绛开始执笔写作《我们仨》。这本书记录了这个家庭的点点滴滴。 书中,她写道:"人间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三里河的寓所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样子。钱瑗的房间,她的书籍,她的物品,都被小心地保存着。 每年钱瑗的忌日,杨绛都会收到北师大学生们送来的鲜花。这些花放在书桌上,仿佛在告诉她,女儿的精神依然活在学生们的心中。 在往后的岁月里,杨绛继续创作、翻译,用工作填补生活的空白。她的坚强和优雅,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一盏明灯。

![该陪孩子陪孩子,二人世界还是要有的[呲牙笑]在一大家子陪着小玥儿过完生日后,汪小](http://image.uczzd.cn/11686834986099924934.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