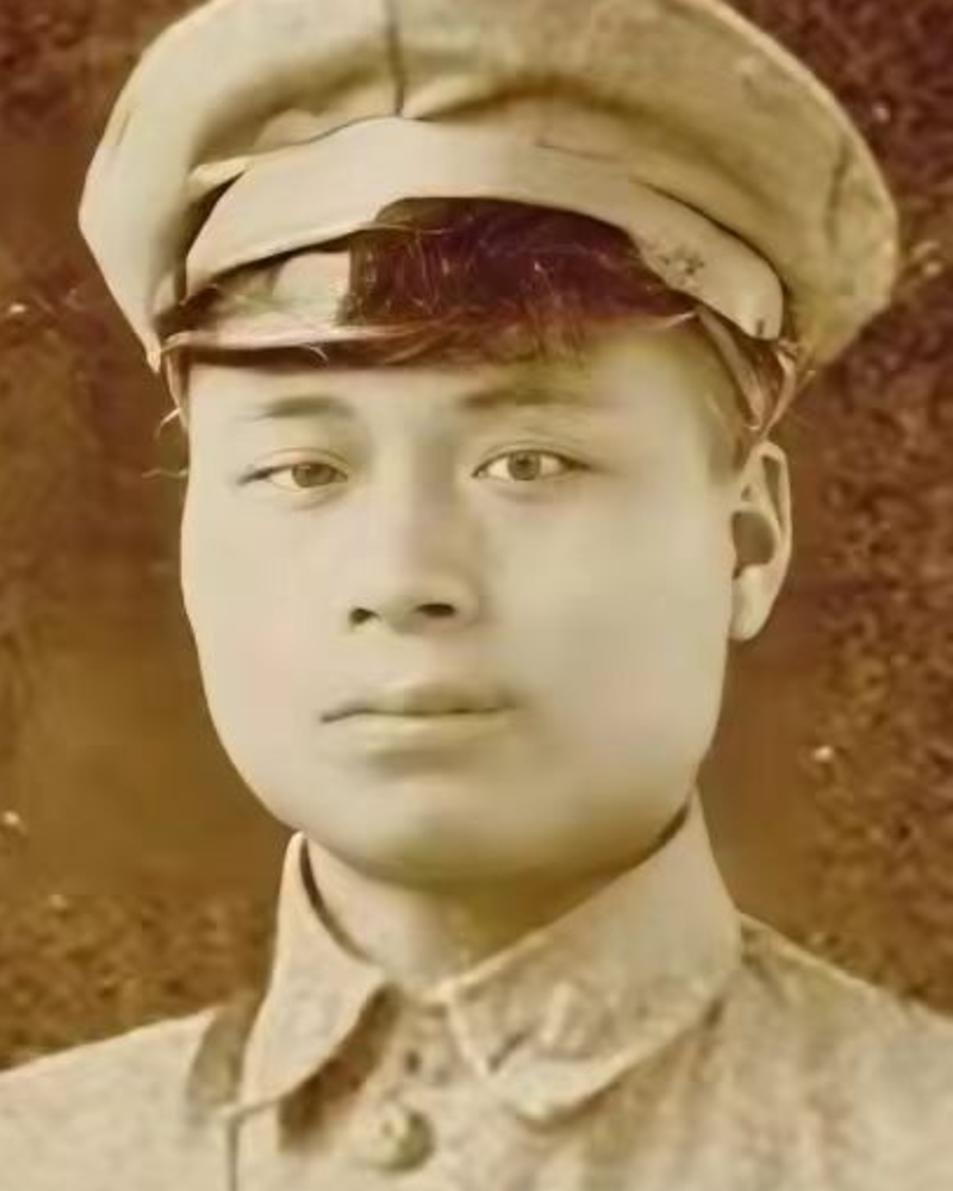1935年11月1日,伪装成记者的杀手孙凤鸣不见蒋介石出来,吞下的鸦片也已发作,他掏出藏在相机中的手枪,向汪精卫冲去连开三枪。 枪声划破了南京的寂静,汪精卫应声倒地,孙凤鸣站在混乱的人群中,脸上没有一丝畏惧。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会场外,寒风裹挟着紧张的气息。国民党要员们刚刚结束会议,正准备在大会厅前合影留念。人群中,孙凤鸣伪装成晨光通讯社的记者,手中的相机只是道具,腰间的手枪才是他真正的底牌。 他的目标是蒋介石,那个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名,迟迟不抗日的领袖。然而,命运开了个玩笑——蒋介石临时缺席,留给孙凤鸣的,是一个必须当机立断的抉择。 南京的清晨,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湿气。孙凤鸣站在记者群外围,灰色呢帽遮住半张脸,眼神却像猎鹰般锐利。他早已吞下鸦片,药效在体内缓缓发作,带来一阵阵眩晕。 他知道,时间不多了。会场外,国民党要员们三三两两走出,孔祥熙的笑声刺耳,张学良皱着眉低声与人交谈,汪精卫则姗姗来迟,穿着笔挺的西装,站在合影队伍的最前列。孙凤鸣的手指在相机上轻轻敲击,心跳却越来越快。蒋介石没来,计划全盘落空,但他不甘心就此退场。 孙凤鸣的脑海中闪过往日的画面。1905年,他出生在江苏铜山的一个破败村庄,家徒四壁,父亲靠打零工养活一家五口。1920年代,父子俩闯关东,沿途的饥荒、战乱和日军铁蹄下的屈辱,让他年少的心中燃起救国之志。九一八事变后,他加入十九路军,满腔热血想驱逐日寇,却被上级调往江西剿共。 战场上,他亲眼见到同胞的血流成河,国民党“先安内”的政策让他愤怒至极。他脱下军装,誓言不再为这样的政权效力。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33年南京街头。孙凤鸣偶遇华克之,一个同样痛恨蒋介石政策的青年。华克之创办了晨光通讯社,表面上是新闻机构,实则是反蒋抗日的秘密据点。两人一拍即合,孙凤鸣在通讯社刻苦学习,学会了摄影、采访,甚至伪造证件,只为掩护更重要的行动。 1934年秋,孙凤鸣向华克之提出刺杀蒋介石的计划,定在四届六中全会上动手。华克之犹豫再三,最终递给他一把手枪,低声说:“兄弟,活着回来。” 11月1日,合影的时刻终于到来。孙凤鸣站在人群后,假装调试相机,实则观察着每一位要员的站位。汪精卫站在最显眼的位置,孙凤鸣的眼神一凛。他知道,汪精卫虽与蒋介石明争暗斗,但在“容共”与“清共”间摇摆不定,其政策同样让抗日事业一再受挫。 既然杀不了蒋介石,汪精卫便是次佳目标。孙凤鸣深吸一口气,鸦片的药效让他的视线有些模糊,但他强撑着站稳,猛地抽出藏在腰间的手枪,高喊:“打倒卖国贼!” 三声枪响,震耳欲聋。汪精卫胸口与背部连中三枪,踉跄倒地,鲜血染红了西装。会场瞬间炸开了锅,孔祥熙吓得钻进汽车底下,多数要员抱头鼠窜。唯有张学良和张继反应迅猛,冲向孙凤鸣,与他扭打在一起。汪精卫的卫兵也回过神来,举枪射击,子弹击中孙凤鸣的腹部,他倒在地上,血流不止。 南京中央医院的病房里,消毒水的气味刺鼻。孙凤鸣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腹部的伤口仍在渗血。医生摇摇头,低声对旁边的国民党军官说:“他活不过今晚。”军官冷笑,递给医生一叠钞票:“给他打强心剂,务必问出幕后主使。”病房外,寒风吹过窗户,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在为这个年轻的生命送行。 孙凤鸣半睁着眼,意识模糊。他想起闯关东的苦难岁月,想起十九路军的战友倒在江西的山野,想起华克之递给他手枪时眼中的担忧。他知道,自己绝不会供出任何人。 刺杀事件震动全国。汪精卫被紧急送往医院,手术保住了性命,但子弹留下的后遗症让他此后饱受折磨,直至1944年去世。蒋介石赶到现场,面对汪精卫妻子陈璧君的泪水与质问,一时无言。社会舆论沸腾,有人猜测这是蒋介石铲除异己的阴谋,有人则将矛头指向共产党。 直到华克之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承认自己与孙凤鸣的计划,澄清共产党无关,舆论才渐渐平息。 孙凤鸣的死并未换来他期望的抗日局面。蒋介石继续“攘外必先安内”,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晨光通讯社也在事件后被查封,华克之销声匿迹。但孙凤鸣的名字,成了那个时代无数爱国青年抗争的缩影。 1935年11月2日凌晨,孙凤鸣在病床上闭上了眼。他的枪声虽未能改变时局,却如一声惊雷,唤醒了无数沉睡的灵魂。 孙凤鸣刺杀事件不仅反映了1930年代青年对国民党政策的极度不满,也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的撕裂。九一八事变后,抗日呼声高涨,但蒋介石的“剿共”优先政策导致大量爱国人士转向激进行动。 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930年代类似的反蒋刺杀事件多达数十起,晨光通讯社等民间组织成为这些行动的温床。孙凤鸣的失败,凸显了个人英雄主义在复杂政治博弈中的局限性,却也激励了更多人投身抗日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