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新加坡以“花园城市”闻名于世,其整洁、安定的社会秩序背后,是一套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高效法律体系。 这个城市国家虽面积不大,却以雷厉风行的执法方式维护社会稳定。尤其在公共秩序方面,新加坡政府以“零容忍”态度对待任何破坏行为,其中包括严厉的鞭刑制度。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18岁的美国青年麦克·菲尔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他随继父来到新加坡,进入当地的美国学校学习。外表俊朗,个性张扬的菲尔早年成长于美国中产家庭。 父母早年离异,母亲改嫁,他与继父关系并不亲近。他在旧学校因多次恶作剧和违反纪律被停学,甚至有过在校园内纵火的记录。 新加坡本希望成为他“重新做人”的起点,但菲尔却并未收敛。他对严格的社会规矩感到不适应,甚至将之视为挑战权威的机会。 他开始在街头巷尾涂鸦、恶作剧,并很快升级为更严重的破坏行为。新加坡的环境,在他眼中不过是一块可以“放肆试探”的游乐场。 那是1993年3月的一个晚上,菲尔与几名同校的朋友在夜色掩护下走入新加坡市区的某个社区。他们带着金属棒和钉锤,潜入停车场,逐一砸毁车辆窗户,轮胎则被他们用刀具刺破。 整个过程持续了近一个小时,他们共破坏了20辆私家车,有些车窗玻璃破裂成蛛网状,碎片洒了一地,有些轮胎整个瘪下去,金属轮毂擦地发出刺耳声响。 当街区的警报器此起彼伏地响起时,菲尔却带着快感笑出声。他并未意识到,这一行为将为他带来何等严重的后果。 次日清晨,车主报警,警方立刻展开调查。通过附近建筑的监控录像,警方迅速锁定了几名嫌疑人。菲尔的身影清晰可辨,他当晚所穿的美国校队夹克成为确认其身份的关键。 被捕时,菲尔仍显得不以为意。他在警局笑着对警察说:“我不过是让他们长点记性。”他以为,这不过是一次青少年的过激玩笑,最多不过罚款或是短暂羁押。但很快,他的幻想被撕碎。 新加坡法院依据《破坏公物法》展开审理,整个审判过程公开透明,但节奏迅速。菲尔在初次听审时仍以轻佻态度应对,在法庭上搅局、不尊重程序,还一度拒绝承认自己有罪。他的无礼行为激怒了法官,也引起公众反感。 最终,法院判决菲尔需支付3500新币罚款,并承担4个月监禁及6次鞭刑。得知这个判决后,菲尔脸色煞白,他第一次意识到事态严重。他试图通过律师提出上诉,结果却适得其反——因他在庭审中无理取闹、对法官不敬,鞭刑从6次提高到了12次。 此时,美国国内的媒体开始关注此案。美国国务院介入,总统比尔·克林顿亲自向新加坡总统王鼎昌致函,恳请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菲尔从宽处理。王鼎昌最终决定将鞭刑次数减至4次,但拒绝完全撤销这一惩罚。 行刑那天,新加坡当局严格按照流程执行。鞭刑官身着制服,手持特制藤条,力度和角度都经过训练,务求一击即中。菲尔被带到刑场,他被要求俯身趴在刑架上,衣物被卷至腰部,手脚被牢牢固定。他全身绷紧,牙关紧咬。 第一鞭落下,鞭痕立现,皮肤瞬间破裂,鲜血涌出。菲尔尖叫出声,声音回荡在整个行刑场上。 第二鞭、第三鞭接连挥下,他背部和臀部的皮肤已被彻底撕裂,伤口深可见肉,第四鞭带着彻骨痛楚如同火焰灼烧。他面色苍白,汗水和泪水交织,几欲昏厥。 结束后,他瘫软在地,狱警将他扶回牢房。狱医立刻为他清创、消毒、包扎,处理过程中,菲尔几次因剧痛低声哀嚎,整个人几乎脱力。 行刑过后,菲尔的身体一度虚弱到难以自行如厕。医生每日为他更换药布,他的伤口需要至少一个月时间才能愈合,而心理的创伤则更难恢复。 几日后,美国驻新加坡大使到狱中探视。他走进牢房时,菲尔正在床上半卧,脸色憔悴,大使的到来引起了他片刻的希望。他试图站起,却因伤口牵动而又跌坐下来。 大使检查了他的伤势,眼见那血肉模糊的皮肤,一度沉默良久。尽管带来了慰问与承诺,大使也无法改变现实。探视结束时,菲尔眼中泛起泪光,他的桀骜早已在鞭刑与痛苦中被撕裂。 随着案件持续发酵,美国社会对新加坡刑罚制度的讨论愈演愈烈。有人批评其残酷、违反人权,也有人反思为何美国年轻人在异国他乡无法自律。新加坡政府则坚持立场,表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国籍,皆须遵守。 菲尔服刑期间每日生活清淡,阅读成为他唯一的消遣。他开始写日记,记录自己的感受。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这四鞭比他过去18年所有惩罚加起来还要痛苦,但也让他第一次思考“责任”两个字的真正含义。 1993年8月,麦克·菲尔刑满释放,随即被遣返回国。他走出樟宜监狱时,脸上不见往昔的轻狂,多了一份沉默与木然。记者拍下了他被搀扶上飞机的一刻,那张苍白的脸似乎印着无法抹去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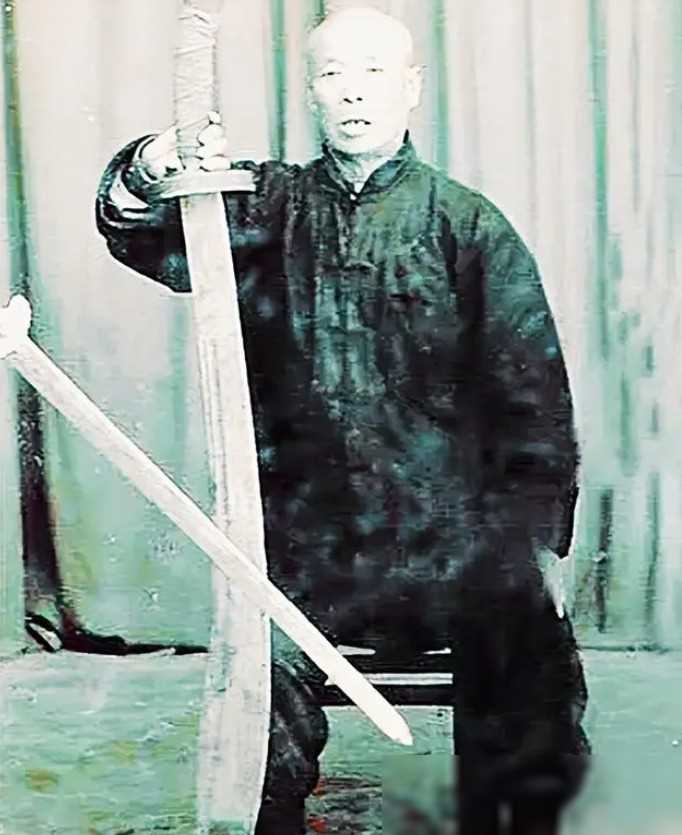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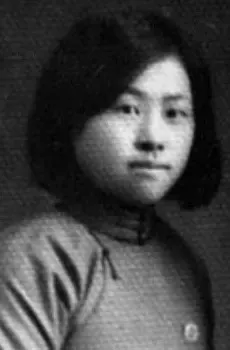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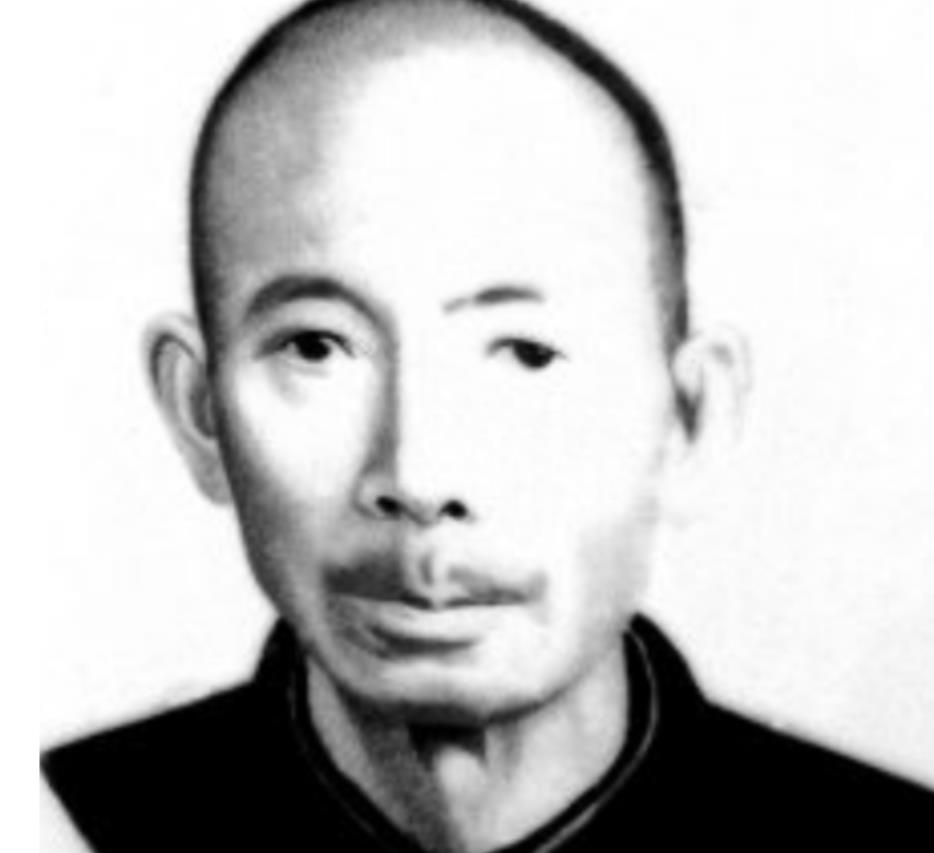

不再天真VS我本善良
几鞭子抽到美国人的心脏上了。